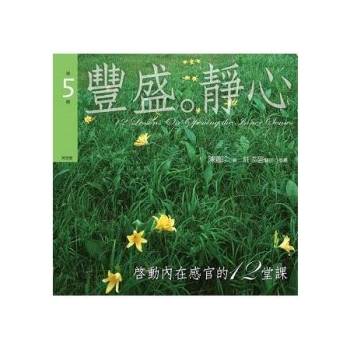序
起先,他不過是想找些樂子。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中載,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於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他看到這卷書時不禁嗤鼻,對它們這種上古異獸居然就三行的形容,必定是撰寫此本的凡人不敢靠近,只能遠遠躲著稍微看那麼一眼,就想當然地寫下來。不過說得卻也不錯,他確有旱燥之能,只要他高興,眨眼間可枯乾大河,遍邑大旱。
但這樣又如何?看了凡人在旱魃肆虐之時,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慘狀,他再插一腳進去?未免太過無趣。
善惡之分,在凡人而言,不外乎有否助力,助者為善,逆者為惡,所以像他這種游離三界外的異獸,能招大旱者,似乎便被劃為萬惡之方。然則他也無妨,反正沒少看到那些有力量卻缺大腦的古獸被拉撥上天,要麼當仙人的坐騎,要麼被當作看門的狗。
他可沒興趣在脖子上掛條鎖鏈,人間逍遙,偶爾與凡間一些自以為功力非凡的遊方道士,或者是就快得道的散仙周旋一下,也是樂趣不是?反正他活得夠久,也修煉得夠久,有幾多個萬年連他自己都記不住的時長,令他有足夠的能力,至今未逢敵手。
可惜漸漸的,連天上的仙人都不多見了,妖怪見了他也懂得躲開,又開始無趣起來。
因此,當從一隻險些被他拿來果腹的豹妖嘴裡聽到逆龍應帝糾合百萬妖軍,逆天作亂之時,他忍不住咧嘴笑了半天。
似乎成為應帝麾下的將領並不複雜。
在他將自己的頂頭上司──一隻馬腹妖給吞了之後,便沒有妖怪再敢位居其上。其實他也很無辜啊!誰讓那隻馬腹人面虎身,還作嬰兒之聲,在他面前嚶嚶哽哽地指手畫腳,看了就心煩。
正巧他因為放過了那隻提供消息的豹妖而腹中空虛,只好拿它來填肚子了。
於是他很快就被應帝召見。
也許再過一千年,不,大約五千年吧,他也不會忘記初見應帝時的情景。
他本來以為對方也就是個有點能耐,野心過大以至於自大瘋狂的妖怪,說不定還能取而代之,不必受人制肘,自己領軍玩個痛快。
然而坐在帝帳內的男人,那雙淬金瞳孔,彷彿看透了他的心思,銳利的視線彷彿已將他整張蛇皮剝下。
力量,這個男人有絕對凌駕於他的力量。
強大得足以讓他不敢升起逆上之意。
有一瞬間,他甚至覺得,此人有掌控天地之能,跟隨他,能逆轉乾坤,地為天,妖為仙。
當然,也就是一瞬而已,他一向對仙妖之別,善惡之分並不在乎,眨眨眼,倒是恭敬朝那上座的帝君行禮:「屬下九鳴,願效力帝座麾下!」
縱然語氣恭敬,但心裡的言不由衷似乎仍逃不過應帝一雙銳目。
然應帝卻並未作惱,更對他吃掉上司,自相殘殺的行為全不在意,將他封為將軍。
連跳幾級,對於他這個加入不到一天的新妖物來說,少不得引來多方忌妒。找茬的妖怪層出不窮,他非但不為此煩惱,甚至有些樂此不疲。
反正伙食是不成問題了。
不過過沒多久,挑釁的妖怪逐漸減少,直至就算他經過也沒有敢正眼瞧他的妖怪時,他又開始覺得無趣了。
第一章
那一天,也像之前的每一天。
他覺得非常無趣。
軍帳之內,只見將軍座上坐了一名精壯男子,看他一頭赤髮猶如火焰,蓬鬆飛揚也不束冠。面相英俊,挑起的唇角帶著幾分流氣,隨意披在肩上的紅袍下,上半身不著片縷的赤裸,然即便隨意靠坐椅上,但胸腹的肌理依舊看來結實分明。
在他身旁貼繞了幾名美豔的女子,姿容絕麗,七彩薄紗衣裙,豐滿的酥胸若隱若現,皮膚白皙如乳,曼妙肢體柔軟地貼在男人身側。
一名黃紗的美女用細長的手指剝開一顆葡萄放入口中,嬌媚地爬到他肩膀,朱唇吐芬,含珠欲滴,極是誘惑。
那男人笑意一深,忽然左臂撈過,將那女子蜂腰擁緊,準確無比地吻住女子豐美的嘴唇。調情的葡萄輕易被他挑過吞掉,隨即舌頭深探,誘得那女子嚶聲亂喘,擒在蜂腰上的大手順勢下移至豐滿的臀部,薄如蟬翼的紗衣彷如無物,時弱時強的搓揉,只讓那女子連腰都軟了,不由得情慾大起,玉手更大膽地扯開男人的衣襟,豐碩雙乳貼上那硬石般結實的胸膛磨蹭求得更多愛撫。
然那男子卻在此時將她放開,女子眼神迷離,意猶未盡般呻吟不已。
旁眾女子見狀,不甘示弱地紛紛拿起酒水,欲以皮杯伺候。
他自然是來者不拒,不多時,帳內春情蕩漾,一眾女子羅衫半脫,玉體橫陳,面上皆是迷亂神色。
然坐在正中的男人掃了一眼,流氣的紅目居然未見半分情動,只隨手拉了拉被扯得大開露至腹肌的衣袍,好笑地彎身出去撈過酒罈海碗,邊自斟飲邊是埋怨:「叫妳們來伺候我喝酒,怎麼還要我自己來倒?」
酒是好酒,問題是沒人陪著喝,味道便差了許多。
不由歎氣。
與他並屬應帝麾下的黑虯將軍倒是喜酒,可惜今日不在軍中,其他的妖怪,別說是陪酒,見著他便躲,實在無趣得很。
正想著,忽聞軍帳外響起吆喝:「你是何人?!竟敢私闖──」話音未落,就聽「啪!」一聲巨響,黑影撞開門簾跌落帳中,他定眼看來,竟見一段半截人形落在中央,血淋淋的半截人形痙攣幾下,便斷氣現出原形,變回半隻山羊。
男人座下的那些女子聞到血腥味道,非但沒有嚇得花容失色,反而紛紛激起,豔美臉容妖相盡露,瞳孔閃爍青光,紅唇張開竟嘶嘶吐出前端分叉的細長蛇舌。
隨之有人掀簾進帳,男人不由好奇地打量來人,但見此人面相普通,灰布衣服,髮髻瀏海均非常整齊,一雙灰中有白的瞳孔好像連轉都不轉,讓他不禁以為又是一具被丟進來的屍體。
那人說話了,及時解除了他的疑惑。
「稟將軍,流月峰後發現天軍潛伏。」
「哦……」
座上的妖怪顯然意興闌珊,托了下腮,「流月峰好像……是黑虯營區附近,怎麼鬧到我這裡來了?」
「軍情緊急,黑虯將軍不在軍中。」
「這樣啊……」終於,他站起身來,大大伸了個懶腰,也罷,雖然他不想多管閒事,但畢竟在應帝麾下辦事,總不好眼睜睜看著那些天兵天將踩進大營耀武揚威吧?
踩過一地血腥,他忽然頓了頓步,問道:「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硬邦邦的聲音,就像敲在鏤空的石頭上般,空明,也冷漠。
「屬下飛簾,左路前鋒斥候。」
第二次見到時,這個男人已經與他同坐帝君軍帳之內,位落將軍尊座。
其時應帝麾下本已有三員大將,分別是黑虯,姚諸,九鳴。
在座四人當中最為魁梧者,正是黑虯將軍,此人看上去像座鐵塔般聳立,面前那張矮桌子跟他這麼一比,就像小孩子玩具一般小巧,他那膚色倒跟名字頗為相稱,黑似鑊鐒,加上面貌醜陋,伺候的妖女們都對他不屑一顧。他倒是沒所謂,自顧自埋頭大喝。
至於另一位,身材四肢修長甚至可以說是乾瘦的男人,臉又長又窄,兩眼分得極開,幾乎像張鹿臉,不過有個好處,就是他打量人的時候很難叫人察覺,這位正是姚諸將軍。
至於新上任的那位,卻是個面無表情,皮膚灰白陰暗,連眼珠子都像抹上了一層白膜,怎麼看都看不出半點情緒,簡直與殭屍無異的男子。
與這三位,要麼沒情趣,要麼面相醜陋的將軍相比,最後一位將軍自是更得侍奉的妖女青睞。這個赤紅頭髮的男人,面相英俊不在話下,加上一雙倒三角的眼睛總是邪魅挑眼,就像一把小刀斜斜劃過女人的心湖,若即若離的疼痛,似被蛇鋒利的毒牙輕輕劃過手臂,在不知道是不是中了蛇毒的困頓中迷惑。
瞧他極有情趣地拈起酒杯,旁邊伺候的女子便爭先恐後地搶著給他倒酒,誰都為這位九鳴將軍能喝上自己倒的一杯酒而沾沾自喜。
只是這位九鳴將軍,看似極為受落,可那眼睛卻是在看別處。
坐在他對面那個面無表情的男人,他看著覺得有些眼熟,愣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但看他神情木訥,也沒感覺到什麼厲害妖氣,卻不知應帝何以破格提拔。只是既然能入帝君法眼,應該也不簡單。
畢竟妖軍之內,一切以力量說話,可不似凡人軍內,必要有一定世家身分才能位至軍將,只要有能力,幹掉上司直接提升的他本身就是一個典範。
他倒是有這個耐性慢慢考據,不過這軍中的妖怪可不是個個像他願意花時間做些無聊事。
今日應帝不在,除了那個埋頭大喝不理旁事的黑虯將軍外,便剩下那姚諸將軍自居最高。他先於九鳴拜入應帝麾下,因隨帝君舉事也早,封為將軍。說起此妖,倒有些神能,能招大水,淹邑化澤。
隨著妖軍勢力日盛,他那氣焰也漸見囂張。
見黑虯將軍總是平和樸實,不怎麼言語,便總是百般挑釁,但礙於黑虯與應帝同是龍宗,不看僧面看佛面,也不敢做得太過出格。
而對於遲於他的九鳴來說,倒是願意姚諸來找些麻煩,可偏偏那傢伙還有點眼力,看出對手是隻旱妖,只怕招再多的水也不夠他給蒸乾,也就不敢多做其他。
這廂又冒上來一個木口木面,橫看豎看也看不出有什麼本事的傢伙,眼下帝君不在座上,自然有了欺生的打算。
只見那姚諸站起身,藉了酒意走到那木面男人面前,掃了一眼桌上面完全沒有動過的菜餚和美酒,皮笑肉不笑地哼道:「為何滴酒不沾?莫非是嫌帝君賜的酒不夠好麼?」
若比常人,必定會多做解釋,免得落了話柄,然而席地而坐的男人連眼角都不抬起丁點,完全無視對方的挑釁。
如此一來,那姚諸大覺面子全失,看他那張又長又窄,連化形都跟馬鹿差不多的臉一下脹紅。不過他還多少有點將軍的自覺,很快恢復了冷靜,冷笑一聲,嘲諷道:「真是的,也不知帝君想些什麼,難道現在是誰都能當將軍了嗎?說不定明日就該輪到貓妖狗怪了!」可惜對方依舊不聞不問,讓他一個人在唱獨角戲,姚諸嘴角抽動,生硬地轉過臉來,朝九鳴舉杯道,「九鳴,你是說吧?」
有好玩的他又怎會不摻乎?
九鳴咧嘴一笑:「說得是啊!將軍之位可不好坐!」
姚諸想不到他居然和應,當即連連點頭。
不想聽他再說:「當將軍的得有隨時被下屬取而代之的覺悟才行呢!哈哈……」九鳴拿起酒壺施然倒滿一杯,朝他稍稍一抬手,歎道:「也不知道下次帝君設宴款待的將軍,還會不會是在座幾位?不過這變來變去的,倒也有趣得很!」
姚諸豈會不知眼前這個赤衣紅髮的妖怪九鳴便是殺了上司取而代之而當上將軍,他這麼一說,擺明就是諷刺自己要多加小心,莫要被下屬莫名取代,登時氣得七竅生煙。
只可惜雖惱恨此妖,卻又無法與之計較,不由得咬牙切齒道:「說不定是你的座位上換人!」
九鳴歪頭想了想,似乎覺得也有道理,便呵呵笑道:「那樣也挺好!……挺好!」
「瘋子!」姚諸冷哼一聲,拂袖回座。
九鳴有些沒趣地自喃自語:「不是吧?這樣就不玩了?!」說罷,搖搖晃晃站起身來,湊過去一屁股坐到飛簾身邊的位置,好像跟對方是幾百年的老交情般樂呵呵地招呼道:「前些天只顧著招呼天兵天將,還真不知道又多了位將軍!呵呵!該罰該罰!」說罷拿起桌上酒杯一飲而盡,對方對他視若無睹,他也不介懷,又逕自問道:「我瞧著你有些面熟!定是在哪裡見過……呵呵,不過一時想不起來了!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對方依然沉默,在他以為等不到答案時,那雙灰白的眼珠子居然轉動過來,注視著他,然後,冷得不帶一絲溫度的聲音回答他的問題:「飛簾。」
九鳴愣了許久,咧嘴笑了起來,一拍額頭:「對啊!飛簾!我記得了!」邊笑邊熱絡地搭過手去,用力拍打對方的肩膀,發覺這傢伙雖然看上去精瘦,但事實上卻肌肉紮實,充滿韌性。
姚諸忍不住好奇湊過頭來:「九鳴你與他是舊識?」
「這傢伙可太有趣了!」九鳴興致勃勃地說道,「一見面就把我的傳令妖兵給劈開兩半了!哈哈……」
姚諸聞言皺眉:「他把你的人給殺了,你竟然不予計較?!」
紅髮的妖怪笑得更加張狂:「沒能耐的傢伙多死幾個也沒差。哈哈,你說對吧?」
坐在他身邊的男人紋絲不動,也不伸手撥開搭在肩膀上的手臂,任得九鳴自鳴得意地招來侍女斟酒,又是叫又是笑地吵吵鬧鬧,低頭看了看對方不見半點酒溼的嘴唇,又鬧上了:「飛簾,你怎麼不喝酒?莫非是想喝天上仙酒?嗯,這還得等等!」
「不勞將軍費心。」
終於是有點回應了。九鳴自然是打蛇隨棍上的滑溜,馬上接茬:「這稱呼就生疏了!我們都是將軍,以後直呼其名便可!」
一邊的姚諸聽了,涼涼地冷哼一聲。
至於飛簾,依舊是不置可否。
惟有九鳴自得其樂,也不返身回自己桌去,湊在飛簾身邊愣是把所有的酒喝個精光,末了還非常稔熟地拍著對方的肩膀,半醉半醒地道:「你這傢伙真是不錯!明日我再找你喝酒!」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七元解厄之鳴翼見 (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七元解厄之鳴翼見 (上)
張揚跋扈、喜惡無常的旱妖九鳴,
生平最怕之事,便是無聊!
原想加入妖軍會有趣許多,
卻發現妖物群聚之地,一樣窮極無聊!
誰知冰冷漠然、不知變通的飛簾,
竟引起他無窮的好奇心──
無畏無懼,視九鳴如無物,
如此妖中異類,不好好探究一番豈不可惜!?
但當貪狼星君神威在前,飛簾的與眾不同,
是否值得自己拚上一切?
章節試閱
序
起先,他不過是想找些樂子。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中載,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於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他看到這卷書時不禁嗤鼻,對它們這種上古異獸居然就三行的形容,必定是撰寫此本的凡人不敢靠近,只能遠遠躲著稍微看那麼一眼,就想當然地寫下來。不過說得卻也不錯,他確有旱燥之能,只要他高興,眨眼間可枯乾大河,遍邑大旱。
但這樣又如何?看了凡人在旱魃肆虐之時,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慘狀,他再插一腳進去?未免太過無趣。
善惡之分,在凡人而言,不外乎...
起先,他不過是想找些樂子。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中載,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於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他看到這卷書時不禁嗤鼻,對它們這種上古異獸居然就三行的形容,必定是撰寫此本的凡人不敢靠近,只能遠遠躲著稍微看那麼一眼,就想當然地寫下來。不過說得卻也不錯,他確有旱燥之能,只要他高興,眨眼間可枯乾大河,遍邑大旱。
但這樣又如何?看了凡人在旱魃肆虐之時,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慘狀,他再插一腳進去?未免太過無趣。
善惡之分,在凡人而言,不外乎...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顧懿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4-17 ISBN/ISSN:978986296231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