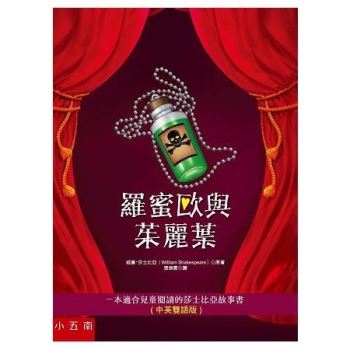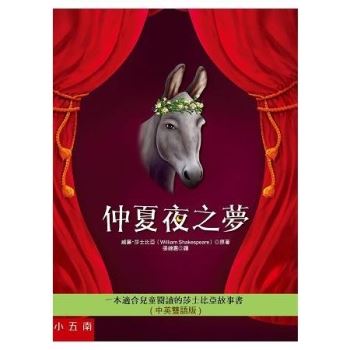一場連貫三十多年的惡夢,
一個執著三十多年的詛咒,
在追索線索的途中,
素問竟然莫名失蹤了!
張雪山死亡後附身對象不明,
而敵人這次的攻擊目標,
竟然是擁有神格的張玄?
馬靈樞與張玄合力應敵,
連神祇都想要的人偶,
到底隱藏了什麼祕密?
特別收錄《那一年的記憶》等番外,
素問和初九的糾纏就將步入結局!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天師執位III 十 人偶 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輕小說 |
$ 216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天師執位III 十 人偶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