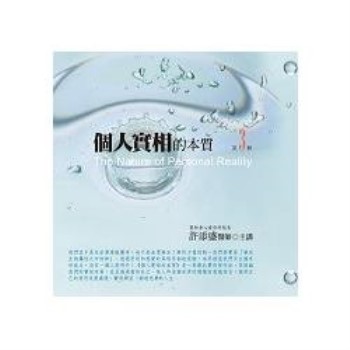一朝淪為階下囚,
張玄不改我行我素的本色,
他不在乎銀白與張正的背叛,
除了自家董事長的安危,
他更好奇傅燕文究竟跑哪去了?
鐘魁沒死,真假犀刃難辨,
聶行風抓住了真相的線索,
傅燕文終於焦慮起來。
然而就在事情步步明朗之際,
被囚困的張玄竟然死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天師執位III 12 心獄 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5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BL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