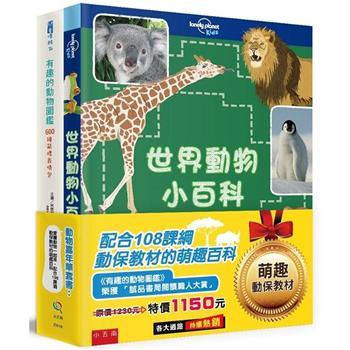第十一章
在銀白感受到異象之兆的同時,聶行風也覺察到了,此刻正是他跟傅燕文交手最激烈的時候,然而來自於天外的溫厚罡氣影響了他們,他的虎矩法器咆哮著閃到一邊,傅燕文的犀刃也被浪濤捲住,差點脫手而出,兩人從空中墜落,各自閃到巨浪的另一邊。
「張玄在哪裡!?」無視眼前咆哮的浪頭,聶行風沉聲喝道。
傅燕文漠視了他的怒氣,將犀刃橫在胸前,微笑道:「沒想到你居然找到了這裡,可惜晚了一步……」
海嘯突然衝他們湧來,打斷了傅燕文的話,他急忙運功抵擋風浪,聶行風則召喚虎神相助,就聽浪花飛濺中傅燕文大聲笑道:「他是你親手殺掉的,不是嗎?」
「如果你真這樣想,那為什麼不將你手中的贗品法器扔掉?」
面對聶行風的針鋒相對,傅燕文一愣,本能地握緊犀刃之柄,聶行風冷笑:「不放棄,是因為你不甘心承認自己的犀刃是假的,或者說哪怕是假的,你也要擁有,只因為它的名!」
「不是!」
「二十多年前電影院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認為這些可以瞞得過上蒼嗎?」無視傅燕文的暴烈反應,聶行風又接著說:「你折騰了這麼久,只能說這一切都是白費心機,我都想起來了,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同位神格,需要元神歸位,自始至終你跟我根本就是兩個人,要說有什麼連繫,最多萬年之前,我們算是同行而已。」
傅燕文不說話,跟聶行風相同的臉上不時浮現出黑色斑點,宛如潑墨般地暈開,他卻不自知,雙手握住兵刃,在海浪中呼呼直喘。
聶行風的一番話戳到了他的痛處,好像多年前的時光裡,他也對聶行風抱有如此同樣的嫉恨,他厭惡看到這張臉,但令人譏諷的是他卻不得不用對方的臉,因為他的容顏早在二十多年前的大火中就毀掉了……
上古洪荒,多的是惡獸妖類,殺伐之神當然不止一人,五帝之中都有他們認命的戰神,刑算一個,傅燕文也是其中一個,可惜相比於深受器重戰績赫赫的刑,傅燕文的存在就不起眼多了,於是他惡由心生,暗中挑起刑跟諸神的嫌隙,逼迫他遠走北海,因為北海一方是海神玄冥的疆土,兩強相對必有一場浩大征戰。
一切正如傅燕文所料的,至此玄冥消失,刑也不知去向,之後上古戰事逐漸平息,他也自封入瞑,直到妖獸再次出沒,才將他驚醒。
但那已是現代社會,所謂妖獸,也不過是一星半點的下等靈體,他不甘心歸於平淡,想重啟五帝法陣,回歸當年妖魅叢生的時空,可惜影劇院的那場大火粉碎了他的夢想,為了隱藏祕密,他只得再次封印自己的力量,直到現今。
在發現聶行風完全不記得前塵往事,又跟玄冥在一起後,傅燕文想到了這個一箭雙鵰的辦法,將聶行風引入魘夢中,讓他看清玄冥的真面目,從而自相殘殺,但事與願違,每次當他認為可以成功時,都會被各種變故打斷,最後五帝封印全部被破陣,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綁架張玄,做最後的賭博。
「我從很早之前就討厭你,」面對聶行風,他恨恨地道:「你這種偽善又自以為是的傢伙,根本不配稱神!」
「彼此彼此,為了私心而濫殺無辜的你也不配殺伐二字!」
「那就看看到最後誰可以留下來吧!」
話音未落,犀刃已在傅燕文的喝斥下向聶行風揮去,聶行風不躲不避,用意念捲起飛濺起的浪花,海浪剎那間化作一道透明長劍,跟犀刃撞到一起,兩強相撞,浪花被犀刃震得四下飛散,犀刃也向後盪去,任憑傅燕文怎麼揮斥都無法再令它移動半分。
這讓傅燕文驚異萬分,不甘心撒手撤刀,但他感覺得出犀刃在不斷排斥自己的神力,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不管是重傷初九,還是幾次與聶行風之戰,它都沒有過這樣強烈的反應。
不好的預兆慢慢向他襲來,看向聶行風,他突然後知後覺地想到了一件事——聶行風的神力恢復了,他的恢復就意味著張玄恢復,也等於說張玄沒有死,而這滔天巨浪正是海神肆虐導致的後果。
「你的法力是什麼時候恢復的?」他不甘心地問。
「這與法術恢復無關,犀刃殺不了我,你知道是為什麼?」
傅燕文沒問,但臉上露出明顯的疑惑,於是聶行風給了他答案,「犀刃殺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惡,鐘魁沒有死,是因為他不是惡,而並非你拿的是贗品。」
「那你的犀刃又是怎麼回事?又怎麼可以殺掉張玄?」
「那才是張玄變化出來混淆你判斷的贗品,也是他的法器索魂絲,」聶行風解釋:「我的確向他揮刀了,但只是將他的魂魄引到索魂絲上而已,法器自有靈性,會自動回到主人的身邊,我只是沒想到你會將他禁錮在北海。」
說到最後,聶行風的話語中透出揶揄,像是在笑他的愚蠢——北海是張玄的地盤,將他囚禁在這裡豈不是放虎歸山?
讀解到聶行風的暗示,傅燕文勃然大怒,他會將囚禁之地選在北海,只是想騙過聶行風的耳目,卻沒想到最終作繭自縛,一想到所有算計到頭來滿盤皆輸,他就愈發不能容忍這一事實,繼續催動意念妄圖將犀刃祭出。
聶行風嘴上說得輕鬆,但面對強敵,他絲毫不敢懈怠,眼見眼前風嘯浪湧,驚濤拍起千堆雪,然後在傅燕文的犀刃罡氣中匯成兩隻惡獸之形,惡獸咆哮,形影越來越清晰,與海嘯一起向他衝來。
聶行風不敢怠慢,凝神催動虎矩,頓時虎嘯穿越雪浪,龐大虎形躍起時在空間帶出恢弘金光,嘯聲將遠處雷聲都蓋了過去,彪悍之風一如上古般的清晰,彷彿眼前海嘯也好,神祇也罷,都不過是死物,隨時都會在虎矩之勢下化為齏粉。
從未有過的殺氣迎面襲來,即使同為殺伐之神,傅燕文也感到了膽怯,心神一恍,似乎看到了當年戰神刑在斬殺惡獸厲鬼時的彪悍氣勢,他嫉恨這樣的氣勢,但同時又妄圖擁有,也許從這一點來說,在一開始他就已經失敗了,他一直怕的、一直想戰勝的從來都不是聶行風,而是他自己,只是他不想面對而已。
祭起的惡獸在虎矩面前消散了,犀刃脫手而出,飛向海中,虎矩凌空一旋,像是要叼住,卻被突然衝來的煞氣逼開,但見半空中金光閃爍,晃亮了昏暗的一片天地,惡氣騰騰的龍形在空中打了個圈,張口咬住犀刃,又一個擺尾,向虎矩甩過,面對暴龍,神虎絲毫不懼,腰身微弓便要衝上前搶奪,聶行風慌忙搖手召喚——那是張玄家的龍神,一家人就不要打了。
感應到主人的呼喚,虎矩神器只好不情願地返身躍回他的身邊,卻依然衝著應龍吼聲不絕,作出無法任意征戰的不滿。
失去了犀刃,傅燕文臉如死灰,再看到天現龍神,他知道不好,催動咒語便想脫身,卻晚了一步,海浪接連打來,丈高般的水柱就像天然的法印結界,將他困在當中,他愈是運力,被反噬的氣力也愈大,如此反復幾次,他身上便已傷痕累累,兩條巨龍首尾相環將他圈住,令他再也動彈不得。
「你害我數次被困法陣,只困你這一次,算是便宜了。」
隨著笑謔聲,一道青色身影從遠處踱來,兩旁巨浪滔天,卻沒有半點水滴沾上他的衣襟,浪花每每靠近,便自動退下了,透露出不敢冒犯之態,於是那人便輕鬆走進了法陣中,一直走到聶行風面前。
「張玄。」
看著他的靠近,聶行風鬆了口氣,雖然眼前玄冥的海神氣勢太重,跟他熟悉的情人格格不入,但完全不降低自己對他的思念,一路趕來時的緊張之心落下,不見回應,他又再次叫道:「張玄。」
玄冥抬起了手,感受到自他身上的戾氣,虎矩神器仰頭發出怒吼,聶行風慌忙攔住牠,玄冥卻沒介意,隨口道:「你養的這隻有點蠢。」
聶行風一哂,不知該如何回覆,就見玄冥低頭看看自己的手掌,藍眸又掃向他,說:「你好像還欠我一巴掌?」
怔了一下聶行風才想起當初在魘夢中自己一時情急曾打過張玄一巴掌,被這樣問就代表他是在記仇了,不由得笑了,只要張玄沒事,別說一巴掌,就算一頓打,他也不會在意。
玄冥的手揚了起來,就在聶行風以為他會甩過來時,響亮的巴掌聲響起,重重打在傅燕文的臉上,並伴隨著輕描淡寫的嗓音。
「我說過那一巴掌我一定會打回來的,身為五帝座下侍從,你該知道我可是很記仇的。」
傅燕文是五帝命定戰神,平生殺魔無數,個性更是高傲,這一巴掌比打傷他更讓他難以接受,聽玄冥嘲諷他只是侍從,他更難嚥下這口氣,揮手以念力祭起風浪,浪花化為尖刀,向玄冥衝來。
玄冥雙手背在身後,視那攻擊為無物,聶行風見他輕敵,想上前相助,卻沒想到尖刀衝到半途時便消散了形影,傅燕文抓住手臂跟臉頰不斷撕扯,發出怪聲尖叫。
「這是怎麼回事?」
聶行風的問話被蓋住了,那邊傅燕文仰頭怒瞪過來,大聲吼道:「你對我做了什麼法術?身為神明,你居然用毒……」
聶行風看過去,就見傅燕文臉上的黑色斑點更多,並且飛快地向周圍擴散,想必那黑斑讓他很痛,整張臉都扭曲起來,無形中化回了他自己原有的模樣,看似堂堂正正的臉龐,只是半邊臉頰滿是疤痕,該是當年烈火焚燒導致的。
「對付你這種低等侍從,焉用我親自動手?」看著傅燕文痛苦,玄冥眼中露出愉悅的光彩,慢悠悠地說:「當初你利用銀白兄弟藉尾戒算計我的時候,沒想到自己也會嘗到被劇毒咬噬的滋味吧?」
「原來……原來是那蛇妖!」
「怪只怪你從來看不上那類妖物,當銀白的血噴到你身上時,你沒想到有一天它會變成穿腸毒藥吧?」
聽著慢悠悠的解釋,傅燕文恍然大悟,難怪每次他對銀白出手時,銀白都會吐血,他只當是妖類法力低下,卻不料早在一開始,這一切就在銀白的算計之中。
「你從強迫銀白為你做事起就有了事後殺掉他的念頭,想必他也知道,所以抱了同歸於盡的想法,怪只怪你眼高於頂,根本沒把低等妖物看在眼中……」
「玄冥,我從未對你出過手,你為何傷我!?」
傅燕文此刻被蛇毒折磨得痛不欲生,但更讓他恐懼的是玄冥睚眥必報的個性,忍著痛努力尋找藉口為自己脫罪,以免結局更淒慘。
「你是沒有直接對我動手,但每次引我進誅仙降魔陣的也是你。」
「那是身為戰神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就像當年刑殺你,也是因為你作惡……啊!」
浪濤在傅燕文的身前炸開,飛濺的浪花宛如一柄柄利刃,一齊扎進他身上,他卻不怕,咬著牙大笑道:「我說中你的心事了嗎?若你不作惡,為何人人得而誅之?」
玄冥面沉似水,手腕上的印記光芒隱現,怕他中傅燕文的激將,再度肆虐北方,聶行風急忙拉住他的手,示意他冷靜,玄冥扯了一下沒扯開,便由著他了,心裡卻在想要不是他自封神力,哪容一個低等偏神在這裡撒野,不過這樣也不錯,因為傅燕文的出現,解開了他一直以來弒師的心結,只這一點,就足以讓他曾經遭受的痛苦不值一提了。
或許為師父改命原本就是不容於天地的,這也算是對他的懲戒吧。
想到這裡,竟然心平了許多,反握住聶行風的手,對在水中痛苦掙扎的人微笑道:「在所有挑釁我的人當中,你是最沒用的一個,只不過你沾了點時運而已。」
傅燕文怒視他,玄冥坦然接受了他的憤怒,繼續道:「從來都是不普通的人想當普通人,只有普通到完全無特色的人才會竭盡全力爭做人上人,你一心想除掉同類,做唯一的戰神,光是這個念頭就證明你永遠只能是頂了個神祇頭銜的侍從而已。」
他說對了!他全部都說對了!
傅燕文發現自己最不甘心面對的事現在就在隨著張玄的侃侃而談而被剖析出來,他最恐懼的不是聶行風有多出色,而是自己的存在有多不重要,不重要就代表著他隨時會被捨棄,這才是他最無法接受的事實。
原來他沒有輸給任何人,他輸給的是他自己。
無關對手的身分有多尊崇,實力有多強大,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連自己這第一關都沒能邁得過去。
那一句句嘲諷宛如鋼針扎上心頭,傅燕文不由得顫慄了起來,他不想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得不承認——這才是最令人絕望的,他感覺自己被蔑視了,這是自然,北海玄冥又怎麼會看得上他這種不起眼的戰神?玄冥做事一向都是這樣的肆無忌憚,張揚得讓他想用盡一切辦法去毀滅這個人,他幾乎做到了,在無數次誅仙降魔陣中,看著玄冥屢屢遭遇險情,那時候的他心裡充滿了無法言說的喜悅。
其實玄冥跟他之間並沒有矛盾,如果說他對付聶行風是抱著除掉對手的想法,那玄冥在他眼中只是個遷怒的藉口而已,他崇拜玄冥,因為玄冥的強大,強大到讓他心生嫉妒的程度,如果他不是多花心思去對付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的話,也許現在一切結果都將改變,但偏偏當時他鬼迷心竅了,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只想著要毀滅對方,只因為玄冥的存在太美好太強大,太高不可攀,只因為他從來都瞧不上自己。
就連在被選擇上,他都輸給了聶行風,他無法容忍這個事實,所以想盡一切辦法讓他們相互懷疑並自相殘殺,他要的結果從來都不是死亡,而是看到對方痛不欲生的面孔,從而滿足他的快感。
景仰的終極不是愛慕,而是毀滅,這就是他對玄冥所抱有的心態,這種想法扭曲得連他自己都無法理解,他只知道自己一直是這樣操作的——既然你不屑於我的存在,那麼我也不屑於你的生命!
可是最後他還是失敗了,他找不到失敗的原因,所以他不肯承認這個結果,更惱怒於玄冥對他的蔑視,這一刻他忘了雙方能力的懸殊,再次大叫著站了起來,雙手做出同歸於盡的祭天法訣——只要可以毀了對方,他毫不介意連自己也一起毀掉。
憤怒跟蛇毒導致的痛苦讓傅燕文的表情扭曲變形,他的面部肌肉開始痙攣,宛如困獸猶鬥般的發出低吼,面對他的垂死掙扎,玄冥根本沒在意,負著手長身玉立,任憑他去做,誰知就在傅燕文的法訣做到一半時,自上空傳來的幾束微光攔住了他的行動——不知何時天已放晴,烏雲散開,天際的五彩雲霞籠罩而來,在祥和光芒下,連海浪也平靜了許多,浪頭逐漸低下去,不復方才咆哮厲氣。
霞光繼續飄散,與海面連成一線,彷彿五彩帷帳從天空降下,難得一見的異景,玄冥皺起了眉,聶行風也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熟悉的天道罡氣散開,讓他們明白了即將出現的是何方神聖。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天師執位 第三部(12):心獄(下)(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BL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師執位 第三部(12):心獄(下)(完)
步步算計,處心積慮,
身為式神甚至背叛主人,
卻沒想仍是無法對抗傅燕文。
與死去的張玄一同被拋入北海,
銀白只怨自己無法保護最重要的弟弟。
五帝復甦,北海之神現世,
上古時代屬於神祇的一切,
也許終將畫上句點。
那麼刑與玄冥、張玄與聶行風呢?
張玄只知道董事長屬於他,
哪怕是神也別想奪走他的招財貓!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在銀白感受到異象之兆的同時,聶行風也覺察到了,此刻正是他跟傅燕文交手最激烈的時候,然而來自於天外的溫厚罡氣影響了他們,他的虎矩法器咆哮著閃到一邊,傅燕文的犀刃也被浪濤捲住,差點脫手而出,兩人從空中墜落,各自閃到巨浪的另一邊。
「張玄在哪裡!?」無視眼前咆哮的浪頭,聶行風沉聲喝道。
傅燕文漠視了他的怒氣,將犀刃橫在胸前,微笑道:「沒想到你居然找到了這裡,可惜晚了一步……」
海嘯突然衝他們湧來,打斷了傅燕文的話,他急忙運功抵擋風浪,聶行風則召喚虎神相助,就聽浪花飛濺中傅燕文大聲笑道:「他是你親...
在銀白感受到異象之兆的同時,聶行風也覺察到了,此刻正是他跟傅燕文交手最激烈的時候,然而來自於天外的溫厚罡氣影響了他們,他的虎矩法器咆哮著閃到一邊,傅燕文的犀刃也被浪濤捲住,差點脫手而出,兩人從空中墜落,各自閃到巨浪的另一邊。
「張玄在哪裡!?」無視眼前咆哮的浪頭,聶行風沉聲喝道。
傅燕文漠視了他的怒氣,將犀刃橫在胸前,微笑道:「沒想到你居然找到了這裡,可惜晚了一步……」
海嘯突然衝他們湧來,打斷了傅燕文的話,他急忙運功抵擋風浪,聶行風則召喚虎神相助,就聽浪花飛濺中傅燕文大聲笑道:「他是你親...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樊落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7-02 ISBN/ISSN:978986296623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