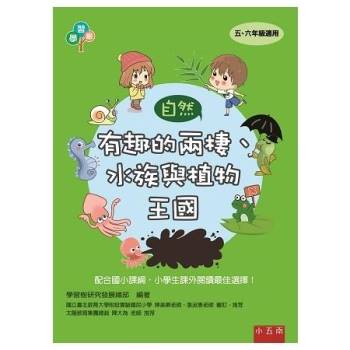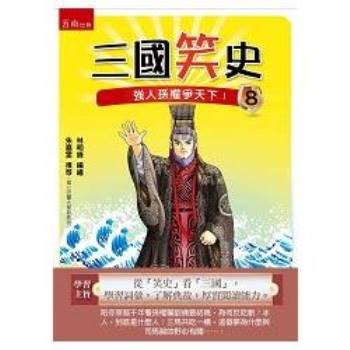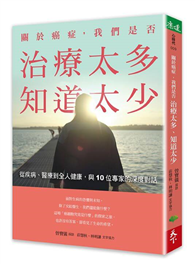34、第三十四章 百獸奔逃
長安在巨山部落裡住了一個多月,可謂是一件正經事都沒幹過。
部落裡什麼都有,肉、糧食、果子,甚至連小時候他當成奢侈品吃的芽糖,在這裡都好像沙土一樣不值錢,長安只是懷念那個味道,他這麼大的人了,對甜膩膩的糖興趣也很有限,吃著吃著便吃不下了,剩下的全進了小奴隸路達的肚子。
還有華沂接二連三地送來的東西,長安雖然糟蹋好東西的本事一流,卻並不是不知好歹——──起碼他知道華沂以前為了貝塔賣過命。
華沂說過,等到天災人禍,就是需要他的時候,可不就是現在麼?
長安總能在不合時宜的時候記得不合時宜的話。
人們點起火把,一開始雖然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卻也並不怎麼慌張,北方部落的生活並沒有那麼平靜。亞獸拿著武器,將女人和孩子們圍在中間,最外圈是獸人武士,至於奴隸們,卻是沒人管的,甚至有獸人驅趕著他們去引開那些過路的野獸們的注意。
長安本想把路達扔進女人們負責照看著的小崽子們中間,見了這情景,目光閃了閃,一低頭,正好對上那路達的目光。
路達雖然不說話,黑乎乎的小手卻緊緊地攥著他的衣服。
他們兩人雖然共處一室,相互卻都當對方不存在,十天半月也說不了兩句話。以致至於長安現在看著他,依然覺得有點陌生。他對路達說道:「不怕死,你就跟著我。」
路達就用行動表示了他不怕死——──死不撒手地當了他的跟屁蟲。
跑過去的,先是狼、狐一類狡猾的東西,隨後是一些小動物,再之後便是一些大型猛獸,所有的動物都慌不擇路地往前跑,唯恐被什麼東西追上似的。
百獸狂奔,相互踩踏,有時撞在一起,還有一些莽撞地衝沖進人群,被當即斬殺的,隨著越來越多的野獸從林子中跑出來,小火堆威懾力有限,很快就會被四散的野獸們衝垮,場面漸漸亂了起來。
長安抬頭看見了站在最高處的華沂,而同他一起的索萊木正在指揮眾人將巨大的油缸與柴禾抬過來,往部落靠近林子的那一邊運,長安久居深山,一眼就明白,他這是要支起一個大的火堆。
可這柴禾並不好擺放,在大火沒有著起來之前,好幾個的獸人戰士守在那裡,還是捉襟見肘,時常被跑紅了眼的猛獸衝沖亂柴禾堆,或者踩滅沒來得及著大的火,其他人要保護無法戰鬥的人,也來不及支援。
索萊木要叫猛獸們避開部落,意在擺上幾個猛獸無法跨越的大火堆,相互呼應,成一道火牆。他跟長安想的得一樣,能讓百獸奔逃的,必然是更棘手的東西,他們必須先做好準備。
就在幾個守在前面的獸人們手忙腳亂的時候,突然,一把一丈多長的大馬刀橫插了進來,一刀便挑飛了一頭巨虎,巨虎吃痛,狂吼一聲翻滾落地,爬起來惡狠狠地瞪向這個膽敢擋路的人,長安把路達往身後一放,低聲道:「幫他們點火,不用怕,沒有什麼能從這過去。」
路達看著他的刀,眼睛裡第一次冒出毫不掩飾的豔羨,然後他一低頭,從長安身邊跑了出去,爹不疼娘不愛地加入到了搬運柴與油的成年人們中,賣力地幹起活來。
大老虎直視著長安的眼睛,似乎感覺到了對手的強大,牠它站在那,不少豺狗之類的小動物也忍不住嗚嗚叫著停下了腳步,長安雙手握住刀柄,刀刃穩穩當當地懸在半空中,獵獵的大風中,他的手穩得像鐵鉗,連一絲抖動也沒有。
第二波來支援的獸人們趕到的時候,便見著這邊的對峙,一邊是衣襟淩凌亂的少年,一邊是巨虎和一干虎視眈眈的食肉畜生,雙方實力差距顯著,然而竟然就這麼僵持住了,誰也不肯先動一下,簡直成了一番奇景。
長安往那大火堆前面大馬金刀地這一站,使他兩邊的防禦壓力也驟然減輕,有人認出他來,大聲道:「你!你就是那天用一把烹肉刀,宰了那個落跑奴隸的長安兄弟!」
長安沒說話,夜風掀起他的頭髮,夜色掩蓋了他異常蒼白的臉色,也一同掩蓋了他眼角唇心的那一點不合時宜的豔色,他的眼睛被大風吹地半瞇眯起來,上眼皮清晰而精巧地勾勒出出了他的眼形,鼻梁樑挺直,額角上沾了塵土,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尊經年坐落在那裡的石像,用手一抹,就露出厚厚的塵土下面、那凝滯在歲月深處的清秀眉目來。
說話的獸人守衛從腰間解下皮囊,不管不顧地往自己嘴裡灌了幾口,吐出來的氣仿佛彷彿帶了火星一樣灼熱,他在一片混亂中扯著嗓子大聲道:「阿蘭姑娘還在整天跟她阿爹吵吵著要嫁給你吶哪!說真的兄弟,我不服氣啊,我也有的是力氣,要是當時我在那裡,我不用拿女人的餐刀,赤手空拳便能輕而易舉地就宰了那個傢伙,可惜我阿媽沒給我生出一張漂亮的小白臉,不討姑娘喜歡啊,哈哈哈!」
長安終於牽扯著嘴角,在這漢子粗鄙拙劣的幾句笑話裡,露出了一點吝嗇的笑容來,就像慘白的石像瞬間活了,人們火把的微光投射到他的眼睛裡,一?剎那,便是熠熠生輝。
這時,地面再一次震動了起來,依然並不劇烈,卻有種非常古怪的味道淡淡地散開,有一點刺鼻,又有一點臭。
可是不等長安細想,大老虎卻突然狂躁了起來,包括在那裡越聚越多的野獸,這種味道似乎刺激了牠它們,叫牠它們意識到,跟面前這些人比起來,身後的東西才是更可怕的。
自然始終無法違抗,萬獸為之驅使。
豺狗們齜呲出牙,一個接一個地撲了上來,周遭雷聲依然刺耳,遠處卻又響起淒厲的狼嚎。
長安直到豺狗已經撲到他近前才動手,他的下半身一動不動,似乎在極力節省力氣,一刀極快地劃過——──只有一刀。
三道血霧同時噴出來,他一刀就劃開了三條豺狗的脖子。
獸人守衛們同時化成了獸形,在火堆前面站了整整齊齊的一排,看起來幾乎叫人膽寒了,長安一個人躋身於百獸之中,分外不合群。
他依然只守一個地方,有東西撲過來,他就給對方一刀。
所有死於刀口下的動物全都是咽喉上一個豁口,連位置幾乎都一模一樣。
不少獸人用咆哮給他叫好,可時間稍長,長安的手就變得不再那麼穩了,甚至微微發起抖來。那種怪味道似乎越來越重,別人沒覺得怎樣,他卻被刺激得氣管生疼,很快,嘴裡就有了淡淡的血味,連帶著胸口肩膀都幾乎快要沒了感覺。
天氣始終是悶熱,長安額前滾下汗珠,他抬手抹了一把,以防滴進眼睛,腳下略微踉蹌了起來。
這時候,一個年輕的獸人戰士被一頭虎咬中了肩膀,巨獸和老虎滾成了一團,搏起命來,而空隙中,一頭狡猾的豺狗趁機跳了進來,路達正好放下一大捆柴禾,還沒來得及直起腰來。豺狗形容猥瑣,強壯的成年男人能把牠它一腳踢死,可牠它咬死路達這樣的小東西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幸而長安的刀長,他回身將馬刀橫掃出去,刀似乎送得急了,將空中向小孩撲過去的豺狗一下子砍成了兩截,他自己也沒了收刀的力氣,被帶出去兩三步。
不知道哪裡躲著的一條狼相準准了這個機會,就在他來不及收刀背過身去的眨眼間,大狼猛地踩著其他動物的屍體撲了上來,一下躥上了長安的馬刀上,牠它體型本就很大,這一蹬的力量更是驚人,足足有幾百斤,長安的刀被這樣一壓,立刻抬不起來了。
大狼俯衝向下,尖銳的爪子一把抓進了長安的肩膀,輕易地便刺破了他的皮肉,將他撲到了地上,一氣呵成地亮出了獠牙——──只要一口,牠它就能咬斷那脆弱的脖子。
下一刻,大狼被不知哪裡伸出來的刀柄狠狠一撞,這一下險些撞碎了狼的下頷頜,牠它慘呼一聲,爪子瞬間收緊,側過了脖子。
就在牠它一側頭的這個縫隙裡,一把食指長、去了刀刃便幾乎沒有什麼的小刀狠狠地劃開了牠它的脖子,刀刃不夠長,那隻只拿刀的手便狠狠地順著傷口掏了進去,大狼玩了命地掙扎,那隻只要命的手卻不依不饒,青筋都暴了出來,直到血肉的人手探進了狼頸兩寸深,大狼才算死得透透了。
身後的大火堆終於點了起來,火星沖天,發出劈啪的警告,很快連成了一片火牆,只留下了一條供一個人穿過的小過道,不要命的往前撲的動物們終於屈從了本能,嗚嗚地叫著,夾著尾巴往後退去。
長安喘著粗氣將大狼的屍體踹到一邊,把自己的馬刀拖出來,他半身都是血,狼血,還有他自己的血,順著他散亂的頭髮一直流進了他的嘴裡,他一偏頭,「呸」一聲吐了出來,心裡不痛快地想道:『「我學藝不精。』」
然後他被一個艱難地從獸堆裡擠出來的人給捉住了,瘦高的山溪大驚小怪地看著他:「我找了你半天!怎麼弄成這副幅樣子?快快,跟我走。」
他提高聲音,大聲道:「所有人都撤到火堆後面,斷後的人通過之後,把過道的油點了,往裡添柴!受傷了的去找醫師!」
長安低低地咳嗽了兩聲,一邊生嚼著草藥,一邊還沒忘了他的小奴隸,他拎起傻站在那裡的路達的後頸,拖著他往火堆後面走去。
索萊木正坐鎮火堆中間,有條不紊地指揮著人們加柴加油,大大小小的火堆夠成了一條堅固厚實的防線,猛獸們闖了幾次不能通過,終於不得不繞開這一片部落所在之地,人們得以喘息片刻。
然而索萊木的表情卻不見輕鬆,反而越來越凝重。
長安逕自向他走過去,打算跟這位什麼都知道的人說說那股怪味。
「我剛才聞到……」
可是他這五個字還沒出口,突然被人提著腰帶一把給抓了過去,華沂按住長安,神色詭異地看著他那一身的血,問道:「這是怎麼弄的?你有勁留著點用不行麼?硬茬子還在後面呢……唉,這倒楣孩子,一時看不住你就給我傷成這樣。」
「只有肩膀讓狼抓了一把,」長安飛快地搪塞了他一句,又轉向索萊木道,「我剛才聞到那股味,像
是……」
華沂見他仍在鹹吃蘿蔔淡操心,眼角簡直要抽起筋來,一低頭瞧見長安肩膀上狼爪抓出來的翻開的皮肉,心裡詭異地冒出了一點火氣,好在當著人,他還知道克制,當下只是抓著長安的腰帶,把他雙腳離地地給拎了起來,口中歎道:「行啦,你快點閉嘴吧,他吃過的鹽比你走過的路都多,難道不比你明白?跟我走!給你的鐵甲呢?都讓你墊桌腳去啦?」
長安見他絲毫也不著急、分明成竹在胸的模樣,也不明原因地跟著放心下來,說道:「嫌沉。」
華沂七竅生煙地看了他一眼,斜睨著他的馬刀罵道:「哦,幾塊鐵片你嫌沉,你那劈爛柴的破砍刀一天到晚地抱著,就不嫌沉啦?」
長安被狼抓了一爪子,本就心虛著自己學藝不精,聞言更是頗為愧疚,老老實實地聽著,沒反駁,暗自決定以後要更加努力才行。
華沂見慣了大場面,此刻看著遠處咆哮奔走的百獸,竟然還有閒暇搖頭晃腦地歎道:「洛桐當首領的時候,風調雨順,屁事沒有,傳到我手裡沒有兩個月,攪和合出了多少么蛾子,莫非是我命硬剋克自己的部落?可真是……」
長安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我師父說過,你這樣的就叫掃把星!」
華沂:「……」
他低頭看了一眼這血葫蘆似的少年,終於咬牙切齒地用力在他額頭上按了一下:「你快給我閉嘴吧,死兔崽子!」
醫師那裡排成了長隊,華沂仗著首領特權直接插了隊進去,輕拿輕放地把長安按在了阿葉面前的小凳子上,半跪下來撕開他肩上的衣服,對她說道:「你給他看看傷口。」
除了阿葉,其他的醫師都是糙老爺們兒,華沂本能地怕他們粗手粗腳地弄疼了長安,但他看著長安坐在那裡讓阿葉清洗傷口,依然不肯鬆開他那把同樣血淋淋的大刀的模樣,心裡忍不住嫌棄自己是多此一舉。
難道這傢伙不是個糙漢子麼?
華沂瞧著長安幾次三番企圖把水罐拿過來、直接要往肩膀上澆的不耐煩樣,心裡恨恨地想道:姑娘細細緻致地伺候他,他還嫌人家手腳慢了!這不知好歹賴的小牲口。
可是即使是個小牲口,華沂也依然忍不住憐惜他,方才抓在手裡,他隔著衣服能摸到長安的骨肉。華沂總覺得那身骨肉長得似乎和別人不一樣。傷口在別人身上,只要不死,就不顯得有多淒慘,可在長安身上,華沂就感覺自己好像也跟著他一起疼了起來。
他不自在地動了動自己略顯僵硬的肩膀,齜呲牙咧嘴,好像那也多了幾道深得見骨的大口子。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獸叢之刀(中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BL |
$ 216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獸叢之刀(中卷)
自深淵的惡魔地火帶來了變動,
也盪起了華沂內心異樣的騷動,
對於長安──這個他一向視若兄弟的男子,
這份悸動是否也能同樣傳達到對方心上!?
在這烽火連天的亂世,
生存是如此凶險,
競爭是如此激烈。
除了鮫人,更有來自極北之鳥人。
是敵對?抑或是攜手合作?
考驗著華沂與長安。
為了未來的新生,
他們只好遠離,
等待寒冬過後萌芽的春天。
章節試閱
34、第三十四章 百獸奔逃
長安在巨山部落裡住了一個多月,可謂是一件正經事都沒幹過。
部落裡什麼都有,肉、糧食、果子,甚至連小時候他當成奢侈品吃的芽糖,在這裡都好像沙土一樣不值錢,長安只是懷念那個味道,他這麼大的人了,對甜膩膩的糖興趣也很有限,吃著吃著便吃不下了,剩下的全進了小奴隸路達的肚子。
還有華沂接二連三地送來的東西,長安雖然糟蹋好東西的本事一流,卻並不是不知好歹——──起碼他知道華沂以前為了貝塔賣過命。
華沂說過,等到天災人禍,就是需要他的時候,可不就是現在麼?
長安總能在不合時宜的時候記得不合...
長安在巨山部落裡住了一個多月,可謂是一件正經事都沒幹過。
部落裡什麼都有,肉、糧食、果子,甚至連小時候他當成奢侈品吃的芽糖,在這裡都好像沙土一樣不值錢,長安只是懷念那個味道,他這麼大的人了,對甜膩膩的糖興趣也很有限,吃著吃著便吃不下了,剩下的全進了小奴隸路達的肚子。
還有華沂接二連三地送來的東西,長安雖然糟蹋好東西的本事一流,卻並不是不知好歹——──起碼他知道華沂以前為了貝塔賣過命。
華沂說過,等到天災人禍,就是需要他的時候,可不就是現在麼?
長安總能在不合時宜的時候記得不合...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Priest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13 ISBN/ISSN:978986296647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