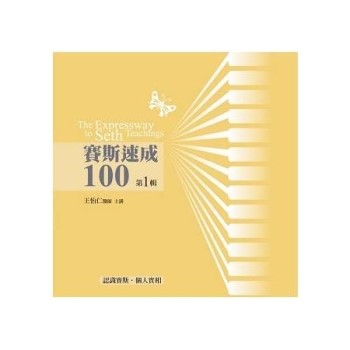過去流離顛沛的零星部族,
成了如今城牆下的千軍萬馬。
當年浴血出逃的半大小子,
如今竟是重鎮城主與稱霸一方的王!
然而,
稱王的華沂卻要對出生入死的長老下手,
最忠心的徒弟將成最大的叛徒!?
長安更將面臨瀕死的大劫!?
隱身這一切陰謀之後的黑手竟是──他!!
人心涼薄,孰敵孰友,
在權謀操弄下,
曾經以命相交的情分竟是消融殆盡。
當一切喧囂落盡,
你我是否還能回到那與世無爭的人間四月?
《獸叢之刀》最終回──
一生的宿敵,終是要一決勝負你死我活!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獸叢之刀 下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中文書 |
$ 216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