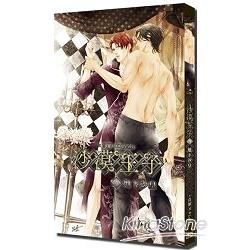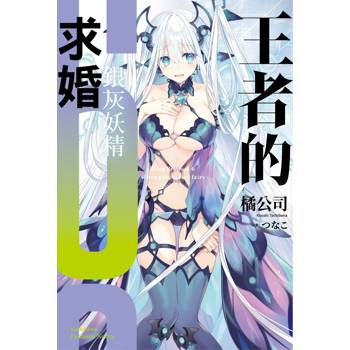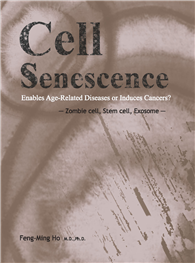祕密拍賣會尚未展開,
一連串的陰影就已來襲。
周旋在眾多收藏家之間,
吳名世扮演的春老師如履薄冰。
地下沙皇伊凡諾夫身分成謎,
費薩爾的存在嚴重影響他的判斷。
祕密拍賣會交易的商品是祕密,
獵人與獵物的分際已然模糊。
肉體交纏、勾心鬥角,
究竟是誰征服了誰?
當所有疑點都指向費薩爾時,
吳名世又該如何抉擇?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沙漠王子(四)地下沙皇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