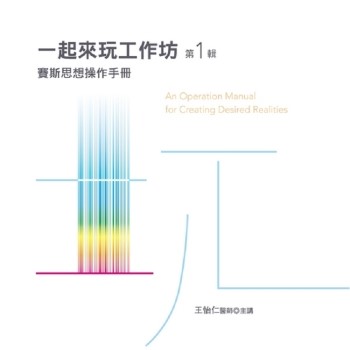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如果你真的這麼想要男人,就讓我來當你的對象吧」!?
因為母親去世而改由親生父親扶養的瑞樹,
進入了完全陌生的異國--英國的住宿學校就讀。
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名男子。
這男子就是父親再婚對象的孩子,
受學生們景仰的繼兄--阿爾弗雷特。
但因為和很多男性發生關係、引發許多問題的亡母的關係,
身為她孩子的瑞樹遭到冷淡的對待。
要好好加油,不能輕易放棄!
每天都很有精神的瑞樹慢慢吸引了阿爾弗雷特的目光,
但在某一天下午,他卻看到了瑞樹全身赤裸地侍奉男人!?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即使這份戀情有罪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8 |
二手中文書 |
$ 211 |
BL |
$ 216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