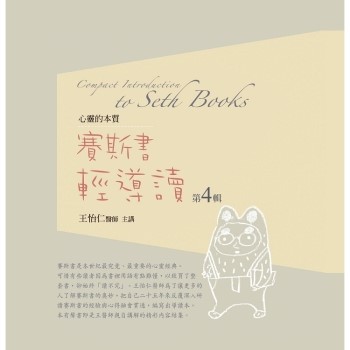第一章
江入畫站在家門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二樓書房的窗開著,能把人耳朵震聾的爭吵聲傳出來,他面無表情地從口袋中摸出一副橡膠耳塞塞到耳朵裡,手插著口袋,晃晃悠悠地進了家門。
「張媽,江文川又在和人吵架?」
張媽苦笑了聲:「江先生要借錢。」
江入畫點了點頭便上了樓,路過書房的時候冷著面孔瞥了一眼裡頭,就徑直地回了房間鎖上門,繼續畫早上沒畫完的一幅畫。
外頭傳來東西被砸碎的聲音,緊接著是撞門,估摸著是江文川死活借不到錢,只好把人給趕走了。
江入畫像是什麼也沒聽到一般耐心地動著筆,筆尖下漸漸出現一團團胡亂組合的色塊。
江文川是個老賭鬼,以前江家還有點錢叫他風風光光的賭幾把,然而現在他恐怕連自己的兒子也養不起了。江入畫大學剛畢業,還沒有找到工作,只得窩在小房間裡任由自己的耳朵遭受摧殘,冷眼看自己的爹藉著江家僅剩無幾的那點名聲東拼西湊地借錢,只為了在賭場上風流快活。
快七點的時候房門被敲響了,江入畫拿掉了耳塞,起身開門,是張媽上來送飯:「晚上又來了個客人,江先生去接待了,小江你先把飯吃了吧。」
「這回兒有什麼客人?」江入畫挑了挑眉,「難道是來討債的?」
「哎──」張媽的話還沒說出口,隔壁書房忽然傳來能把人耳朵震聾的怒吼:「你還有沒有良心!悖時砍腦殼兒的!改了姓換了名就忘記是誰給你錢把你養大的是不是?!」
江入畫想也沒想就拍著桌子學著樣吼回去道:「你他媽給我閉嘴!!我在畫畫!!」
這幾乎已經是他的習慣,只要到了晚上江文川再把人帶回家吵,他就必須也跟著喊兩句,殺殺他老子的銳氣。
「……小江你瞎起什麼勁。」張媽給嚇了一跳,連忙伸手去捂他的嘴,「看江先生那樣子這個客人挺要緊,你別拆他的臺,啊?」
「能有多要緊?會借他錢的話我把畫板吃下去。」江入畫哼了一聲,道,「妳那麼擔心,不會是高利貸吧?」
「那倒不是。聽起來像是你們江家的親戚。看打扮不太熟悉,像是個年輕的大老爺。江先生說這次多半要靠他了。」張媽低頭擺弄碗筷,沒有看到對面的人忽然挺直了背脊,又補充說道,「好像是姓顧。」
江入畫的手指動了動,連忙問道:「是不是叫顧碎?」
「這我就不知道了,依我說,你也別太多管這些個破事兒,趁早把工作找好了要緊,我估計你也不想一直待在這兒,況且指不定以後你妹妹還要靠你來照顧。」
江入畫悶悶地點了點頭,有些煩惱的把頭髮抓得亂翹。
張媽給他孩子氣的舉動逗笑了:「我說你,成天待在家裡學點真本事也就罷了,老是畫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早點收收心吧。」
江入畫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便把張媽送出了門,假裝淡然自若地關上了門,門一闔上,他的臉色就變了。
顧碎來了!
他猛地拿頭撞了撞書櫃的門,接著握著拳敲了敲胸口,想把那顆躁動不已的心按得平靜一點,腦子裡頭卻是一片混沌。
顧碎來了!
江入畫猛地吸了一口氣抬起頭,臉上竟然帶著不知名的紅暈:
我男人來了。
這個詭異的念頭一浮現就被他按了回去,心裡連罵自己恬不知恥。
接著他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房門拉開了一條窄得幾乎看不見的縫兒,趴在地上隔著門縫偷看外面的動靜。
過了將近一刻鐘,書房的門打開了,江入畫從門縫裡看見一雙皺巴巴的拖鞋走出來,後面跟著一雙乾凈得像鏡面一般的皮鞋。
他的心猛地一跳,彷彿一股血湧到了腦門。
「你真的不考慮一下?我的小顧大老爺,」江文川的語調浮誇得令人生厭,卻是不難聽出他已將冷靜了下來,「你當時在法國一擲千金買下一塊破石頭的時候可是出手闊綽得很啊。」
顧碎似乎答應了句什麼,只是他的聲音很輕,江入畫聽得不大真切。
江文川嗤笑了一聲轉身進了書房,用力地碰上了門。
黑皮靴沒有什麼遲鈍,不緊不緩地向樓梯走來,經過江入畫房門的時候忽然頓了一頓。
江入畫猛地瞪大了眼睛,那***金呈***油瓦亮的皮鞋離自己的臉很近,中間就隔著一扇薄薄的門,讓他硬逼著自己才克制住拉開門衝出去把嘴唇貼在上面的欲望。
可惜它只停留了不超過五秒的時間便徐徐地離開,不然江入畫就要懷疑對方發現自己在偷聽了。
一陣細碎的腳步聲後,外面徹底的安靜了,過了一會大門最後的插銷被插上,便再也沒有一點聲音。
顧碎終於徹底的走了。
江入畫狼狽地從地上爬了起來,鎖門的動作連做了三次才把門鎖上。
他吸了吸鼻子,像是有些委屈,卻說不出自己委屈在了哪裡,只得把自己的頭髮抓得更亂來掩飾自己的心慌,接著他打開書櫃,解開了防塵的白紗。
書櫃裡裝滿了畫,若是張媽看到了這些,就會明白江入畫一天到晚把自己埋在房間裡幹什麼了。
最外面的是一幅肖像畫,畫上的男人有著油亮的烏髮和灰色的眼睛,他靜靜地看著江入畫,刀鋒般的薄唇微啟著,像是隨時會對著他說出愛語。
江入畫痴痴地看了半晌,隔空給了「它」一個飛吻,便用畫框把它裝了起來,接著用還沒畫完的抽象畫遮住了那帥得難以言喻的肖像。
書櫃裡幾十幅畫全是這模樣,雜亂的色塊,凌亂的線條,深紅漆黑下藏得都是這樣一張俊美的臉。
江入畫抱著新作滿足地笑了笑,背靠著門就睡著了。那裡彷彿還留著顧碎身上的味道,這讓江入畫既高興,又忍不住耷拉下了嘴角。
──顧碎是他心尖尖上的人,只是像那些畫一樣,誰也不能看到。
永遠也不能看到。
不知道多久以後江入畫被砸門聲吵醒了。他捂著頭從地上爬起來,清了清嗓子,喉嚨痛得要命。
感冒了……江入畫無奈地歎了口氣,屋漏偏逢連夜雨。
「吵死人了!你他媽叫鬼啊?!」嘶啞著聲音扯了兩句,他不甘願地開了門。
江文川抱著手臂站在門外,斜斜地靠著門框。
老男人內裡腐爛透了,外頭的架子還擺在那裡,看上去價值不菲的毛衣,斯文的面孔和金絲框眼鏡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個需要到處借錢的賭鬼。
「什麼事?」江入畫不耐煩地問道。
「你和你堂哥感情很好?」江文川比他更加不耐煩,直截了當地說,「他出國幾年你們有聯繫?」
江入畫一愣,立刻有些慌:「你說顧碎?我們只當過一年校友,別的沒啥關系。」
這倒是真話,顧碎比他大了兩歲,高中當過一年校友也只不過是擦肩而過的交情,只是江入畫自己暗地裡抱有的齷齪心思讓他有些心虛。顧碎高中一畢業就出了國,那時候他在自己家裡大辦了一場,也請了江家,自那以後他和顧碎就再也沒有見過面。顧碎回國後連家都搬到了南邊的城市裡,更是和江入畫沒有什麼聯繫。
「就是你的好校友,」江文川冷笑道,「委婉地說我這裡你待著不好,要把你接到他那裡去住。他不把我、不把江家當親戚,倒是對你看重得很啊。」
江入畫的臉立刻僵了,他比江文川更加百思不得其解。
「你……你答應了?」他的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來,疑惑不解之餘竟然還帶著幾分期待。
「放屁!」江文川罵了聲,「我答應了他不是打自己的臉?」
江入畫心裡頭已經成了一團亂麻,這個早就交了女朋友估計過不了多久就要結婚的堂兄怎麼會突然想要把自己接過去?他們兩個人說過的話加起來恐怕也不超過十句!
然而江文川的拒絕卻讓他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失望。
江文川看他臉色不太好,也就沒有再說什麼難聽的話,只是在心中又把算盤打了幾遍,才放緩了語氣說道:「入畫,你想不想幫幫江家?」
江入畫猛地抬起頭:「你要我幫你搞顧碎,想都別想!」
「你怎麼把話說得這麼難聽?」江文川皺起眉,忍不住揚起了的聲音,「誰要你搞他?搞他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那你想要我做什麼?」江入畫心裡有底,知道絕對和顧碎有關,而且必定不是什麼好事。
「互利互惠的事兒。你知道現在我們江家日子過得不太景氣,你那個好堂哥現在又飛黃騰達了,偏不肯接濟我們。他怕我不還錢我也不一定要他借,只要他最近那個大生意可以讓我搭個便車,也夠我們消受的了。」
「你要拿我逼顧碎?恐怕沒什麼用。」
「誰要拿你?」江文川嗤了一聲,「只是要你辦一件事,你辦好了,顧碎一定會答應我的條件。你辦不好,就自己滾出江家,我養不活你,順便把你那個一臉倒楣樣的妹妹也帶出去。」
江入畫的瞳孔一縮,不禁握緊了拳頭。
他自己確然可以一走了之,可是難過的會是他的雙胞胎妹妹江辰潔。
江辰潔和江入畫長得很像,性格倒是天差地別。江入畫一向比較內斂,而這個妹妹則是熱情外向,像個小太陽,走到哪兒都會發光,都招人疼的,江入畫自然也不例外。
這樣一個小姑娘家,要是給江文川掃地出門,恐怕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而且江入畫知道他們的老頭子做得出這種事來──這男人的靈魂都給賭博抽掉了,恨不得馬上把家裡的兩張嘴換成賭場上的籌碼。
抿起了嘴唇,指尖擰得發白,江入畫冷著聲音問道:「你到底──要我幹什麼?」
「放心,不是什麼難事兒。」江文川的臉色終於漸漸的好轉起來,他側身讓江入畫出了房門,然後兩人一起進了書房。
江入畫咬了咬嘴唇,動作卻沒有猶豫。
強烈的罪惡感攫住了他的心臟──他隱隱發現自己的內心深處埋藏著一丁點,雖只是一丁點卻無法忽略的期待。
第二章
飛機上。
「請問有紙巾嗎?」青年等了好久才等來了乘務員,有些可憐地問。
感冒第二天,不僅喉嚨痛,漸漸地開始鼻涕流個不停,他都懷疑要掛到臉上了。
乘務員好心地給了他一包紙巾,又遞給他兩顆感冒藥。
「謝謝!」青年開心地笑了,眼睛彎了彎,年輕英俊又偏向斯文俊秀的長相很快博得了對方的好感。
江入畫對這雪中送炭的空姐十分感激,他沉浸在即將見到顧碎的忐忑和愧疚中迷迷糊糊地被江文川送上了飛機,感冒加重後才驚恐地發現自己幾乎什麼東西也沒帶。
若不是這個好心的空姐,恐怕自己真的要掛著兩條鼻涕去見夢中情人了。
吃了藥,有些犯困,卻被心裡的緊張壓了下去,江入畫心裡仍舊像是一團亂麻。
六年了,離上次見到顧碎已經六年了。
學生時代的顧碎有一頭柔軟的黑髮,一雙漂亮的灰色眼睛和像玉器一樣光滑潔白的皮膚,他冰冷而又安靜,就像是一塊完美無瑕的玉石。
然而過了六年,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毫無疑問會更加的高大挺拔,那雙灰色的眼睛會更加的深邃美麗。一想到這些,江入畫的呼吸就不禁急促了起來,像是豪飲下了一壺烈酒。
他無奈地呻吟了一聲,用力在腦袋上拍了一掌:別想了,江入畫,你不是去見情人,也不是去相親,你是去當小偷的!你不用臉紅心跳,只要仔細不給顧碎抓起來打死就好了。
顧碎名義上是江入畫的堂哥,但看姓氏就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恐怕還要更加複雜。
顧碎和江入畫並沒有血緣關係。
顧碎的母親莉密爾是個來自法國的雕刻家,是位性感的法國女郎,有著雪白的皮膚和美麗的灰色眼睛。她對中國歷史悠久的玉雕技術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著,便趕來深造學習。期間愛上了江文川的哥哥江文濤,結婚後生下了顧碎──那個時候的顧碎還姓江,也沒有這樣一個不祥的名字。
傳聞顧碎十二歲那年江家東窗事發,江文濤得知他是莉密爾和一位顧姓雕刻家的私生子,便把那漂亮的法國女郎關進了她的工作室,不讓她外出也不讓她碰雕刻工具,失去靈魂的女子成日的哭叫,終於有一天她的兒子忍不住把她的刻刀還給了她,她便毫不猶豫地拿刻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鮮血噴在還未刻完的白玉玫瑰上,也噴了顧碎一頭一臉。
自那以後,江文濤腦子就出了問題,酗酒,賭博,說不定如今江文川那副鬼樣子就是受的他的影響。
顧碎十五歲的時候江文濤死了。並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十五歲的少年用啤酒瓶的碎片刺穿了心臟。沒有人知道這對父子間發生了什麼,只是警方在看了監控錄像後判了正當防衛,顧碎也被檢查出了輕度的精神分裂,毫無疑問,當時江文濤一定是想要對這個私生子做出一些慘無人道的暴行。
顧碎與莉密爾相似的眉眼讓人不難猜到江文濤想要做什麼。
想到這裡江入畫的心就揪了起來,他生恐顧碎知道了自己對他的那點齷齪心思以後厭惡自己,於是便免不了的緊張慌亂。
江文川要江入畫做的事絕對不簡單,他要江入畫把莉密爾死前的最後一件作品,那朵玉雕的玫瑰偷出來。那玫瑰當年被顧碎的親生父親帶去了法國,顧碎出國後沒多久就一擲千金把它買了回來,江文川堅信這朵玫瑰會是用來威脅顧碎的籌碼,江入畫卻覺得不然。
沒有什麼能威脅到顧碎,除了他的玫瑰夫人。
咬了咬牙,江入畫下了飛機,轉了幾站車又走了幾公里路才找到了顧碎家,一見到那房子他就驚呆了。
江文川說顧碎飛黃騰達了果然不假,那地處偏遠的別墅大得像是一座小型的城堡。
江入畫猶豫了一下才走到那氣派的院門前按下了門鈴,過了好半天才有個管家模樣的人過來開門:「您是?」
「是顧碎家嗎?」江入畫假裝出一副很隨意的樣子,「我是他以前高中的校友,正好路過這一片,就想過來看看他。」
話還沒說完他就想打自己耳光:碰巧路過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說出來自己都不相信。
那管家果然微皺起了眉:「您貴姓?我去問先生一聲。」
江入畫忙陪笑道:「免貴姓江。」
管家的神情微變:「江入畫先生?」
「是的。」江入畫有些狐疑。
「趕快請進吧,顧先生前些日子還提起過您。」管家忽然笑了起來,「顧先生現在在沐浴,您可以四處走走──請務必留下來與他共進晚餐。」
沐浴?
江入畫嘴角抽了抽,耳根有點熱,面上不動聲色。
「那麻煩您了。」他笑著對管家點了點頭,又作出一副驚豔之色,「這房子真大!我可以參觀下嗎?」
「請您隨意參觀。」管家帶著禮節性的微笑點了點頭,引江入畫穿過院子,走了近百米才到正門,「顧先生在頂樓沐浴,我要去為他準備晚餐,您可以到處看看──往西走就是先生的書房和藏品室。」
江入畫的眉頭跳了跳,藏品室?得來全不費功夫啊?
心跳有些加速,他面上仍然十分平靜,笑著與管家道了別,便看似漫不經心地在這棟豪宅裡邊晃悠,東轉西轉了好半天才轉進了向西的走廊裡。
這一條走廊是與眾不同的,客廳及其他走廊鋪的都是復古的彩繪地毯,唯獨這一條鋪著寬大柔軟的雪白長毛毯,連帶著整條走廊都更加溫馨明亮了起來。
江入畫猶豫了一下,還是脫下了鞋,赤著腳走在那雪白的毛毯上,發現這毛比想像中的還要長,幾乎覆蓋住了他的腳踝。
細軟的皮毛莫名其妙地讓青年想到了馬索克,他整個人都僵直了抖了抖。
「想點正常人該想的東西吧江入畫,你已經精蟲上腦,沒救了!」他暗罵了自己一聲。
越走越深,裡面越昏暗,江入畫想要開燈卻沒有找到開關,他驚恐地發現這條長廊裡竟然一盞燈也沒有裝,反倒是這白毛毯越發顯得光亮柔和,像是在雲端一般。
這別墅處處透著詭異。
他吸了口氣,有些膽怯地想要回頭,忽然發現幾乎在長廊的盡頭有一扇門。
江入畫鼓起勇氣把門開了,撲面而來的陽光讓他有些傻眼。
那是一間非常大的書房──與其說是書房,不如說是圖書館。壁爐,落地窗,連著外面的長毛地毯,牆上掛著的世界名作,桃花心木的書櫃,上萬冊的藏書,一切都奢侈精致到了極點。
他緩緩地走了進去,花了好半天功夫小心翼翼地繞著那書房走了一圈,終於在書房最裡面發現了另一扇門。
估計就是那所謂的藏品室。
倒底是作賊心虛,江入畫苦笑著搖了搖頭推開門進去,有些驚訝地發現這根本不是什麼藏品室。
這是一間整潔的客房。裡面的陳設很單調,只有簡單的床鋪衣櫃和一間不大的衛生間。唯一有些令人咋舌的是,那衛生間是全透明的,像是嵌在房間裡的一間玻璃屋子。
江入畫一想到顧碎興許會在這裡面寬衣解帶臉上就燒得慌,連忙移開了視線。
他逼迫自己想些別的什麼:這條長廊已經走到了盡頭,可是並沒有看到管家口中說的藏品室,難道那書房裡還有什麼玄機?或者這間客房就是所謂的藏品室?
江入畫將信將疑地將手伸向那兩個衣櫃,猶豫再三,終於下定了決心:「對不起了顧碎,我逼不得已的,如果你覺得冒犯了就把我打一頓吧,我保證不還手。」
頂樓。
男人從浴池裡出來,身上鬆垮地披著一件浴袍,頭髮上還帶著斑駁的水跡,他背對著門輕聲問道:「晚飯準備好了麼?」
「準備好了,先生。」
他點了點頭,接著仰起頭繼續看著前方。
房間的盡頭是一塊巨大的液晶屏,裡面的畫面很清晰,任何一個微小的動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視頻裡的青年盲目又慌亂地在他的書房裡走動,接著進了他的藏品室,對著透明的浴室耳根發紅。
男人嘴角始終帶著溫和的笑意,他靜靜地看著奔走的青年,從他圓潤的耳垂一直到白皙的腳跟,連身上的每一根纖維似乎都捨不得放過,他的眼裡帶著一種讓人讀不懂的含蓄光彩,直到對方伸手試圖打開收藏室裡的衣櫃。
「亞當和夏娃受到薩麥爾的誘惑偷嘗禁果,潘多拉因為好奇打開了魔盒。」他的聲音很輕,也很冷,「無論是盜竊還是欺騙,都是不應該的。」
灰色的眼睛像兩顆沒有感情的玻璃珠,裡面折射出有些駭人的異樣光來,骨節分明的手指從寬大的浴袍中伸出,輕輕地覆上了一個紅色的按鈕。
那雙手很白,白得有些刺目,但是那色澤就能讓人感到一陣寒冷,像是從來沒有見過陽光似的。
他闔上眼睛,幾乎沒有顏色的嘴唇動了動,發出一聲喟歎:
「這樣的會面真是糟糕極了,不是嗎?」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玫瑰夫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0 |
二手中文書 |
$ 170 |
BL/GL |
$ 170 |
小說 |
$ 176 |
BL |
$ 180 |
華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玫瑰夫人
江入畫有一個藏於畫布的祕密,
他暗戀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堂哥顧碎,
嗜賭的父親卻要求他成為可恥的小偷,
再沒有比被顧碎抓個現行更讓人絕望。
顧碎有一頭柔軟的黑髮和漂亮的灰色眼睛,
他冰冷而安靜,像是一塊完美無瑕的玉石。
但如此溫文爾雅充滿禁欲感的顧碎,
卻囚禁了江入畫,引誘他墮入欲望的深淵。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江入畫站在家門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二樓書房的窗開著,能把人耳朵震聾的爭吵聲傳出來,他面無表情地從口袋中摸出一副橡膠耳塞塞到耳朵裡,手插著口袋,晃晃悠悠地進了家門。
「張媽,江文川又在和人吵架?」
張媽苦笑了聲:「江先生要借錢。」
江入畫點了點頭便上了樓,路過書房的時候冷著面孔瞥了一眼裡頭,就徑直地回了房間鎖上門,繼續畫早上沒畫完的一幅畫。
外頭傳來東西被砸碎的聲音,緊接著是撞門,估摸著是江文川死活借不到錢,只好把人給趕走了。
江入畫像是什麼也沒聽到一般耐心地動著筆,筆尖下漸漸出現一團...
江入畫站在家門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二樓書房的窗開著,能把人耳朵震聾的爭吵聲傳出來,他面無表情地從口袋中摸出一副橡膠耳塞塞到耳朵裡,手插著口袋,晃晃悠悠地進了家門。
「張媽,江文川又在和人吵架?」
張媽苦笑了聲:「江先生要借錢。」
江入畫點了點頭便上了樓,路過書房的時候冷著面孔瞥了一眼裡頭,就徑直地回了房間鎖上門,繼續畫早上沒畫完的一幅畫。
外頭傳來東西被砸碎的聲音,緊接著是撞門,估摸著是江文川死活借不到錢,只好把人給趕走了。
江入畫像是什麼也沒聽到一般耐心地動著筆,筆尖下漸漸出現一團...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涼容 繪者: 青哥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3-15 ISBN/ISSN:978986296942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13*21*1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