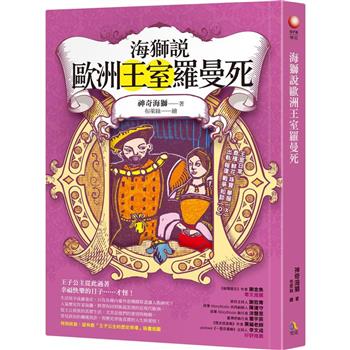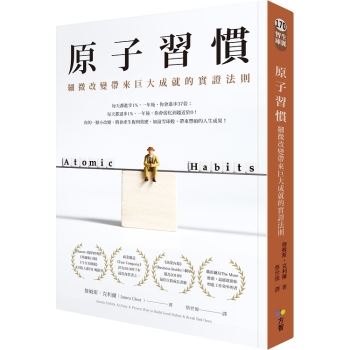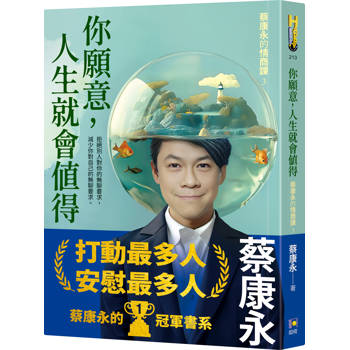父子倆在海濱別墅住了半個月,期間不是吃飯就是做愛,偶爾手拉手去附近的海灘上散步,或者由喬元禮掌舵乘小帆船出海──往往演變成野戰的結局。
喬元禮使盡渾身解數滿足兒子的渴望,用盡各種花樣手段開發這具年輕生澀的身體,耐心地尋找每一處能引發快樂的位置,引導他學會接受和釋放自身的欲望,同時取悅和滿足擁有他的男人。
這樣從零開始親身「教育」一個年輕人,對喬元禮來說尚且是頭一遭,更別提對方還是自己親手養大的兒子。他滿懷熱忱,如同對待一件無價的稀世珍寶一般小心翼翼地開拓,為喬銘易的每一個進步而狂喜不已。
喬銘易初嘗性愛的美妙滋味,整日沉溺於同喬元禮耳鬢廝磨,恨不得一輩子都躺在喬元禮的床上。他從未想過自己最隱祕的旖念竟有成真的一天,夜裡沉睡時,時常作遭到喬元禮拒絕的噩夢,驚醒後發現自己躺在父親懷中,一時分不清夢境和現實,總要喬元禮深深吻他才能放心睡去。
與養父產生超越親情的關係到底對還是不對,他已經無從分辨了。他只知道自己喜歡喬元禮,喬元禮也喜歡他,在床上結合的時候,他快樂得都要哭出來了。
清晨和傍晚時在沙灘上散步,挽著喬元禮的胳膊或是被他摟在懷裡,每當這時喬銘易心裡就彷彿有什麼溫暖的東西要溢出來了。如果喬元禮忽然惡作劇地親他一下,他覺得自己會像臺暴走的機器一樣直接過熱爆炸。
海濱別墅是一座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對喬銘易來說則是從小到大所待過的最愉快的地方。這裡沒有規則,沒有束縛,沒有人為劃定的界限,也沒有需要維持的尊嚴,更沒有會來打擾他們的人。這個地方只關乎愛和幸福,只有喬銘易和喬元禮。
喬元禮覺得兒子滿二十歲了,應該送件貴重禮物以示慶賀。生日的時候他把人家拐到海濱別墅吃乾抹淨,沒來得及送禮,事後才想起來補上。
理論上來說送輛名車就差不多了,身邊那些大佬討兒女歡心似乎都是這麼幹的,但喬銘易豈是普通人,雖然天天對著喬元禮的幻影流口水,但送車還真不一定會笑納。喬元禮委實拿不準兒子的喜好。
所以他單刀直入,問喬銘易:「沒來得及送你禮物,你想要什麼?」
喬銘易猶豫片刻,小心翼翼地問:「要什麼都可以嗎?」
「嗯,你儘管說……但是也別太離譜。」
「……買個X音miku的塑膠小人兒行嗎?」
喬元禮:「???」
喬銘易解釋了半天喬元禮才搞懂,所謂的塑膠小人指是日本產的動漫人物小模型。他搞不清現在的年輕人怎麼會迷上那個,果真是有代溝了嘛……而且在這種幾千塊的小玩意兒上花錢對喬元禮來說就相當於走在路上不小心掉了個一毛硬幣,根本無關痛癢,喬銘易應該開口要個更昂貴的東西才對。
喬元禮打電話給部下。每天都有專門的傭人往別墅送食材和日常用品,沒過兩天,禮物便和每日食材一起送過來了。
喬元禮看著那個綠頭髮美少女百思不得其解。
「以後這種東西……你想買就自己買吧,何必叫我送……」
「自己買和你送的怎麼一樣!」喬銘易振振有詞,拿起美少女偷看人家的小褲褲。
喬元禮哭笑不得。別家的黑幫少主,俗的愛玩車玩錶玩槍,雅的愛收集標本古董字畫,還有些劍走偏鋒獨闢蹊徑的在搞藝術玩樂隊,自家兒子卻鍾情於美少女手辦……他自己對這種東西毫無興趣,所以兒子到底是在成長的哪一步出了錯,養成這種奇怪的愛好?
雖然沒辦法理解,但喬銘易高興比什麼都重要。
喬銘易拿到塑膠小人之後愛不釋手,擺在桌子上拍個不停,要不是怕碰壞了哪個小零件,恨不得睡覺都摟在懷裡。就連裝小人的盒子都捨不得扔,打算一併帶回喬家大宅。
可喬銘易不願把塑膠小人和八角尖尖的漂亮盒子同一堆雜物放在一起,萬一他和喬元禮「情難自禁」的時候不小心碰壞了怎麼辦!
臥室裡沒什麼地方。喬銘易記得別墅也有一間書房,書架上方的空隙恰好足夠放下一個盒子,還不容易被弄壞,便屁顛屁顛地搬來人字梯,將空盒子和塑膠小人擺到書架頂端。
爬下梯子的時候不小心碰到書架上的書,幾本硬皮大部頭嘩啦啦掉了一地。喬銘易跳下梯子收拾現場,將書本塞回原位。
除了書本,被他不慎碰落的還有一本藍色文件夾,就是普通用來夾資料檔案的那種。喬銘易沒有偷看的想法,他和喬元禮在這方面向來井水不犯河水,喬元禮不會亂翻他的漫畫書小本子,他也不會瞎碰喬元禮那些神祕兮兮的文件,與其說是他們相互尊重,毋寧說是他們對彼此的領域都絲毫不感興趣。
但文件夾掉落時裡面的紙張也一併摔了出來,喬銘易彎腰拾起的時候,發現那是一幅鉛筆素描,畫著一個裸男。他從不知道喬元禮會畫畫,還是這種人體藝術作品。爸爸的興趣愛好真是廣泛。
他紅著臉將畫作放回文件夾中,可一打開才發現裡面全是裸男素描。
等等,這畫中的裸男……怎麼好像是他?
他仔仔細細一張張翻過去,發現果然畫的是自己。畫中的他神態迷醉,擺出各種性感姿勢,有幾張甚至露骨地畫出了性器官的模樣。
他臉上火燒似的發燙,身體更因為目睹了這種撩人畫面而微微起了反應。
喬元禮這是要搞事啊!幹嘛偷偷摸摸地畫他的裸體?對著擼嗎?到底是什麼時候畫的?難道他睡著的時候,喬元禮就在旁邊暗戳戳地畫畫?他以為他是傑克嗎?!
但是想到爸爸對自己抱有這種不可言說的祕密心思,喬銘易又覺得有些興奮不已……人人都有奇怪的性幻想,原來喬元禮喜歡這個……
以喬銘易閱漫無數的眼光看來,喬元禮畫技算得上是大觸級別了,如果改行以紳士漫畫出道,肯定會獲得無數擁躉。
就是有個地方畫錯了。畫中人右額上有一條傷疤,喬銘易的傷卻在左邊,位置也不大對,可能是喬元禮記錯了吧。而且疤痕這麼畫的確更帥氣一點,要不是喬銘易知道自己是什麼德行,真會以為畫中人是位黑幫大少呢。
快樂的時光終究是短暫的。半個月後,他們不得不返回喬家大宅。喬元禮總得回去主持幫派大局。他是父親也是情人,更無法脫開黑幫魁首的身分。喬銘易覺得可惜,但喬元禮晚上總會回到他身邊。
大宅子裡的傭人們很快就發現了兩人的關係──畢竟喬元禮雖然沒明說,但也沒刻意隱瞞。主人每天晚上都和少主人同床共寢,第二天床鋪上總會出現可疑的凌亂和水跡,再加上喬銘易的脖子和手臂上時不時出現的吻痕,答案簡直呼之欲出了。
一些傭人認為父子間發生這種事簡直不可理喻,但更多人則覺得意料之中,畢竟養父風流瀟灑,兒子俊俏可愛,兩人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在同一個屋簷下日日相處,即使擦槍走火也無甚稀奇。
有些傭人的錢包裡多了或少了一些鈔票,原來多年前他們私下就賭過大老闆和小公子會不會發生什麼,現在賭局結果總算見了分曉。
一天早餐的時候,廚師做了好些高熱量高營養的食物端上桌。喬元禮對食譜的變動相當敏感,問:「一大早就吃這麼豐盛?」
廚師是喬家十幾年的老傭人了,和喬元禮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尊卑之分,揶揄地回答:「給銘少補補身子。」
喬元禮沉默地盯著他。
廚師繼續道:「銘少還年輕,萬一縱欲過度搞壞健康就不好了。大老闆可得節制一點。」
喬銘易難為情得恨不得鑽進餐桌下面!
喬元禮也有些狼狽。「你們都知道了?」
「我們做下人的又不瞎……」
既然傭人們都知道了,喬元禮也不再顧忌什麼,此後在家裡不論是親吻還是做愛都光明正大地來,也不迴避他人的眼光。
喬銘易臉皮薄,總覺得在服侍了自己這麼多年的保姆傭人面前有點抬不起頭,好像做了什麼羞於見人的事一樣。可不知是不是他自以為是的錯覺,總覺得下人似乎對自己更尊敬了一些。畢竟他現在不僅是大宅子的少主人,更是唯有的兩個主人之一了。
就是常常覺得傭人看自己的目光有些奇怪,尤其是那些在喬家工作多年的老人。這也難免。他當喬元禮的兒子當了那麼多年,突然之間變成了喬元禮的情人,傭人們一時適應不了、甚至內心鄙棄也很正常。
那些看著喬銘易長大的老傭人們常常對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喬銘易常猜測他們到底是要勸告自己,還是抒發什麼不滿?終於有一天,他叫住自己的保姆松姨,問:「松姨想說什麼?直接說就好了,我又不是我爸,不會大發雷霆的。」
松姨猶豫了一會兒,問:「銘少,大老闆對你好嗎?」
喬銘易莫名其妙:「他對我當然很好啦。」
「他有沒有對你說過奇怪的話?」
「……怎麼樣算是奇怪?」
松姨摸了摸他的腦袋。小時候這個動作代表親暱,現在喬銘易已經比老婦人更高,摸頭就顯得有些滑稽了。
「沒有就好。」老婦人意味深長地笑笑。
之後不論喬銘易怎麼追問,松姨都不肯透露她這番問話的緣由。
喬銘易拿同樣的問題問喬元禮。父親若無其事地捧著茶杯:「松姨待你親,大概怕我三心二意虧待你吧?」
「爸你會嗎?」
「當然不會。」
他攬過喬銘易的腰,兩人交換了一個熟稔而自然的深吻。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喬銘易總覺得喬元禮的眼神有些閃躲。
又到一年中元節。
依照慣例,喬元禮應該帶喬銘易去拜祭親生父母。可今年有些不同尋常。不久之前他們才在于氏夫婦墓前大鬧過一場,沒過幾天喬元禮就把喬銘易拐上了床。現在他們不僅是父子也是情人,到了于氏夫婦面前,身分頗為尷尬。
喬元禮左思右想,決定不去了。
「今年你一個人去看看吧。」
中元節那天早上,他讓喬銘易規規矩矩穿上一件白襯衫,站在落地穿衣鏡前替兒子整理衣領。
「你不去?」喬銘易不解。
「你說我見了信城和阿梅,是該叫他們大哥大嫂呢,還是該叫他們岳父岳母?」喬元禮苦笑,「怕他們生我的氣,無顏面對他們。」
好像也有道理。喬銘易一直以為養父天不怕地不怕,想不到他居然會因這種事而忐忑不安。不過若是換做他自己,恐怕也覺得汗顏。「我把兒子託付給你,你居然上了他,喬元禮你他媽還是人嗎?」他腦補著親爹暴跳如雷的模樣,不禁打了個哆嗦。
「那我替你多美言幾句。」
喬銘易正準備離開,喬元禮拉住他的手笑著問:「是不是忘了什麼?」
喬銘易踮起腳在爸爸唇上蜻蜓點水般吻了一下。
剛要分開,喬元禮忽然用力扣住他的腰,將他拖回跟前,深深地獻上一個溼潤濃厚的吻,這才依依不捨地放他離去。
喬銘易捂著紅腫的嘴唇,胸口小鹿亂撞。現在喬元禮對他完全就像對待情人一樣,甚至比一般的情人更加親暱和寵愛,他卻不怎麼適應。多年來相處的習慣可不是說改就能改的,而且他還是第一次和別人發展出這麼親密的關係……
不過只要時間久了,慢慢就習以為常了吧。也許有一天他們會變成老夫老妻那樣……嗯,現在想那麼久遠的事幹嘛!
喬元禮准許他開自己的車,所以他駕著幻影瀟灑地來到風山陵園。今天前來祭拜掃墓的人很多,上山的小路甚至有些擁堵。好不容易來到父母陵前,喬銘易點上兩炷香,學喬元禮的樣子放上一支古巴雪茄,在墓前蹲下,擦了擦墓碑上的照片。
「爸、媽,是我,我又來了……」他不好意思地說,「抱歉讓你們擔心了。我和我爸……呃,我是說我養父,我們已經和好了。他對我一直很好很好,之前我說他虧待我,那是我鬧脾氣說胡話,你們千萬別當真。」
頓了頓,臉上騰起一朵紅雲,「另外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我和……」他思忖幾秒,覺得這時候再叫爸就有點奇怪了,於是改口直稱喬元禮的名字,「我和元禮在一起了。就是那個在一起的意思。你們別誤會!從小到大他一直對我規規矩矩,從來沒幹過什麼越線的事。是我先喜歡上他的。」
他揪著地上的草葉,扭扭捏捏了半天才繼續說下去,「今天他不好意思過來,覺得丟臉,所以只有我一個人來了。我就是想說……我們倆這個事吧,是有點奇怪,但是我真的喜歡他,他也喜歡我,我們不是隨便玩玩,而是真心的。我是想……」他的聲音低下去,「是想跟他過一輩子的。你們不要生他的氣好不好?」然後又補充一句,「也不要生我的氣!」
于氏夫婦當然無法回答他的問題,所以他自顧自認為九泉之下的雙親看到他們恩愛幸福,一定也會祝福他們。他轉而講起自己在大學裡的經歷。不知不覺,一個小時過去了。他拍拍手上的塵土,準備告辭。
起身的剎那,他猛地注意到墓碑照片上的一處細節──過去一直沒在意過,現在卻明晃晃地扎眼。
照片上的于信城右眉有一道傷疤。
和喬元禮畫作中的一模一樣。
喬銘易忽然生出了一種可怕的想法。
讓喬元禮心心念念到畫進畫中永遠保存的男人或許不是他,而是他的親生父親于信城。
下山時喬銘易腦子亂作一團,整個人失魂落魄的,幸虧掃墓的人多,他只需要跟著大部隊緩緩前進就不會迷路。
快到陵園門口時,模模糊糊聽到「喬元禮」三個字,猛地清醒過來。
前方不遠處有一男一女正背對著他,也是往陵園外的方向走。他混在人群中悄悄接近那對男女,豎起耳朵聆聽他們的對話。
「剛才在停車場明明看見喬元禮的車了,卻沒見到他人。」男人說。
「有沒有可能剛好是同款的車?」女人問。
「如姐啊,那可是本市唯一一輛勞斯萊斯幻影。」
「興許是剛好錯過了吧。」
喬銘易覺得男人面熟,回憶了一下,想起他也是道上的一位大佬,名叫孟仁博,經營地下賭場,和喬元禮關係不錯,經常喊他去搓麻打牌,逢年過節不時送上些禮物。喬銘易對他的印象還算可以。
他稱呼身邊那女子為「如姐」,大概就是喬元禮曾經提過的那位「阿如」。她身材火辣,五官精緻,是個美豔少婦,難怪喬元禮拿她來和自己開玩笑……
「說到喬元禮,如姐有沒有聽過最近一個八卦?」孟仁博似笑非笑。
是女人就愛聽八卦。如姐立刻好奇地湊近:「什麼什麼?快和我說說!」
「上次打牌時老茶不是提過,喬元禮收養了他兄弟的遺孤嘛。本來當他是個正人君子,結果最近他終於繃不住,把那孩子給睡了。」
喬銘易握緊拳頭。孟仁博到底是從哪兒聽說他們家私事的?!
但回頭一想,喬家大宅的傭人保鑣全知道這事了,說不定其中某個人在外面說漏了嘴。黑幫大佬們消息何等靈通,什麼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何況喬元禮本來也沒有刻意隱瞞的意思。
如姐掩唇嬌笑:「原來喬老闆喜歡光源氏這套呀……哎喲喲,人不可貌相。」
「如姐說得分毫不差,可不就是光源氏嘛!喬老闆年輕時是喜歡他那個兄弟的。如姐大概沒見過那孩子吧?和他親爹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妳說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喬元禮竟然能忍這麼多年,也是蠻了不起的。」
「那孩子也是可憐,被養父這麼著了,以後大概再難找別的對象了吧……」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姐妳覺得人家可憐,說不定人家挺開心的呢。不過喬老闆是有福啦,都說自己的勞動果實最香甜,那麼自己養大的孩子也最好吃吧,嘿嘿嘿嘿嘿……」
兩人竊竊私語,有說有笑,喬銘易卻在後方聽得心驚肉跳!
他們到底在說什麼……爸爸喜歡他親爹?怎麼可能,肯定是他們胡說八道!是他們聽風就是雨,散播惡毒的謠言中傷喬元禮!
爸爸喜歡他,是因為他是喬銘易,因為他是心愛的兒子和可愛的情人,甚至因為貪戀他年輕鮮活的身體,而不是因為……不是因為他酷肖生父于信城!
然而喬銘易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
為什麼大宅子裡老傭人看他的眼光那麼奇怪?
那些素描又該作何解釋?
他這才想起畫紙已經有年頭了,泛著陳舊的黃,不可能是近期畫的,喬元禮將畫著心中隱祕幻想的畫作夾進文件夾是很多年前的事,而當時喬銘易還是個孩子,額上更沒有傷痕。
畫中的男人只可能是于信城。
喬元禮對自己的弟兄抱著難以啟齒的愛意,當對方不幸過世後,將這份愛意轉移到了對方的獨子身上。
難道喬元禮在床上和他翻雲覆雨的時候,竟然把他當作于信城的替身嗎?!
他耳鳴不已,頭暈目眩,彷彿能聽見血液瘋狂奔湧的聲音。他差點一個跟頭栽倒在登山階梯上。旁邊有人扶了他一把,說:「當心啊小夥子,是不是天氣太熱中暑啦?」
喬銘易咕噥著對旁人道謝,追上前方的孟仁博和如姐。
他非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非黑即白(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非黑即白(下)
作為養父子一同生活了十多年,
卻因裴子莘這條導火線,
燒出了兩人之間別樣的愛意。
突破了悖德的界線,
喬銘易義無反顧地跳進一場,
名為「喬元禮」的濃情美夢之中。
但原以為是相伴永遠的甜蜜,
卻因一份陳舊畫作,
意外地戳破心底最痛苦的秘密──
原來他,從來都只是那人的替身而已……
聖光戰士波瀾壯闊一生已告終,
從此他只是個平凡的青年人。
然而喬元禮想要的,從沒有得不到的。
更何況是這枚自己悉心呵護,
難得可貴的宅男真心──
聖光戰士的人類老父不可小覷,
耍賤的本事可是堪稱一流地……
TOP
章節試閱
父子倆在海濱別墅住了半個月,期間不是吃飯就是做愛,偶爾手拉手去附近的海灘上散步,或者由喬元禮掌舵乘小帆船出海──往往演變成野戰的結局。
喬元禮使盡渾身解數滿足兒子的渴望,用盡各種花樣手段開發這具年輕生澀的身體,耐心地尋找每一處能引發快樂的位置,引導他學會接受和釋放自身的欲望,同時取悅和滿足擁有他的男人。
這樣從零開始親身「教育」一個年輕人,對喬元禮來說尚且是頭一遭,更別提對方還是自己親手養大的兒子。他滿懷熱忱,如同對待一件無價的稀世珍寶一般小心翼翼地開拓,為喬銘易的每一個進步而狂喜不已。
喬銘易初嘗...
喬元禮使盡渾身解數滿足兒子的渴望,用盡各種花樣手段開發這具年輕生澀的身體,耐心地尋找每一處能引發快樂的位置,引導他學會接受和釋放自身的欲望,同時取悅和滿足擁有他的男人。
這樣從零開始親身「教育」一個年輕人,對喬元禮來說尚且是頭一遭,更別提對方還是自己親手養大的兒子。他滿懷熱忱,如同對待一件無價的稀世珍寶一般小心翼翼地開拓,為喬銘易的每一個進步而狂喜不已。
喬銘易初嘗...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唇亡齒寒 繪者: 原若森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17 ISBN/ISSN:97898629695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13*21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