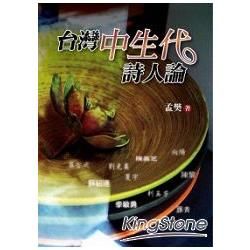緒言
一
我的上一本學術論著《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2006),如該書名所示,從事的是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的研究,其中有四篇論文的研究主題與台灣新詩有關,足見我對新詩付出的關注。轉行跨入文學專業領域,多年來我孜孜矻矻研究的重心主要擺在台灣的新詩,最早關注的是當初方興未艾的後現代詩,試圖從理論的角度切入,檢視台灣後現代詩的表現,目的是希望藉由引介和討論將後現代詩予以理論化,這是我從事學術工作初期的研究焦點,並也因此交出了一本《台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2003)專著。
這本《台灣中生代詩人論》是我研究的另一個轉向,也就是從文學史與文學理論的鑽研轉到詩作的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我的詩作批評當然不是自本書始,在我尚未轉換工作跑道到大學黌宮之前,其實已寫了不少詩評文章,只是那些評論文字零零散散不成系統。本書則是我從文學專業的角度出發,為台灣詩人的詩作所做的較有系統的評論。
二
批評是理論的運用與落實,本書係從西方文學理論出發來考察詩人的詩作文本,其中涉及的文論包括:文學社會學(導論)、修辭學、英美新批評與結構主義(李敏勇論、羅青論、陳黎論)、文類批評(蘇紹連論)、女性主義(利玉芳論)、現象學(陳義芝論)、原型分析(羅智成論)、傳記式批評(向陽論)、後現代主義(夏宇論)與生態批評(劉克襄論),兼顧文本的內緣和外緣研究;而如何適用相關的文論,則視詩人及其詩作特性為何而定。
事實上,每一種文學理論都有它的洞見和盲見。某種文學理論可能適合某類文本,以之做為評論的依據可說正中下懷,並可以挖掘出意想不到的問題─這是洞見;但對於其他文本而言,可能就會顯得格格不入,難以入手,而發覺不到文本潛藏的深意─這是盲見。誠如柏瑞斯勒(Charles E. Bressler)在《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1994)一書中所說,世界不存在有一種無所不包的「後設理論」(metatheory,或譯為「元理論」),可以適合於任何文本的詮釋,「也沒有一種理論可涵蓋一個文本所有的可能詮釋」;換言之,「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窮盡追問任一文本的所有合法性的問題」(8)。正因為如此,面對不同性質的文本,就必須慎選相應的適切理論,始能對症下藥,庖丁解牛。本書運用西方文論入手詮釋當代台灣詩人文本,即係出於這樣的考慮。
就拿文類批評來說,本書以之做為分析蘇紹連散文詩的依據,批評重點自然落在文類的詮釋上,而無法像新批評那樣斤斤計較於蘇氏個別詩作的細讀(close reading)。再以傳記式批評來說,本書對於向陽「亂詩」的檢視乃係自此一研究途徑入手,自然無法顧及其詩作的內緣分析,蓋因傳記式批評是外緣而非內緣研究。你可以說,對向陽「亂詩」不做內緣分析,難以深入其詩作之內蘊─這就是選用傳記式批評本身與生俱來的盲見(可不是我的盲見啊),但是它的洞見卻也讓我們了解詩人的生活經歷如何影響他的創作表現至深且巨。然則我的分析文本為何會落在中生代詩人身上?
三
歷來台灣詩壇注目的焦點一直放在資深輩的詩人身上,他們為新詩在台灣的發展塑造典型、奠定基礎,從辛鬱、菩提、張默、張漢良、管管等人合編的《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開始,各種「十大詩人」的選拔與論述,以及各種詩選集的編選,要角都是前行代詩人,遑論邇來研究對象也都以資深輩詩人為主的博碩士論文了。然而,前行代的這種「三千寵愛在一身」,久而久之也造成「研究擁擠」的現象,譬如就拿余光中一人來說,從國家圖書館的《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題目條查詢「余光中」,即可知迄至目前為止,共有十七篇博碩士論文以他為研究對象(二○一一年十二月瀏覽);換言之,學界的研究對象重疊性太高,這就形成研究資源的浪費。
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言,「江山代有才人出」,時序走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前當時所謂的詩壇新世代,如今由於時間的演進與創作的增長,已經跨入中年而成為中流砥柱的中生代了。目前中生代詩人已成為台灣詩壇創作的主力,綜觀他們的創作也臻於成熟的階段,可謂是台灣新詩史中的要角。縱然如此,在學術研究上受到的關注仍無法和前行代詩人媲美,即以羅智成為例,從《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上查詢到的博碩士論文研究筆數,只得四筆,委實不多。出於上述如此的考慮,才讓我興發以中生代詩人為探究對象的念頭。然則又是哪些中生代詩人值得探討?
四
首先,我要為研究對象樹立挑選的標準:
第一,即是最基本的年歲條件。本書如第一章導論所言,設定年紀約略在四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的詩人為所謂的「中生代」(理由參見第一章,茲不贅述);但這並非楚河漢界的劃界,譬如:李敏勇、羅青、蘇紹連現今都已六十來歲,但是他們仍然不同於洛夫、桓夫、蓉子等人的前行代。
第二,當然是要有質量俱佳的詩作。其中「創作量」指的是至少要出版四本詩集(利玉芳只能勉強算達此標準,雖然她出版有五冊詩集,但其中有兩冊主要是綜合舊作的選集)。四冊詩集的標準自然是個人主觀的認定,我的想法是,如果一本詩集(通常)收有五十至六十首詩作,那麼四本詩集應該可以收入(至少)兩百首作品,而中生代詩人不管是年齡或詩齡都不能算短暫,若創作迄今交不出兩百首詩作,其創作力未免單薄了些。
第三,則是要具備某種代表性或典型性。例如利玉芳之所以列入本書的討論,乃是她同時具備本土(客家)、女性,以及是笠詩社同仁的三重身分;再如劉克襄,以自然寫作聞名於台灣文壇,卻是詩壇長期以來的「獨行俠」,但是他的詩作及其風格卻另闢蹊徑,將自然寫作的文類擴展到新詩的領域,自成典型。其他詩家的情形大體類似,均具備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或典型性。
其次,簡政珍、詹澈、馮青、零雨、白靈、林燿德、陳克華、陳育虹、鴻鴻、江自得,我想到符合上述條件的詩人,一長串具有相當代表性詩人的名單立即浮上腦海來;然而,儘管「情長」,畢竟「紙短」,我終究無法以一本書的份量同時容納─譬如二十位詩家的討論(爰是,本書不敢將書名逕稱為「中生代十大詩人」)。上述那些中生代詩人無一不是當今台灣詩壇具相當份量的詩人(除了已過世的林燿德),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
因此,這本《台灣中生代詩人論》不妨視之為我對於中生代詩人研究的第一步。但盼不久的未來能持續開拓此一研究課題,並交出另一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