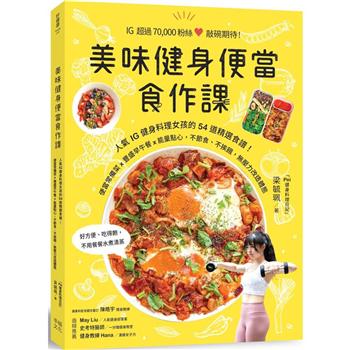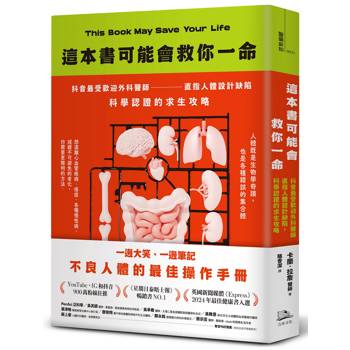一開始我還沒頭緒為自己的這第五本詩集命名。想了老半天,依然委實難以決定,苦惱不已。前幾本詩集,都在書尚未成形之前,已然先有了書名,尤其是前三本:《旅遊寫真》、《戲擬詩》、《從詩題開始》,主要是那三本詩集,在創作之初即有明確的目標,寫作的是新詩特定的文類:旅遊詩、戲擬詩、小詩。即便是處女作,在付梓之前,書名也早已定案。但為何這一冊詩集的書名竟讓我六神無主?原因無他,就是寫作之時與出版之前,迥異於前三本詩集的是,事先沒有訂下任何目的,和絕大多數詩集的出版相似:創作量夠了,可以輯成冊出版,就集結出書,再取個書名――而這也就是我這第五本詩集的由來。
在茫無頭緒為書名傷腦筋之際,左思右想,索性乾脆來個翻轉,先將詩集內各個分輯定名稱,然後再回頭來找書名。依照詩作的主題與調性,我將它們分成七輯;而第一輯名為「十二月練習曲」則是較早就了然於胸的名稱,十二個月份分別就是十二首詩;而所謂「練習曲」乃是指專門提供某樂器練習特定技巧的音樂作品,雖然「練習曲」顧名思義係為初學者的練習而做,但也有不少練習曲要求演奏者有極高的技巧,鋼琴大師蕭邦和李斯特就有好幾首這樣的作品。我的練習曲自然不在炫技(像李斯特那樣),更不敢跟楊牧的「十二星象練習曲」媲美。我只想從特定的視角來表達我對十二個月份的想像與感受。而由「練習曲」開始往下想像其他各輯名稱時,自然而然想到從音樂方面下標題,於是各輯與音樂有關的輯名便一一成形。等到各輯名稱底定之後,書名終於水到渠成,於是「我的音樂盒」便這樣出現。
收入音樂盒裡的總共有六十四首詩作,分別是:輯一「十二月練習曲」十二首、輯二「浪漫樂章」十三首、輯三「夢的小夜曲」五首、輯四「第一人稱獨唱」八首、輯五「生活組曲」十一首、輯六「創作詼諧曲」八首、輯七「主義協奏曲」七首。新詩雖然不像古詩那樣講究格律――因為如今都採自由詩形式,但仍未排除音樂性,其音樂性的表現可從斷句、迴行、停頓、疊韻、複沓、頂真……乃至反覆迴增來表達,至少我自己的詩作是從這些手法入手以求其音樂性。若自此角度觀之,則詩集名曰「音樂盒」,也不能說都無道理。
由於不像我之前的詩集那樣事先已有「定見」,因此收入本詩集裡的詩作,無論是在主題、語言、形式、手法……乃至類型等等,都顯得較為駁雜――而這也是為何詩集會被分成七輯這麼多類別的原因,比如有些詩的語言放得很鬆,且極為透明(〈我的筆名〉),明顯有寫實味;有些詩則語言濃縮、意象稠密(〈睡在一起〉),超現實色彩厚重。有些詩沉重(〈三月〉),有些詩又非常輕盈(〈給吹鼓吹詩論壇開個玩笑〉)。不過,本冊詩作一反我之前出版的詩集,收有不少抒情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情詩作品。情詩多是少艾之作,很多人初初寫詩都是自情詩入手,我也不例外。在這冊詩集中,我特意讓年輕時(大學時代)寫的舊作曝光,而偏偏那時多是情詩作品,是以本冊詩集有較多的情詩收錄在內。也或許因為懷舊情懷使然,竟興起寫情詩的熱頭,人到中年――尤其這兩三年,寫起情詩來反而更能得心應手,甚至油然而生起幸福感呢!
至於說到詩的形式或類型,在「音樂盒」內,我特意收藏了七首散文詩,以往雖也寫過散文詩,但只偶一為之。散文詩有跨文類的特性,其實不易寫作,因為一旦失手,很容易就變成散文――也許是一篇好散文,但卻屬非詩一類了。在我看來,當初以散文詩聞名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的憂鬱》,比較像散文而不是詩。散文詩多少要具備敘事功能,而敘事之多寡以及其具備的詩味厚薄(詩味往往要從其是否具備充足的意在言外的效果來斷定),就要看詩人本身的表現功力了。我需要某種程度的敘事性以表達我的思想,所以我選擇了散文詩來創作;若加上之前已發表與出版的作品,也累積了十多首散文詩,儘管數量不多,但向這種跨文類的挑戰,有時還容易激起創作的熱情哩。
譬如,〈溫暖的黑暗〉這首散文詩,就是在讀完商禽的同題詩作引發的揣想,必須藉如此的敘事始能一吐為快,並且一氣呵成。而這首詩的功成則主要來自由商禽元文本∕元文本的延伸――也就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形成。可以說,互文手法是我在本詩集中刻意為之的一項嘗試,在某些時候甚至有點樂此不疲,如〈夢中之夢〉、〈只剩標點符號〉、〈未來是一隻灰色海鷗〉、〈星散的天秤座〉……這些詩或引用或套用或複製或濃縮或……以達成互文效果,手法不一而足。其實我的第三本詩集《戲擬詩》,主要就是一冊「互文詩集」,只是現在收在這個音樂盒中的互文作品,更加地肆無忌憚,因為我不必只關注「戲擬」一途。
按照始揭此一「互文性」詞彙的法國文論家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的說法,所謂的互文性係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現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而事實上,任何一篇文本或多或少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本;換言之,誠如索樂斯(Philippe Sollers)所說:「每一篇文本都聯繫著若干篇文本,並且對這些文本起著複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互文性使得一個訊號系統被移至另一個系統中以形成其易位(transposition),而如此易位將產生何等光景,讓元文本∕原文本轉世投胎或改頭換面?一向讓我心生好奇而樂意冒險嘗試。當然,會興起這樣的念頭,與我讀詩之餘,受到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思想的啟迪不無關係,而這又和我的書齋生活與學術生涯息息相關。
總之,我這一匣音樂盒所收錄的各式「曲子」,色彩顯得較為豐富,色調較為駁雜,語言則有緊有鬆;但無論如何,它記錄了我已近耳順之齡的創作歲月。我滿心期望下一次再有的「豐收」。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我的音樂盒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6 |
華文詩集 |
$ 255 |
詩 |
$ 270 |
華文現代詩 |
$ 270 |
小說/文學 |
$ 27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79 |
中文書 |
$ 279 |
現代詩 |
$ 28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音樂盒
收藏在這本音樂盒中,
有各種詩的聲音,
從獨奏到協奏……
有我年少的喟嘆,
那最最天真的抒情,
也有我犬儒式的輕笑,
那帶點莞爾的詼諧。
──孟樊
作者簡介:
孟樊,本名陳俊榮,寫詩,寫散文,也寫評論文章;寫最多的是萬字以上的學術論文。
目前供職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開有「現代詩創作」等課程。曾幹過讓人煩透的系主任工作。也在國內外報章雜誌撰寫過十幾年的專欄,在600字稿紙時代寫到食指都長繭。
迄今出版書籍三十多冊,可堪安慰。詩集共有五本,還要加油。
TOP
作者序
一開始我還沒頭緒為自己的這第五本詩集命名。想了老半天,依然委實難以決定,苦惱不已。前幾本詩集,都在書尚未成形之前,已然先有了書名,尤其是前三本:《旅遊寫真》、《戲擬詩》、《從詩題開始》,主要是那三本詩集,在創作之初即有明確的目標,寫作的是新詩特定的文類:旅遊詩、戲擬詩、小詩。即便是處女作,在付梓之前,書名也早已定案。但為何這一冊詩集的書名竟讓我六神無主?原因無他,就是寫作之時與出版之前,迥異於前三本詩集的是,事先沒有訂下任何目的,和絕大多數詩集的出版相似:創作量夠了,可以輯成冊出版,就集結出書,...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輯一 十二月練習曲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輯二 浪漫樂章
PS. 我愛妳
散步
讀經
白露為霜
紅豆吟
再吟紅豆詩
風景照
未來是一隻灰色海鷗――寄給普拉絲的信
重讀少作
在眼瞳裡居住
女孩
秋涼小憩
夜的呢喃
‧輯三 夢的小夜曲
夢的大廈
夢中之夢
我的夢
睡在一起――致布勒東
一整個月無夢
‧輯四 第一人稱獨唱
我的筆名
寫詩的豬手
天秤座
星散的天秤座
撕破臉
溫暖的黑暗――用商禽韻
日以繼夜
在谷歌
‧輯五 生活組曲
在芝加哥
我來...
‧輯一 十二月練習曲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輯二 浪漫樂章
PS. 我愛妳
散步
讀經
白露為霜
紅豆吟
再吟紅豆詩
風景照
未來是一隻灰色海鷗――寄給普拉絲的信
重讀少作
在眼瞳裡居住
女孩
秋涼小憩
夜的呢喃
‧輯三 夢的小夜曲
夢的大廈
夢中之夢
我的夢
睡在一起――致布勒東
一整個月無夢
‧輯四 第一人稱獨唱
我的筆名
寫詩的豬手
天秤座
星散的天秤座
撕破臉
溫暖的黑暗――用商禽韻
日以繼夜
在谷歌
‧輯五 生活組曲
在芝加哥
我來...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孟樊
- 出版社: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1-20 ISBN/ISSN:978986298278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