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縫合傷口,我去下洗手間。」林雪脫掉了血淋淋的橡膠手套,說了一句話,也不等其他人反應便推開有些破損的門離開了。他徑直走進了洗手間,從自己的衣服內側拿出了手機,上面顯示了整整三十四個未接來電。
都是同一個人——許雁。
手機再次震動起來,許雁的第三十五個電話來了。林雪接通了電話,放到耳邊,卻沒有說話,沉默著等著手機對面的反應。
「你在醫院,對吧?」許雁的聲音很平靜,沒有憤怒,沒有焦急,有的只是一種看似柔弱卻極為頑固的篤定,「這便是你最後想做的事?」
「別亂想……是妳睡眠不足,該好好休息了,晚安。」林雪摸了摸鼻子,同時舌頭舔了舔有些乾燥的嘴唇,心中卻對女人的直覺充滿了一種接近委屈的恐懼。這種不符合任何道理的指認往往帶有極高的命中率,沒有一點證據以及道理,直接繞過所有求證程序,簡單而直接地指向了一個事實——林雪就是現在被醫院裡的人恐懼的炸彈狂魔。
直覺那麼管用,還要證據幹嘛?林雪想到這裡,心中的那抹不爽也被放大了,導致他有些憤憤不平。
「現在太陽才剛下山。」許雁的口氣終於顯得有些不悅了,「想騙人,好歹有點誠意,這是起碼的尊重。」
「妳煩死了。」林雪一把將戴在腦袋上的手術帽摘了下來,露出有些凌亂的頭髮,帶點惱怒地說道:「別以為我打不過妳!那一巴掌是我讓妳的!」
「你從六歲起打架就沒贏過我。」
「……」張了張嘴,林雪發現在絕對的事實面前,他的辯駁有些無力,所以他直接跳過中間這個令人尷尬的過程,乾咳一聲,「總之,沒什麼事了吧?」
電話那頭輕嘆了一聲,彷彿在感嘆某人的無賴無恥無臉皮,但林雪卻感覺到了那聲嘆息中帶了點傷感的意味,「你……沒什麼話想和我說?」
林雪沉默,嘴唇微動,似乎想要說些什麼,但他看到走廊盡頭出現的兩名員警時,頓時滿面笑容地朝對方走過去,手機也沒有掛掉,「別擔心別擔心,親愛的,沒什麼炸彈狂魔,反正我沒看到,也許是惡作劇……」
「……」電話那頭陷入了沉默,顯然許雁明白了林雪遇見了一些事。
當林雪從兩名員警面前即將走過的時候,林雪衝那兩名員警在嘴前豎起了食指,滿臉歉意的笑容,似乎期望兩人配合一下。
那兩名員警互相對視了一眼,好像在猶豫要不要盤問,但林雪卻沒有給他們盤問的時間,而是直接從他們中間穿了過去,不斷地比著手勢向兩人表達感謝,滿臉帶笑地對電話裡說:「別被那些新聞嚇到,我想妳知道,現在的記者為了取材可是什麼故事都會編的……好的好的,沒問題,我馬上回來,妳會發現我絕對沒有少一塊肉。」
然後他下了樓梯,隱隱約約聽到上面的對話,「算了,反正犯人肯定早跑了。」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然後又下了一層樓,他的聲音便重新恢復了原來平淡中帶著三分尖刻的語調,「沒事的話,我就掛了。」
回答他的是電話那頭的忙音——顯然許雁沒有問第二遍的意思了。
林雪撇了撇嘴,將手機重新放回口袋,當他快要步出醫院大樓的時候,他碰到一個正踏著重重的腳步,帶有惱怒氣息的聲音從電梯裡走了出來,正是那個被他放倒後,同時被替身手術的李醫生。
「我再說一遍!根本沒有這事!都是……」李醫生看到從一邊樓梯走出來的林雪,頓時嘴巴大張,疑惑中帶著驚懼,不知如何是好。
而李醫生身後也跟上了一名三十多歲,戴著金邊眼鏡的男子。
他指著林雪,嘴唇微動,似乎張口欲言,卻被林雪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手。
「李醫生,沒什麼消息能比見到你沒事更好了……」林雪一臉痛惜地用左手拍了拍李醫生的肩膀,右手卻用指甲狠狠地掐了下李醫生,「不管發生什麼事,畢竟生命才是第一的……況且只要我們什麼都不說,這件事也就過去了,你說是不是?」
不知是否是錯覺,李醫生總覺得這段話中「生命」和「什麼都不說」咬字特別的清晰,清晰到他可以輕易地看到林雪唇齒開合時露出的潔白牙齒,其中似乎擁有著異樣的鋒利。
李醫生艱難地咽了口唾沫,他看著面前這個一臉帶著關切的男子,只覺得他黑色的瞳孔深處有著說不出的冷意和無情,而最後一點的勇氣也在他看到林雪有意無意露出的槍柄而消失——那槍就在只有他看得到的角度的大衣內側口袋裡。
當李醫生的手在林雪的手中一下子變得冰涼,林雪便知道他已經度過了危機,他很滿意地聽到了那個顫抖中帶著怯懦的回答。
「是……是的。」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我想送李醫生回家,他母親打電話給我,很擔心,她希望我能送他回家。」林雪朝李醫生身後的那名男子說著,「他現在最需要親人的關懷。」
男子詫異地點了點頭,又看了看李醫生那有些複雜的表情,說道:「那就走吧,他今天也的確不適合繼續工作了,我還有工作,就不送了。」
「謝謝。」林雪點了點頭,看著男子重新走進電梯,然後轉頭看向李醫生,眨了眨眼,「很明智的判斷,這樣就不太會發生一些讓人不想看到的悲劇了,如果我能走出去……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長壽的。」
「那要是……」蒼白著臉的李醫生說了一半,卻驀然停住了嘴,彷彿唯恐激怒面前的人。
「嗯,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都是聰明人……」林雪笑了笑,瞳孔深處卻沒有絲毫的笑意,「但很遺憾,因為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總之我不想看到,所以你也不會想看到的。」
李醫生額頭的汗開始冒得更加厲害,他顫抖著嘴唇,有些說不出話來,只是用一種恐懼地目光看著林雪。
也許是李醫生的表情實在妨礙他的視線,所以林雪自認為很有耐性地安慰了一句:「安心吧,他們根本就沒查出來目標是什麼人,在某個病人醒來之前,他們無法做出任何有實際效果的針對性行動,只要在那之前出了醫院,就不會發生任何事。事實上,如果不是碰到你,我是打算一個人出去的……嗯,說了這麼多,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呃?」李醫生顯然因為心慌意亂而失去了原有的判斷力,這讓林雪眉毛微微一挑,他本來就沒有太多的耐性和這類人耗著,所以很直白地傳遞出了自己的意思——
「如果你的表情在三十秒內還是寫著『我有麻煩,救命』的話,為了安全起見,我很願意永久性地替你解除煩惱,然後一個人走出這家醫院。」
※
老舊的窗簾遮擋著已經漸漸消失的陽光,讓房間顯得有些昏暗,但是坐在角落裡的人卻沒有站起來將燈開亮的意思,只是沉默著坐在地板上,一柄不常見的武士長刀斜靠在肩膀上,他目光低垂,似乎隨著太陽的告別而即將進入夢鄉。
到了聯邦世紀,武術幾乎已經完全成為了競技遊戲,大多練習武術的人僅僅是為了強健體魄、鍛鍊心志,導致這種古老的武器已經越來越少,不是成為歷史文物放在博物館,就是作為工藝品放在展覽架裡,很少有人會將它拿在身邊,並且還是沒有上保險的狀態。
因為這是違法的,一經發現,便會被檢察院以二級謀殺罪起訴。倒楣的話,也許到生命的盡頭時,身邊放著的還是監獄裡的飯盒。
正常人是不會將這種東西帶在身邊的,所以這個似乎已經陷入熟睡的人自然不是正常人。
他叫櫻井賢治,他的身分本就是殺人犯,所以帶不帶手中這把刀,都沒有區別。更何況,這不是一般的刀,這是他的家傳刀刃——千鳥一文字。
看其俊秀的臉頰,被梳理得宛若流水般暢滑的黑色長髮,以及其恬靜的姿態,實在沒有辦法把他和一個殺人凶手聯繫在一起;更沒有辦法理解,他殺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親。
櫻井賢治的左手一直放在刀鞘上,當房間裡的光線變得更加昏暗的時候,櫻井賢治依舊瞇著眼睛,似乎在養神,但他白皙的拇指在刀鍔處輕輕推了一下,武士刀彷彿在此刻活了過來,縫隙處的刀刃將微弱的陽光映射得無比森冷,「你遲了整整半個小時。」
「注意你說話的口氣,新人。」一團漆黑的影子在窗下漸漸浮起,最後露出神情不悅的巴布魯,「從死刑犯變成異能者已經夠幸運的了,想要繼續保持這種幸運,就得老實一點,老實人總是能活得久。」
「無理。」櫻井賢治抬起低垂的頭,冷冷地看著巴布魯。
「我比你厲害,我就是道理。」在已然變得黑暗的房間中,巴布魯的膚色讓他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透明的狀態,只能聽到他以一種老兵欺負新兵的態度說話,「這也是組織裡的道理,你有意見?」
「有理。」櫻井賢治沒有生氣,反而皺著眉頭想了下,隨後認真地點了點頭,他從地上站了起來,慢條斯理地拍打著褲子上不知存在與否的塵土,「你融入影子狀態需要多久?」
「我為什麼要告訴……」巴布魯話說了一半,驀然頓住了,他的瞳孔和貼緊頭皮的捲髮瞬間變為綠色,但他的左邊臉頰上,卻依舊多出了一道血痕。
「不告訴我也沒關係,我只需要知道你比我的刀要慢就可以了。」慢慢地將帶著微弱寒光的刀刃緩緩地歸入鞘中,使那最後一抹讓人無法直視的鋒銳遮擋起來,櫻井賢治面無表情地看著神情愕然的巴布魯,「所以現在,我便是理。」
摸了摸臉頰上的那道細長刀痕,感覺有些疼痛的巴布魯咧了咧嘴,然後他很光棍地點了點頭,「是我不對,我道歉。」
櫻井賢治是個講理的人,所以他的回答也很有道理。
「沒關係。」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偏執狂事件簿(1):鬧彆扭的炸彈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偏執狂事件簿(1):鬧彆扭的炸彈客
嗯,今天心情有點壞?那來幾顆炸彈吧~
沒良心+快要死了的天才VS.演技百分百痞子刑警
偏執狂協尋失蹤人口(who?)第一彈,混亂登場!
「我不是兄控,我只是記仇而已!」
始終「念念不忘」兄長失蹤前將他打暈的那一下,
執著的林雪總算自警察好友委託的事件中找到了線索,
等候多年的愛與恨(?),都將有個結果……
因為別有目的,林雪始終無償提供腦袋,協助刑警好友解決案件,
這一次,自嚴密監視的重獄中消失的死刑犯帶來了全新挑戰!
然而犯人遺留在監獄之中的線索,
竟是牽扯出林雪那失蹤多年、患有精神癌症的兄長……
為了尋找兄長的下落,林雪不惜化身炸彈客,
同時將槍口指向了攔在自己身前的好友──該是索求報償的時候囉~
唯一的好友的唯一貢獻,是獻上他唯一的……肉體?
(喂!你的槍是對準哪裡!)
☆收錄最病人物設定:偏執狂的100種(?)症狀
人物介紹:
林雪
年齡:23歲
特色:有病!
個性:有病!
賓銳
年齡:27歲
特色:警界新星+花叢老手
個性:性格圓滑,但處事卻頗有原則,遇上各種奇妙(?)的危機時,都能用聰明的手段順利化解。
作者簡介:
出生:1989.2.28
興趣:小說、電影、音樂
喜歡的食物:生魚片、拉麵、烤肉……
討厭的食物:肝臟、牛奶、蘿蔔……
性格優點:脾氣好好先生
性格弱點:脾氣好好先生
目標:寫文寫到死
FB:https://www.facebook.com/zhenyu.zhou.902
章節試閱
「你們縫合傷口,我去下洗手間。」林雪脫掉了血淋淋的橡膠手套,說了一句話,也不等其他人反應便推開有些破損的門離開了。他徑直走進了洗手間,從自己的衣服內側拿出了手機,上面顯示了整整三十四個未接來電。
都是同一個人——許雁。
手機再次震動起來,許雁的第三十五個電話來了。林雪接通了電話,放到耳邊,卻沒有說話,沉默著等著手機對面的反應。
「你在醫院,對吧?」許雁的聲音很平靜,沒有憤怒,沒有焦急,有的只是一種看似柔弱卻極為頑固的篤定,「這便是你最後想做的事?」
「別亂想……是妳睡眠不足,該好好休息了,晚安。...
都是同一個人——許雁。
手機再次震動起來,許雁的第三十五個電話來了。林雪接通了電話,放到耳邊,卻沒有說話,沉默著等著手機對面的反應。
「你在醫院,對吧?」許雁的聲音很平靜,沒有憤怒,沒有焦急,有的只是一種看似柔弱卻極為頑固的篤定,「這便是你最後想做的事?」
「別亂想……是妳睡眠不足,該好好休息了,晚安。...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怪異的天才
第二章 綠色的髮絲
第三章 死亡的腳步
第四章 影子的追捕
第五章 講理的新人
第六章 野豬和家豬
第七章 林風的謀略
第八章 風雪的世界
第九章 林雪的敗北
第十章 原液的救贖
第十一章 內局的人們
後記
第二章 綠色的髮絲
第三章 死亡的腳步
第四章 影子的追捕
第五章 講理的新人
第六章 野豬和家豬
第七章 林風的謀略
第八章 風雪的世界
第九章 林雪的敗北
第十章 原液的救贖
第十一章 內局的人們
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千川雪
- 出版社: 鮮鮮文化事業 出版日期:2013-09-06 ISBN/ISSN:978986303932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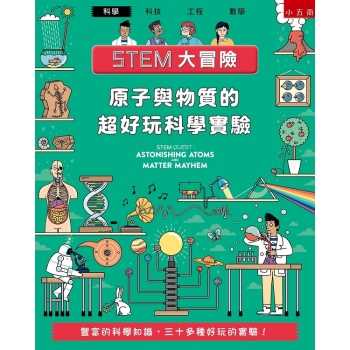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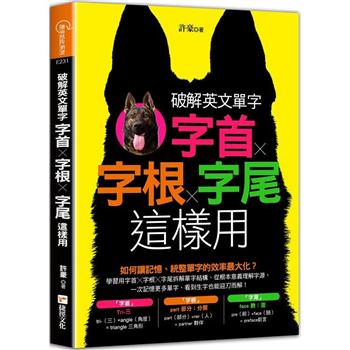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