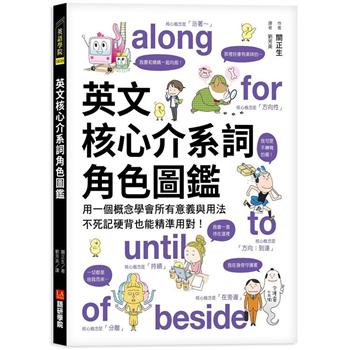節錄自〈電視與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的自我統治之理想模型。電視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形式,曾經被設想為最能代表公共領域的具體展現。表面上,電視似乎是一個公共競技場的複合體,容許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個人或團體自由參與。電視似乎包容不同意識型態的修辭、論述,從而構成一個可以進行共同討論的社會空間。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多元性」只是電視的表象。媒體社會學戳破了這層表象,而直接揭露電視背後看不見的行動結構。依循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Oevermann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將這種電視背後獨特的行動結構界定為自我搬演的邏輯。從經驗研究中,我們也發現,這個自我搬演的結構邏輯同樣適用於對臺灣電視傳播運作的解釋上。 作為理論性的鋪陳,本文目前只能侷限於針對這個電視結構的相關理論問題上面,做為未來進行更大範圍的經驗研究之理論指引。
我們由經驗研究的成果得到以下的命題,並據以構築理論論述:
第一,電視傳播的自我搬演之結構邏輯混淆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分,並邏輯一致地使得哈伯瑪斯所設想的公共領域理想模型成為不可能。
第二,電視不但沒有形成公共領域,反而製造出「假共同體」。它透過模擬人身親近關係的情緒共同體的方式,使得人類的社會關係重新封建化。
第三,電視生產出「假公共領域」。它壓制客體實在的紀錄及其傳送,以利於運作出自身的自我搬演。缺乏真摯性的電視之自我搬演,摒除了公共領域的理想,反而仍然在文化工業的理論範圍內進行變異。
一、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
「公共領域」的問題,由於哈伯瑪斯1962年出版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而得到西方學術界廣泛的注意。 隨著其1990年代英譯本的出版,公共領域的議題,也在英語世界與臺灣學界得到廣泛迴響。公共領域變成是一個針對大眾媒體的規範性概念,形成對電視運作與大眾媒體進行批判的判準。
不同於西方現代性歷史脈絡中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的二分,「公共領域」在哈氏的理論體系中有著獨特的位置。概括而言,公共領域是一種在溝通行動中產生的社會空間,它是民主化社會對公共議題進行理性論辯的場所,它必須向社會中的行動者保持一種平等、開放的地位。 因此它的重要特徵在於理論論述產生的可能性,並且期待達成共識。它實際上的動力來自於「真理越辯越明」的邏輯,以構成公民社會主要的自主性力量,推動政治行動的理性化。
媒體只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但是媒體卻是唯一使得公共溝通長期持續維持的力量,並使得公共溝通得以為整個社會的成員觀察得到。公共領域藉由媒體而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成為政治運作與討論的平臺。按照哈伯瑪斯的看法,公共領域主要依賴三組行動者在運作:第一組行動者是利益團體,他們可以是政黨利益的代表者,也可以是商業利益代表者或是專門職業團體;第二組行動者是由從事自我指涉性的認同政治之社會運動者所構成,他們設定特定的政治目標,在公共領域中設定議題,並參與到公共領域結構的再生產之中;第三組行動者則是新聞工作者,他們蒐集資訊,決定節目的選擇與表現形態,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資訊的流通。 在大眾傳播高度分殊化的社會之中,這三者其實早已交織在一起。
隨著晚近媒體環境的歷史性轉變,掌控資訊流通的媒體,事實上早已藉由對資訊的選擇過程變成一種新型的權力。情勢與1960年代哈伯瑪斯寫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時相比有著極大的變化,某些媒體社會學者甚至稱之為「新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在1960年代,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論述有其當時時代的需要,它面對的是在二次大戰之後,西德由納粹德國轉型為先進民主社會的獨特歷史情境。「代表型的公共領域」早已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由大眾媒體生產製造的公共領域,它取代了公眾,事實上並由政黨的利益與商業組織的利益所占據,使得公共領域「再封建化」。「公眾的批判意識成為再封建化過程的犧牲品。」 公眾的自主性意見形成的過程受到大眾媒體的干擾,除非公共領域形成一種「批判的公共性」,否則具有自主性的公共領域無法形成。
在1990年代,哈伯瑪斯建構其法哲學的基本理論時,公共領域的主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大眾媒體應該將自身理解為一個已啟蒙的公眾代理人,並預設、要求及強化公眾學習的準備與批判的能力;與司法相似地,大眾媒體應該保持其與政治行動者和社會行動者的獨立性;大眾媒體應該不偏袒任何黨派地接受公眾的請求與建議,並在這些主題與建議的光照之下,並將政治過程置於合法化的強制與被增強的批判之中。」 在這種公共領域的理想模型之中,必須首先將媒體的權力中立化,公共領域才有建立的可能。
在政治的功能上,相對於密室政治,大眾媒體可以幫助公開透明的民主社會意見的形成,其實現有賴於公共溝通與公民社會的密切結合。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之「代表型的民主」,公民社會依賴於具有理性論述與行動能力的公民與公民團體,自主地形成公共議題,將公共議題置入公共領域的討論,最終並在法制化的過程中影響政治決策。這是一個依賴於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才得以運作的民主的自我統治。
在今天特殊的歷史條件之中,公民社會構成的核心在於那些非政府的、非經濟的連結與自願性的團體,透過他們自發性的聯合、組織、運動,使得在私人領域運作的社會問題情境得以被發現,並形成公共議題,逼迫政治公共領域加以處理。公民社會的首要任務在於將公共議題納入建制化的論述性空間之中,並以商談的民主、平等、開放的程序展開溝通行動。 換言之,公共領域其實是,在其社會學的意義上,民主社會中溝通的結構。同時,一個有活力的公民社會也仰賴於一種自由的政治文化,它所涉及的是行動者的行動結構。比較被一般公共領域討論忽略的是,這種自由的政治行動結構有其相應的社會化基礎。在政治的權威主義與家庭的「權威人格」仍然起主導作用的社會(如東亞),這種自發性公民社會與自主性的公共領域的形成仍然有著極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論述中,隱而不顯的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誠如哈氏早年的分析,公眾早已分裂為無法公開論述的少數專家與大多數文化消費的大眾,兩者均不具備公共批判的能力。 知識分子的高度菁英化,與大眾媒體中介的公眾距離愈來愈遠,理性論辯所仰賴的知識能力要去何處尋找?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結構詮釋學:Oevermann與德國社會學的轉向的圖書 |
 |
結構詮釋學:Oevermann與德國社會學的轉向 出版日期:2018-02-1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6 |
Others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社會 |
$ 246 |
Others |
$ 252 |
社會學 |
$ 252 |
社會學總論 |
$ 252 |
社會 |
$ 25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結構詮釋學:Oevermann與德國社會學的轉向
Oevermann將詮釋學的德國系譜推向另一個理論高峰,「序列分析」的方法解決了阿多諾與波普在一九六○年代的實證主義論戰後所留下來的方法論難題,「生活實踐」理論所強調的「危機與常規的辯證」也形同推翻了Oevermann的老師哈伯瑪斯在《溝通行動理論》一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架構。作為一種獨特的黑格爾辯證哲學與李維史陀結構主義的巧妙融合,結構詮釋學也超越了布迪厄略嫌僵化的結構主義社會學。
Sociology
MIT
系列叢書(唐山出版社)
臺灣人對自己的家鄉—「臺灣」,所做的社會研究論集系列叢書
主要是探討臺灣的人們自己所生活的地方
為了讓大家清楚了解自己所接觸之人、居住的環境、城鎮之活動等社會現象
收錄各種臺灣社會議題,正是此系列叢書存在之意義
Sociology MIT
許嘉猷《藝術之眼:布爾迪厄的藝術社會學理論及其在臺灣之量化與質化研究》
許嘉猷《藝術與文化社會學新論》
黃聖哲《美學經驗的社會構成》
黃聖哲《結構詮釋學:Oevermann與德國社會學的轉向》
作者簡介:
1964年生,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專任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最高學歷: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師承Ulrich Oevermann的結構詮釋學學派。
著作《美學經驗的社會構成》(唐山,2013)。
章節試閱
節錄自〈電視與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的自我統治之理想模型。電視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形式,曾經被設想為最能代表公共領域的具體展現。表面上,電視似乎是一個公共競技場的複合體,容許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個人或團體自由參與。電視似乎包容不同意識型態的修辭、論述,從而構成一個可以進行共同討論的社會空間。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多元性」只是電視的表象。媒體社會學戳破了這層表象,而直接揭露電視背後看不見的行動結構。依循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Oevermann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將這種電視背後獨特的行動結構界定為自我...
公共領域是民主的自我統治之理想模型。電視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形式,曾經被設想為最能代表公共領域的具體展現。表面上,電視似乎是一個公共競技場的複合體,容許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個人或團體自由參與。電視似乎包容不同意識型態的修辭、論述,從而構成一個可以進行共同討論的社會空間。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多元性」只是電視的表象。媒體社會學戳破了這層表象,而直接揭露電視背後看不見的行動結構。依循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Oevermann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將這種電視背後獨特的行動結構界定為自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結構詮釋學:Oevermann與德國社會學的轉向》
作者序
PART 1 方法論基礎
第一章 意義的結構:結構詮釋學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
第二章 個案重建的邏輯
PART 2 社會學諸面向
第三章 社會性的雙重結構
第四章 危機與宗教性:論Oevermann的宗教社會學
第五章 危機與自我的形成:論Oevermann的社會化理論
第六章 生活風格的自我搬演
第七章 電視與公共領域
PART 3 經驗研究範例
第八章 電視新聞的自我搬演
參考書目
西文部分
中文部分
作者序
PART 1 方法論基礎
第一章 意義的結構:結構詮釋學作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
第二章 個案重建的邏輯
PART 2 社會學諸面向
第三章 社會性的雙重結構
第四章 危機與宗教性:論Oevermann的宗教社會學
第五章 危機與自我的形成:論Oevermann的社會化理論
第六章 生活風格的自我搬演
第七章 電視與公共領域
PART 3 經驗研究範例
第八章 電視新聞的自我搬演
參考書目
西文部分
中文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