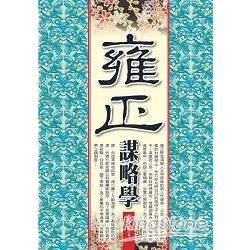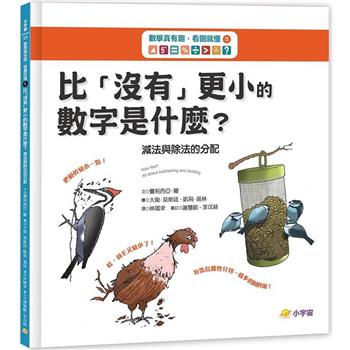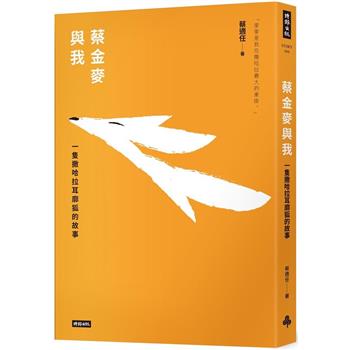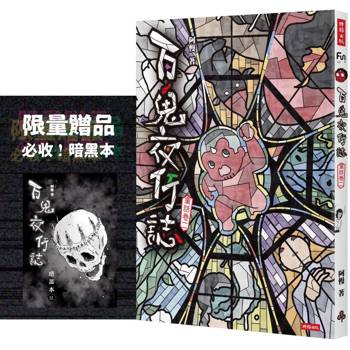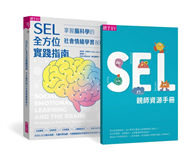雍正,即是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第三代皇帝,又是一個臨近近代門檻的封建皇帝。他的洞察力極強,從狩獵中深深領悟到野狼的核心內涵︰一是敏銳的洞察力,善於捕捉時機;二是不屈不撓的精神,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三是群體作戰,威猛無比;四是奉獻精神,為了集體犧牲個人利益。他將此四點總結出一套影響其一生所作所為的刁鑽狠辣狼性之道,並身體力行將狼性之道貫穿於爭位和統治的過程中,把大清推向了輝煌極至。
本書從狼性的角度,透過對雍正皇帝奪位、固權、懲貪、馭人和掌權等五個方面成敗得失的深入剖析,為讀者諸君提供了一副用野狼眼看世界的放大鏡,願您在事業奮鬥的道路上,能夠多一點狼性,少一點羊性。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雍正謀略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2 |
人文歷史 |
$ 196 |
社會人文 |
$ 202 |
中文書 |
$ 202 |
歷史人物 |
$ 207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雍正謀略學
內容簡介
目錄
第一章 冷眼旁觀,坐收漁翁之利
「秋獮」之中悟狼性
「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
抓住機會,打出致勝的「皇孫牌」
第二章 進退有度,露與藏巧把握
向狼族學智慧的「天下第一閒人」
潛龍在淵,巧布勝局
「不逐是逐,逐是不逐。」
揚長避短,借允祥之力巧收軍心
第三章 隱忍待機,先布局後出手
果斷出招,收兵權絕不手軟
剪除羽翼,收拾強敵
快意恩仇,樹立君威
第四章 八面玲瓏,時時留下退路
麻痹對手,創造可乘之機
設離間計,削弱對手實力
後發制人,反敗為勝
笑到最後的人,才是勝利者
第五章 戒急用忍,不要感情用事
皇帝也需要擁有狼一般的耐性
帝心難測,用人疑時也要用
戒急用忍,巧穩悍將
借助「麻醉劑」,讓臣下乖乖聽命
第六章 心思已定,執行到底
狼族不相信眼淚
以大丈夫的硬心腸,發狠做去!
借題發揮,上綱上線
小題大做,殺雞用牛刀
祕密立儲,刻意栽培嗣主
第七章 唯我獨尊,天生傲骨
改革旗務,不許他人染指皇權
過河拆橋,隆科多囚禁暢春園
輕曾重呂,在全國大興「洗腦術」
棄車保帥,讓別人當替罪羊
第八章 心狠手辣,以毒攻毒
當機立斷,非常之時敢行非常之舉
先發制人,置對手於死地
栽贓嫁禍,強加罪名,逼對手就範
利用矛盾,巧妙借用第三者除掉對手
斬草除根,不給自己留下後患
第九章 大刀闊斧振百年頹風
子改父規,「攤丁入糧」
不力除此弊者,必治以重罪
嚴加約束,不可因私而廢公。
徇私結黨之惡習不可原諒
第十章 高薪養廉,貪者必誅
不再縱容官員剝削老百姓
稅制的大改革
禁官場送禮陋習,必先禁收禮之上司
「秋獮」之中悟狼性
「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
抓住機會,打出致勝的「皇孫牌」
第二章 進退有度,露與藏巧把握
向狼族學智慧的「天下第一閒人」
潛龍在淵,巧布勝局
「不逐是逐,逐是不逐。」
揚長避短,借允祥之力巧收軍心
第三章 隱忍待機,先布局後出手
果斷出招,收兵權絕不手軟
剪除羽翼,收拾強敵
快意恩仇,樹立君威
第四章 八面玲瓏,時時留下退路
麻痹對手,創造可乘之機
設離間計,削弱對手實力
後發制人,反敗為勝
笑到最後的人,才是勝利者
第五章 戒急用忍,不要感情用事
皇帝也需要擁有狼一般的耐性
帝心難測,用人疑時也要用
戒急用忍,巧穩悍將
借助「麻醉劑」,讓臣下乖乖聽命
第六章 心思已定,執行到底
狼族不相信眼淚
以大丈夫的硬心腸,發狠做去!
借題發揮,上綱上線
小題大做,殺雞用牛刀
祕密立儲,刻意栽培嗣主
第七章 唯我獨尊,天生傲骨
改革旗務,不許他人染指皇權
過河拆橋,隆科多囚禁暢春園
輕曾重呂,在全國大興「洗腦術」
棄車保帥,讓別人當替罪羊
第八章 心狠手辣,以毒攻毒
當機立斷,非常之時敢行非常之舉
先發制人,置對手於死地
栽贓嫁禍,強加罪名,逼對手就範
利用矛盾,巧妙借用第三者除掉對手
斬草除根,不給自己留下後患
第九章 大刀闊斧振百年頹風
子改父規,「攤丁入糧」
不力除此弊者,必治以重罪
嚴加約束,不可因私而廢公。
徇私結黨之惡習不可原諒
第十章 高薪養廉,貪者必誅
不再縱容官員剝削老百姓
稅制的大改革
禁官場送禮陋習,必先禁收禮之上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