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更鳥之死
四月二日
星期六
中午
格林家血案是菲洛.萬斯以非正式檢察官身分參與調查的刑事案件中,最讓人感到驚悚、離奇和難以理解的案件。這樁發生在格林豪宅內的凶殺案,直至十二月才宣告破案,出人意料的結局,令人為之扼腕!
這下子,萬斯終於閒了下來,有了這段空檔,他穿上休閒服到瑞士去度他的萬聖節了。二月底,他回到紐約,開始專心於他的文學翻譯工作――本世紀從古埃及經典文學中發現的梅蘭.托勒斯的著作殘片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這項枯燥乏味的翻譯工程,萬斯竟津津有味地研究了一個多月。
這段時間,萬斯過得很平靜,沒有受到任何干擾。儘管萬斯一直熱中於文化研究,但對這份翻譯工作並沒有十足的把握。他那份對知性世界的冒險精神、追究根源的執著勁往往與研究學問必須的淡定與耐心產生衝突。據我所知,萬斯早在幾年前就已著手寫作贊諾芬的傳記――大學時期初讀的《希臘遠征波斯記》和《蘇格拉底回憶錄》給了他這樣的靈感――然而,在寫到贊諾芬戰敗,帶領一萬人馬渡海逃亡的時候,他就不再對贊諾芬感興趣了。鑒於上次的經驗,這一次著手做的翻譯工作,也很快在四月份擱淺。此後的幾個星期,外界一直充斥著某種邪惡的氣氛,又一樁離奇的謀殺事件,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當中。
在這起謀殺事件的調查取證中,萬斯充當了紐約州地方檢察官約翰.馬克漢的法庭助理。不久之後,案件便以「主教謀殺案」的名號轟動一時。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樣的說法――基於那些新聞從業者的本能而被賦予的――並不確切。事實上,這起血腥殘忍、泯滅人性的暴行和神聖的主教大人,一點瓜葛也沒有,不過是借用那本《鵝媽媽童謠》增加人們恐怖的想像罷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這一名號也很恰當――兇手基於他那殘忍的殺人陰謀,使用了「主教」這樣的代稱。但也恰恰是這個讓人匪夷所思的稱號,給萬斯提供了一條關鍵的線索,使他最終偵破了這起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案件,揭露了出人意料的殘酷真相。
毫無頭緒的案情現場,讓人毛骨悚然的殺人手法,足以讓梅蘭.托勒斯和古希臘的一行詩從萬斯的心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凶案發生於四月二日的早上,距離格林豪宅發生的朱利亞與契斯特遭槍殺的案件不足五個月。
此時恰逢初春時節,和煦的陽光照耀著紐約,是個讓人神清氣爽的春日。萬斯正在自家公寓的屋頂花園內享受豐盛的早餐――儘管已經快到正午時分了。有時,時間對於萬斯來說,並不具有任何的約束意義。工作經常持續到半夜,閱讀書籍直到拂曉時分,然後再回去睡覺。
溫暖的陽光曬得人懶洋洋的,萬斯脫下睡袍,攤開四肢躺在安樂椅上,以他那一貫的桀驁不馴,又略帶慵懶的眼神瞥著花園裡的樹梢枝頭。旁邊的矮几上放著早餐。我知道,萬斯又在想事情了。每到春天,他都會去一趟法國。就像喬治.摩爾那樣,在他的腦海中,巴黎和五月早已融為一體了。然而戰後,蜂擁至法國的那些美國暴發戶們,完全破壞了每年的這一好興致,他終於在昨天作出決定,取消今年的法國巡禮活動,整個夏天都留在紐約。
我――范達因,作為萬斯的朋友兼法律顧問,早在幾年前,就辭掉了在父親的律師事務所裡的工作,一心一意為萬斯做事――和那些正襟危坐,氣氛嚴肅的律師事務所裡的工作相比,我更喜歡現在的職業。我在西岸旅館有一間單人房,不過我在萬斯公寓裡度過的時間,遠比在旅館裡消磨的時日多得多。
這天早晨,當我到達公寓的時候,萬斯還沒有起床。將這個月的帳目全部處理完畢之後,我就坐在一旁抽著煙。此時,萬斯正吃著他的早餐。
「老范,」萬斯用他那慣有的滿不在乎的口氣對我說,「不管是春天,還是夏天,紐約簡直都沒勁兒透了,一點兒也不浪漫。每天這麼無所事事,真是無聊啊!不過話又說回來,總比到歐洲和一群鄉巴佬似的觀光客,擠在一起要好得多……那簡直太令人掃興了。」
恐怕萬斯做夢也沒想到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所發生的事情。浪漫的巴黎和這些比起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主教殺人事件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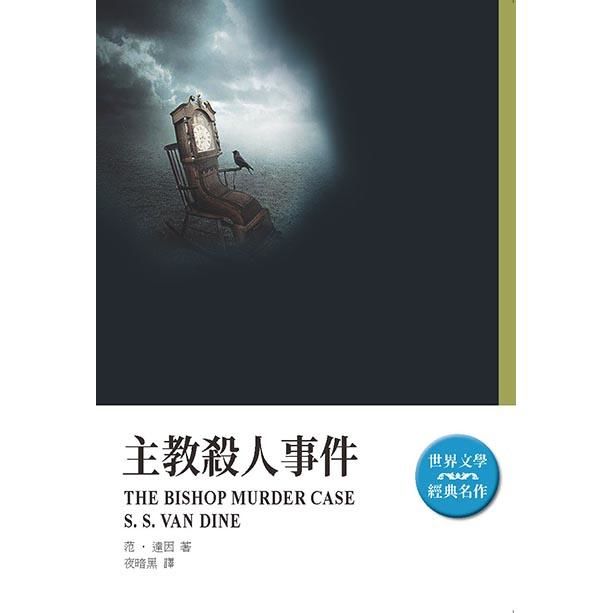 |
主教殺人事件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37 |
推理/驚悚小說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英美文學 |
$ 270 |
翻譯推理/犯罪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主教殺人事件
美國殿堂級本格推理大師的巔峰力作,刷新世界圖書銷量紀錄的血腥童話。
最離奇、最驚悚、最令人髮指的殺人命案。
幽暗的童謠宛如惡魔譜下的追魂曲,
彷彿召喚躲在一旁的死神。
陰沉的聲音令人不寒而慄,
血腥遊戲不斷升級,
主教的魔爪又在伸向誰?
第一位死者被人用箭射穿心臟,第二位死者被槍射穿頭部,第三位死者從高牆上摔死……署名「主教」的殘酷凶手不斷地刻意提供線索,一連串令人不寒而慄的離奇命案,竟然與一首家喻戶曉的古老童謠完全吻合!
――是誰殺了小知更鳥?
「是我。」麻雀回答。
「我用弓和箭射死了小知更鳥!」
陰暗、幽沉的童謠宛如惡魔譜下的追魂曲一般,預示著一幕幕血腥的慘劇,死亡的陰影霎時籠罩了整個紐約……誰是藏在幕後的黑色主教?他為什麼製造謀殺又提供線索,如幽靈般若隱若現?一切究竟隱藏著什麼天大陰謀?
作者簡介:
范.達因(S.S.Van Dine,1888.10.15~1939.4.11),美國作家與評論家,歐美推理小說黃金時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對後世推理小說的創作影響很大,本書是最能體現作者風格的一部作品,用了很多篇幅分析了數學家的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並以此作為破案的心理依據,書中涉及的許多數學、物理、天文和西洋棋知識,知識涵蓋層面較為深廣,這一點在一般的推理小說中都是極少見的,涉案人物幾乎都是科學家、數學家,採用的是典型的童謠模式,頗能烘托出恐怖詭異的氣氛。
章節試閱
小知更鳥之死
四月二日
星期六
中午
格林家血案是菲洛.萬斯以非正式檢察官身分參與調查的刑事案件中,最讓人感到驚悚、離奇和難以理解的案件。這樁發生在格林豪宅內的凶殺案,直至十二月才宣告破案,出人意料的結局,令人為之扼腕!
這下子,萬斯終於閒了下來,有了這段空檔,他穿上休閒服到瑞士去度他的萬聖節了。二月底,他回到紐約,開始專心於他的文學翻譯工作――本世紀從古埃及經典文學中發現的梅蘭.托勒斯的著作殘片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這項枯燥乏味的翻譯工程,萬斯竟津津有味地研究了一個多月。
這段時間,萬斯過得很平...
四月二日
星期六
中午
格林家血案是菲洛.萬斯以非正式檢察官身分參與調查的刑事案件中,最讓人感到驚悚、離奇和難以理解的案件。這樁發生在格林豪宅內的凶殺案,直至十二月才宣告破案,出人意料的結局,令人為之扼腕!
這下子,萬斯終於閒了下來,有了這段空檔,他穿上休閒服到瑞士去度他的萬聖節了。二月底,他回到紐約,開始專心於他的文學翻譯工作――本世紀從古埃及經典文學中發現的梅蘭.托勒斯的著作殘片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這項枯燥乏味的翻譯工程,萬斯竟津津有味地研究了一個多月。
這段時間,萬斯過得很平...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小知更鳥之死
致命弓箭
咒怨
神祕字條
驚魂慘叫
「我是兇手」
疑雲密布
再現血案
死亡密碼
是誰在說謊
不翼而飛的手槍
午夜訪客
黑色的主教
巔峰對決
拜訪帕第
駝背的憂鬱
長明燈下的死屍
石牆上的血跡
不祥的筆記本
一籌莫展
陰謀與數學
詭異的紙牌屋
顯露端倪
離奇失蹤的瑪蒂
撥雲見日
救贖
致命弓箭
咒怨
神祕字條
驚魂慘叫
「我是兇手」
疑雲密布
再現血案
死亡密碼
是誰在說謊
不翼而飛的手槍
午夜訪客
黑色的主教
巔峰對決
拜訪帕第
駝背的憂鬱
長明燈下的死屍
石牆上的血跡
不祥的筆記本
一籌莫展
陰謀與數學
詭異的紙牌屋
顯露端倪
離奇失蹤的瑪蒂
撥雲見日
救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