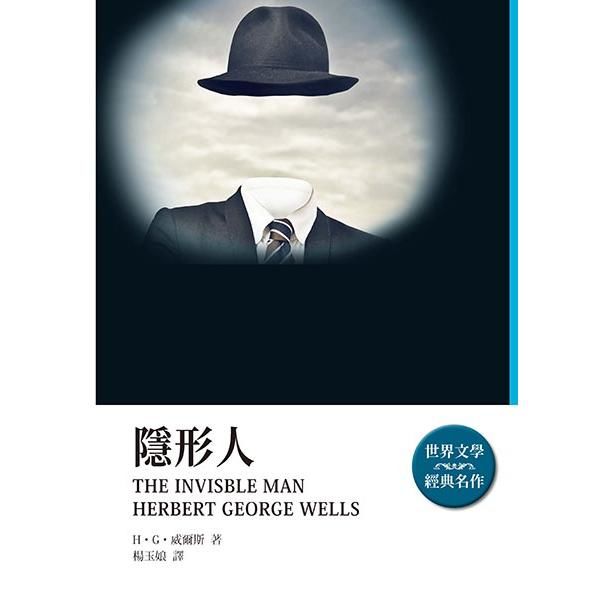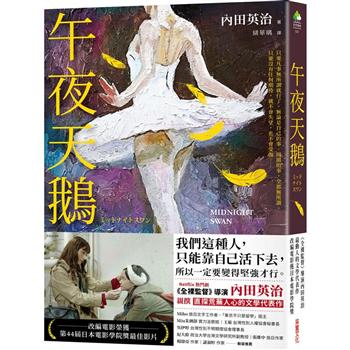怪客初到
那怪客是在一個寒冷的二月天的大清早,頂著刺骨寒風,穿越鵝絨細雪而來。這是那一年裡的最後一場降雪。他手戴厚厚的手套,拎著一個黑色小旅行皮箱,踩著綿綿雪地,看樣子像是打從「荊棘林火車站」出來的。他從頭到腳裹著保暖衣物,頭上的軟氈帽帽沿遮去整張臉龐的每一吋地方,只露出一點光亮的鼻尖。雪花堆積在他的肩頭和胸坎,又為所攜的行李上頭添加一頂白冠。這人蹣跚跨入「車馬棧」,擱下小皮箱。客棧裡死氣沈沈,感受不到半點活力。「火!」他嚷著:「看在老天爺份上,快給個房間,燒盆火!」他跺跺腳,在櫃台處抖掉一身雪花,跟隨賀爾太太走入她的客房,議訂住宿價格。經過一番詳盡介紹後,他欣然認可房錢,擲了兩枚金鎊在桌上,住進這家客棧。
賀爾太太生好火,撇下他,下去為他親手調理一頓正餐。冬天裡能有客人在宜賓落腳,本來就是樁聞所未聞的奇事,更甭說是這麼個全然不「討價還價」的客人了。賀爾太太決心好好露兩手,以顯示自己當得起如此好運。等到燻肉燻得差不多,手腳遲頓的助手蜜莉也在連遭她擺了幾個司空見慣的鄙夷表情以後表現得利落些了。她很快帶著餐巾、端著杯盤來到客房,以最隆重的姿態擺設這些東西。她驚訝地發現,儘管爐火燒得正旺,那人依舊頭戴帽子、身穿大衣,背對著她站在窗口,凝視院子裡頭紛紛飄墜的雪花,兩手交疊在背後,彷彿正在沈思。她注意到依然在他肩頭閃著銀光的溶雪,正一滴滴滴落到自己的地毯上。
「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大衣和帽子,」她說:「拿到廚房去給它徹底烘乾。」
「不!」他頭也不回地應聲。
她不確定那人是否聽到自己的問話,正要重覆一聲。
他扭過頭來,注視著她,加重語氣表示:「我寧可照舊穿戴著。」
她注意到他戴著一副配有偏光鏡片的藍色大眼鏡,大衣領子以上又蓄著把濃濃密密的落腮鬍,把整個面部和兩頰全給遮住了。
「很好,先生!」她說:「隨你的便吧!要不了一會兒,房裡就會溫暖多啦!」他再度把臉別開,沒有答腔。賀爾太太感到這不是藉著交談來對他表示友善的好時機,於是迅速擺好剩下的餐具,然後快步離開。等她回來時,那人仍舊像尊石像般佇立原地,弓著背,衣領上翻,溼淋淋的帽沿向下壓,徹底遮蓋臉龐和雙耳。
她鄭重其事地放下蛋和燻肉,與其說是在對他說,倒不如說是在對他喊:「先生,你的午餐準備好啦!」
「謝謝!」他立即應聲,人卻動也不動,直到她帶上房門,這才趕緊轉過身來,迫不及待地疾走到桌旁。
她剛從吧台後走向廚房,就聽見某個聲音以規律的音程在周而復始地響著。吱嘎,吱嘎,吱嘎!是一支湯匙在淺盆裡疾速攪動的聲音。
「那女孩!」她輕呼:「呀呀!我都給忘啦!都大半天了。她可真能蘑菇!」於是她親自接手完成攪拌芥末的工作,同時為蜜莉的拖拖拉拉狠狠數落她幾句。她都已經煎好火腿、煮好蛋,擺好了餐桌,做好每一件事情,而蜜莉(助手;真是!)卻搞了半天,還沒把芥末醬調好。那一頭可是個想要住宿的新客人呢!她忙慎滿了芥末罐,鄭重萬分地用一個黑金雙色的茶盤托著端進客房。
她敲敲門,快步往裡走。她的房客聽見聲響,急急忙忙移動,因此她只匆匆瞥見一個白色的物體在餐桌後方消失蹤影,看起來就像他正要從地上拾起什麼東西似的。她用芥末罐敲敲桌面,這才注意到客人已經脫下大衣、帽子,擱在爐前的一把椅子上,一雙溼答答的靴子大有要把她的鋼鐵炭欄滴得生誘之勢。她斷然朝那些東西走去,以不容拒絕的口吻表示:「我看現在我該可以把它們烘乾了。」
「別動帽子!」客人發出沈悶的聲音。她一扭頭,看見對方已經抬起頭來,正坐在椅子上對著她望。
她目瞪口呆,望著他,一時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他手持一方白布――是一條餐巾――掩住臉龐下半部,因此整個嘴巴和上下顎全被遮住了,講話的聲音也才會顯得那麼窒悶。但賀爾太太吃驚的不是這個,而是事實上,他的整個額頭在那副藍彩的眼鏡以上,全被一條繃帶蓋住了,另一條繃帶則遮去他的雙耳,偌大的臉部只暴露出淡紅色的尖鼻;而那鼻子還像最初一樣紅潤、光澤、醒目。他身上穿著一件天鵝絨夾克,黑色的亞麻布裡襯高領向上翻起,圍住了脖子;濃密的黑髮竭盡所能地自兩條交叉的繃帶之間和底下鑽出,形成好些稀奇古怪的髮束和犄角。整個外型怪異到出乎人所能想像之外的地步。她壓根兒沒料到會看到這樣一顆纏著繃帶、包得密密麻麻的頭,一時之間不由得僵在那兒。
他沒移開那方餐巾,反而用(她現在看清楚了)戴著棕色手套的手繼續拿著它擋住臉龐,戴著無法透視的藍眼鏡瞅著她,透過白布,一清二楚地交代:「別動帽子。」
她的神志開始從錯愕中恢復清醒,把那頂帽子放回爐畔的椅子上。「我不知道,先生,」她開口說道:「你――」隨即尷尬地閉上嘴巴。
「謝謝妳!」他冷冷淡淡地說著,視線由她身上飄向房門,然後又轉回她的身上。
「我一定會把它們烘得乾乾爽爽,先生―—馬上。」她說著,拿著他的衣物出了客房。將要跨出房門時,她再次瞄瞄他那裹在白布條裡的頭和藍色護目鏡;但那條餐巾依舊蒙在他的臉前。她微微冷顫,關上房門,滿臉淨是無限驚訝和困惑。「我從未……」她低聲私語:「噢!」隨即輕手輕腳地走到廚房。由於太過出神,竟然沒有一進廚房就詢問蜜莉現在在瞎忙些什麼。
客人坐下來,側耳傾聽她漸漸走遠的腳步聲,探頭探腦地瞄瞄窗口,再拿掉覆面的餐巾繼續用餐。他滿含一大口食物,疑神疑鬼地瞄瞄窗口,再吃一口,然後站起身來,手上拿著餐巾,走到房間另一頭,拉下百葉窗,一直遮到掩住下面窗板的白棉布窗簾頂上。如此一來,房裡只剩昏弱的微光,而他也才帶著較輕鬆的態度回到桌邊用餐。
「這可憐人想必是出過車禍或者動過手術什麼的。」賀爾太太說:「那些繃帶嚇了我多大一跳呵!毫無疑問。」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隱形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科幻小說 |
$ 22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25 |
英國現代文學 |
$ 225 |
歐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隱形人
一位名叫葛立芬的科學家對科學發明狂熱追求,他家境貧寒,才華橫溢,仍堅持科學研究,最後終於如願以償,發明了隱身術,然而,葛立芬沒有利用科學發明造福人類,反而妄想憑藉隱形人稱霸世界,建立恐怖統治,不顧朋友苦口婆心的勸誡,一意孤行,落得眾叛親離,最後在人們的喊打聲中含憤死去……
作者簡介:
H.G.威爾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9.21~1946.8.13),通稱H.G.威爾斯(H.G.Wells),英國小說家,創作的科幻小說對該領域影響深遠,《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是在1897年發表的小說,被視為是描寫瘋狂科學家與社會對立的傑作,講述了一位天才科學家在發明了隱身藥水之後,迷失自我最終自我毀滅的故事,作者想表達的是,在一個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裡,科學的成果非但不會造福於人,反而可能危害社會,而人性中的自私和罪惡可能會使一個有才華的科學家走上墮落和毀滅。
章節試閱
怪客初到
那怪客是在一個寒冷的二月天的大清早,頂著刺骨寒風,穿越鵝絨細雪而來。這是那一年裡的最後一場降雪。他手戴厚厚的手套,拎著一個黑色小旅行皮箱,踩著綿綿雪地,看樣子像是打從「荊棘林火車站」出來的。他從頭到腳裹著保暖衣物,頭上的軟氈帽帽沿遮去整張臉龐的每一吋地方,只露出一點光亮的鼻尖。雪花堆積在他的肩頭和胸坎,又為所攜的行李上頭添加一頂白冠。這人蹣跚跨入「車馬棧」,擱下小皮箱。客棧裡死氣沈沈,感受不到半點活力。「火!」他嚷著:「看在老天爺份上,快給個房間,燒盆火!」他跺跺腳,在櫃台處抖掉一身雪...
那怪客是在一個寒冷的二月天的大清早,頂著刺骨寒風,穿越鵝絨細雪而來。這是那一年裡的最後一場降雪。他手戴厚厚的手套,拎著一個黑色小旅行皮箱,踩著綿綿雪地,看樣子像是打從「荊棘林火車站」出來的。他從頭到腳裹著保暖衣物,頭上的軟氈帽帽沿遮去整張臉龐的每一吋地方,只露出一點光亮的鼻尖。雪花堆積在他的肩頭和胸坎,又為所攜的行李上頭添加一頂白冠。這人蹣跚跨入「車馬棧」,擱下小皮箱。客棧裡死氣沈沈,感受不到半點活力。「火!」他嚷著:「看在老天爺份上,快給個房間,燒盆火!」他跺跺腳,在櫃台處抖掉一身雪...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怪客初到
第二章 泰迪.韓福瑞先生的第一印象
第三章 無數只瓶瓶罐罐
第四章 卡斯先生會見怪客
第五章 牧師宅竊盜案
第六章 著了魔的家具
第七章 揭開怪客真面目
第八章 過路
第九章 湯瑪斯.馬威爾先生
第十章 馬威爾先生的宜賓行
第十一章 車馬棧內
第十二章 隱形人大發雷霆
第十三章 馬威爾先生逆來順受
第十四章 斯陀港邊
第十五章 奔跑的男子
第十六章 在歡樂板球員酒店
第十七章 坎普醫生的訪客
第十八章 隱形人入睡
第十九章 基本原理
第二十章 波特蘭大街之屋
第二十一章 牛津街頭
第二十二章 百貨商...
第二章 泰迪.韓福瑞先生的第一印象
第三章 無數只瓶瓶罐罐
第四章 卡斯先生會見怪客
第五章 牧師宅竊盜案
第六章 著了魔的家具
第七章 揭開怪客真面目
第八章 過路
第九章 湯瑪斯.馬威爾先生
第十章 馬威爾先生的宜賓行
第十一章 車馬棧內
第十二章 隱形人大發雷霆
第十三章 馬威爾先生逆來順受
第十四章 斯陀港邊
第十五章 奔跑的男子
第十六章 在歡樂板球員酒店
第十七章 坎普醫生的訪客
第十八章 隱形人入睡
第十九章 基本原理
第二十章 波特蘭大街之屋
第二十一章 牛津街頭
第二十二章 百貨商...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