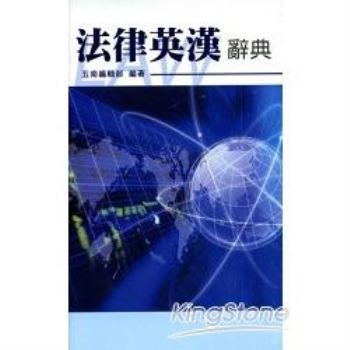真實,令人難堪的真實―—丹東
小城
置萬千生靈於一處,把壞的揀出,那籠子還能熱鬧不?―——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區有不少城鎮,風光秀美,維里埃這座小城可算得上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樓,聳著尖尖的紅瓦屋頂,疏疏密密,羅列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壯的栗樹十分密集,點出斜坡的曲折蜿蜓。杜河在舊城牆下,數百步外,源源流過。這堵城牆原先是西班牙人所築,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了。
維里埃的北面擋著一座高山,屬於庫拉山區的一條分支,每當十月乍寒,峰巒起伏的維拉峰便已蓋上皚皚白雪。山澗奔沖而下的急流,流經維里埃市,最後注入杜河,為無數鋸木廠提供了水力運轉的驅動;這是一種簡易作坊,大多數與其說是市民,還不如說是鄉民們,倒藉此得到相當的實惠。
然而,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卻並非鋸木業,而是靠織造一種叫「米魯茲」的印花布,使家家富裕起來:拿破崙倒台以來,城裡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進城,就聽到噪聲四起,震耳欲聾:那響聲是一部模樣可怕、喧鬧不堪的機器發出來的。二十只笨重的鐵錘,隨著急流沖擊水輪,忽起忽落,轟隆轟隆,震得路面發顫。每只鐵錘,一天不知能沖出幾千個釘子。鐵錘起落之間,自有一些水靈靈的漂亮小姑娘,把小鐵塊送到大鐵錘之下,一轉眼就砸成了鐵釘。
這工作看起來挺粗笨,初到法瑞邊界山區來的遊人見了,不免少見多怪。別看這釘廠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暈頭轉向,假如這遊人進入維里埃地界,問起這間光鮮的廠家是誰家的產業,別人準會拖腔拉調地回答:「啊―—那是我們市長大人的。」
維里埃的這條大街,從杜河岸邊慢慢上揚,直達山巔。遊人只要在街口停上一下子,十之八九會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樣子。
一見到他,路人紛紛脫帽致敬。他灰白頭髮,灰色衣服,胸前佩著幾枚勛章,前庭飽滿,鼻如鷹嘴;但總的說來,相貌不失為端正。第一眼望去,他眉宇之間不僅有一市之長的尊貴,還兼具壯年男子的和藹。但巴黎客人很快便會對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發覺他那自滿之中,還夾雜著某種褊狹與拘謹;最後會感到,此人的才幹只在追索欠款時不容少給分文,而輪到由他自己償債,則能拖就拖。
他就是維里埃市的市長,德.雷納先生。市長先生步履莊重,穿過街道,走進市政廳,便在旅客眼中消失了。假如這外地人接著遛躂,再走上百十來步,便會看到一座外觀相當漂亮的房子,從與屋子相連的鐵柵欄望進去,是一片婉紫嫣紅的花園。遠眺天邊,見勃艮第山脈群山隱約,十分賞心悅目。旅人如果對競逐蠅頭微利的惡濁空氣感到鬱悶的話,那麼對此清景,自有塵俗頓忘之感。
遇到當地人,便會告訴你:這就是德.雷納先生的房子。正是靠鐵釘廠的大宗贏利,市長才蓋得起這座巨石砌成的漂亮住宅;整幢房屋,還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傳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舊家世族;據稱,遠在路易十四把維里埃收入版圖之前,這個家族就已定居於此了。
一八一五年,德.雷納先生當上了維里埃的市長;從此,他對自己的實業家身分常感羞愧。須知,花園各部分的護牆也是靠他鐵器經營得法才建造得起;如今,這鮮麗繽紛的花園,層層平台,迤邐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濱了。
在德國萊比錫、法蘭克福、紐倫堡等工業城市,這類明麗怡人的花園多似繁星環抱;而在法國,卻難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區裡,誰家的庭院圍牆造得越長,石基壘得越高,就越受四鄰尊敬。雷納先生家的花園圍牆重重,格外令人嘆賞,尤其因為有幾塊圈進來的地皮是出了高價買來的。且說那雄居杜河岸邊的鋸木廠吧!進入維里埃時,劈面就會看到的。那屋頂上,你會注意到有塊橫板,上面寫著「索萊爾」三個大字。該廠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劃入雷納先生家的花園,正用來造最下一層第四道平台的護牆。
索萊爾老頭是個固執己見,無可理喻的鄉民。市長先生雖則很高傲,可為了叫老頭兒把鋸木廠遷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於那條推轉輪鋸的公共河道,雷納先生憑他在巴黎的關係,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過,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X年大選之後才得到的。
市長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遠的四頃地,才換來索萊爾這一頃地的。這個地段雖然更有利於索萊爾老爹(他發跡後,地方上都這樣稱呼)的樅木松板買賣,但他門檻精,利用鄰居的急性子和地產癖,居然敲到一筆六千法郎的巨款。
這樁交易,事後頗遭當地精明人的非議。有一次,那是四年後的一個禮拜天,雷納先生身著市長的盛裝,從教堂出來。他老遠瞧見索萊爾老爹身旁圍著三個兒子,望著他直發笑。這一笑,在市長心裡投下了一道陰影;此後,他不免常想,那次換地,本來可用更便宜的價錢成交的。
每年春上,有一幫泥水匠穿過庫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維里埃,如想贏得眾人敬重,最關鍵的是造圍牆時,千萬不可用這伙泥水匠從義大利帶來的圖樣。哪位業主一時不慎,用了這種新花樣,就會永遠落個「沒頭沒腦」的名聲;這在聰明穩健的人眼裡就體面掃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評論他人、左右輿論的,正是這批不偏不倚的聰明人。
事實上,這類聰明人言論霸道,令人生厭。大凡在巴黎這個號稱偉大的共和國住慣的人,再到內地小城來棲身,就會覺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該到這個惡劣詞兒裡去找。專橫的輿論―—這算什麼輿論―—無論在法蘭西的小城,還是在美利堅合眾國,其愚蠢都是一樣的。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紅與黑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紅與黑
于連是木匠的兒子,精明能幹富有野心,由於精通拉丁文,被選作市長家的家庭教師,市長年輕漂亮的妻子雷納夫人是在修道院長大的,對像她丈夫那樣庸俗粗魯的男人感到厭惡,於是當她見到年輕英俊且溫柔動人的于連時,漸漸對他產生了好感,于連也瘋狂地追求雷納夫人,兩個人暗通款曲,然而紙包不住火,兩人的事跡敗露,于連逃離市長家,進了神學院,經神學院院長推薦,于連到巴黎擔任拉穆爾侯爵的私人秘書,很快就得到侯爵的賞識和重用,此時于連又與侯爵的女兒瑪蒂爾德有了私情,瑪蒂爾德意外懷孕,侯爵震怒之餘做出妥協,答應了于連和女兒的婚事,然而此時卻收到了雷納夫人在教會逼迫下寫的一封告密信,使于連的飛黃騰達毀於一旦,在氣憤之下開槍擊傷深愛他的雷納夫人,也因此被送上斷頭臺,而于連竟然拒絕上訴……
作者簡介:
斯湯達爾(本名:馬利-亨利•貝爾Marie-Henri Beyle,1783.1.23~1842.3.23),筆名斯湯達爾(Stendhal),19世紀的法國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是寫實主義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展現了當時法國社會的風貌,強烈地抨擊了復辟王朝時期的貴族,教會的黑暗和資產階級新貴族的利慾薰心,反映了19世紀早期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本質問題,是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品。
章節試閱
真實,令人難堪的真實―—丹東
小城
置萬千生靈於一處,把壞的揀出,那籠子還能熱鬧不?―——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區有不少城鎮,風光秀美,維里埃這座小城可算得上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樓,聳著尖尖的紅瓦屋頂,疏疏密密,羅列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壯的栗樹十分密集,點出斜坡的曲折蜿蜓。杜河在舊城牆下,數百步外,源源流過。這堵城牆原先是西班牙人所築,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了。
維里埃的北面擋著一座高山,屬於庫拉山區的一條分支,每當十月乍寒,峰巒起伏的維拉峰便已蓋上皚皚白雪。山澗奔沖而下的急流,流經維里埃市,最後注入...
小城
置萬千生靈於一處,把壞的揀出,那籠子還能熱鬧不?―——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區有不少城鎮,風光秀美,維里埃這座小城可算得上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樓,聳著尖尖的紅瓦屋頂,疏疏密密,羅列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壯的栗樹十分密集,點出斜坡的曲折蜿蜓。杜河在舊城牆下,數百步外,源源流過。這堵城牆原先是西班牙人所築,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了。
維里埃的北面擋著一座高山,屬於庫拉山區的一條分支,每當十月乍寒,峰巒起伏的維拉峰便已蓋上皚皚白雪。山澗奔沖而下的急流,流經維里埃市,最後注入...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長
第三章 窮人的福利
第四章 父與子
第五章 討價還價
第六章 煩悶
第七章 緣分
第八章 小小的風波
第九章 鄉野一夜
第十章 雄心與逆境
第十一章 長夜悠悠
第十二章 旅行
第十三章 網眼長襪
第十四章 英國剪刀
第十五章 雞叫
第十六章 翌日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 國王蒞臨維里埃
第十九章 思考令人痛苦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與主人的談話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年的作風
第二十三章 長官的苦惱
第二十四章 省會
第二十五章 神學院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長
第三章 窮人的福利
第四章 父與子
第五章 討價還價
第六章 煩悶
第七章 緣分
第八章 小小的風波
第九章 鄉野一夜
第十章 雄心與逆境
第十一章 長夜悠悠
第十二章 旅行
第十三章 網眼長襪
第十四章 英國剪刀
第十五章 雞叫
第十六章 翌日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 國王蒞臨維里埃
第十九章 思考令人痛苦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與主人的談話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年的作風
第二十三章 長官的苦惱
第二十四章 省會
第二十五章 神學院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