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的呼喚
‧進入蠻荒
古老的流浪奔騰之渴望
摩擦著習性的鎖鏈;
再次從它的冬眠中
喚醒了不馴的野性。
巴克不看報,否則牠就會知道大禍正要臨頭――不僅對牠,而是遍及於由普吉灣到聖地牙哥這一大片濱海低地,每一條筋肉結實、毛長耐寒的狗身上。原因是跑到未開發的北極寒荒去探險的人們發現了金礦,加上輪船業者與運輸公司大肆鼓吹宣傳,促使成千上萬的人潮爭先湧向北地。這些人需要狗;需要筋骨強壯足以吃苦耐勞、毛皮厚密可以抵禦霜雪的粗壯大狗。
巴克生活在驕陽遍地的聖塔克萊拉谷中一幢大宅裡,人稱此處為米勒法官邸。它位於馬路後方,在樹林之間若隱若現。透過樹木縫隙,可以看到圍繞在它四周陰涼寬闊的走廊。高大的白楊錯落的枝條下,幾條礫石車道蜿蜒曲折地穿過廣佈的草坪通抵屋前。屋後的事事物物規模甚至比前頭更龐大。十餘名馬夫、僕役常在幾座大馬.邊高談闊論。藤蔓覆頂的傭人房舍一排又一排,外帶井然綿延不盡的附屬小屋,以及長長的葡萄藤架和翠綠的牧野,還有果園和漿果田。深水井邊設有抽水機,另外尚有一座大水泥泳池,是米勒法官的孩子們晨間游泳,和炎炎午後泡水沖涼的好地方。
這一大片領域全在巴克的統轄範圍內。牠生於斯,長於斯,已經四歲大。誠然,這裡還有別的狗。這麼遼闊的一片土地當然不可能只有一條狗,只是其它那些都不算數。牠們性情不定。有的鎮日逗留在稠密的狗舍裡,有的學起日本種哈巴狗嘟嘟或墨西哥無毛犬伊莎貝兒的調調兒―—牠們是兩隻難得把鼻尖伸到門外、四肢踏在地上的怪東西—―窩在家裡隱僻的角落裡。相對的,這裡還有至少二十隻以上的小獵狐狗。每當嘟嘟和伊莎貝兒在大批女傭手持掃帚、拖把當武器的護衛下,從窗口對她們張望時,那些獵狐犬便發出嚇人的狂吠警告這兩隻小東西。
但巴克既非膩在家裡,也不是窩在狗舍中的狗。這一大片領域都是牠的王土。牠隨法官的兒子們出獵;跳入游泳池中戲水。牠伴護法官的女兒茉莉和艾莉絲在早晨或傍晚漫長地閒步;料峭冬夜裡,熊熊的書房壁爐火焰前,牠趴在法官的腳跟邊,牠馱負法官的孫子女,推著他們在草地上打滾,或在他們貿貿然跑到馬廐外的噴水池邊、甚至更遠的圍場和漿果田時,追隨在一旁保衛。在獵狐犬間,牠傲然昂首闊步而行,對於嘟嘟和伊莎貝兒更是不屑一顧。因為牠是王者―—高高凌駕於法官邸中所有飛的、走的、爬的,包括人類之上的王者。
過去牠那體型碩大的聖伯納種父親艾爾摩曾是法官不可分離的夥伴,如今巴克也大有克紹箕裘之望。牠長得不若父親高大―—由於母親雪珀是條蘇格蘭牧羊犬,巴克體重只有一百四十磅。然而這樣的體重再加上因生活優渥而普受崇敬而帶來的威嚴,仍使牠顧盼之間流露王者之風。自幼犬時期到現在,牠始終過著飽足舒適的貴族生活。牠洋洋自得,甚至像某些因少見世面而夜郎自大的鄉紳一般,有那麼點兒狂妄自負。幸而牠並未放縱自己變成一條嬌生慣養的家居狗。追逐獵物與類似的戶外娛樂抑制了贅肉的生長,促使牠全身結實強壯。此外,跟其他浸泡冷水的動物一樣,對水的喜好也是巴克的一帖保健良方。
在克朗岱克淘金熱引來世界各地的人投入冰天雪地的北國之際,這正是巴克的狀況。時間是:一八九七年的秋天。只是巴克不看報,也不曉得那個叫曼紐的園丁助手居心不良。曼紐有個積習難改的惡癖―—他嗜賭如命。更要命的是:這人賭博時還有個大毛病—―迷信成套的打法,以致永遠翻不了身。因為賭博到成套賭金很驚人,而園丁助手的薪水卻僅勉勉強強能應付一家大小的溫飽而已。
在曼紐背主求財那個令人難忘的夜晚,法官參加一項葡萄乾農夫協會的會議去了,孩子們也在忙著籌組一個體育俱樂部,沒人看見他和巴克穿越果園而去,至於巴克本身更只以為是要出去蹓蹓腿而已。當他們到達那個叫做書院公園的信號停車站時,也只有一個—―只是一個男人看到他們。這人和曼紐交談,兩人之間錢幣聲音響叮噹。
「你要先把貨捆好、綁好,才能交給我啊。」那名陌生男子粗暴地說。於是,曼紐又用一條結實的繩索在巴克項圈底下多綁了一圈。
「揪住牠,你就算要牠不能喘氣也行。」曼紐說完,陌生人馬上冷哼一聲以示同意。
巴克帶著鎮靜的威嚴接受了那段繩索。當然,曼紐的行動絕對罕見;但牠早已學會信賴自己認識的人,和他們高超的智慧。不過等繩頭一交到陌生人手上,牠立刻發出威脅的咆哮聲。牠的咆哮只是用以宣告自己的不悅。在牠高傲的信念中,那就等於下命令。讓牠驚訝的是纏繞在脖子上的繩索竟然縮緊了,勒得牠不能呼吸。牠氣急敗壞地向那人撲去,卻在半途被對方抓著喉頭拖向身前,然後靈巧地一摜,將牠摔了個四腳朝天。在巴克暴烈的掙扎中,繩索無情地催緊。牠的舌頭垂在嘴巴外,碩大的胸膛徒勞無功地喘息著。有生以來牠從未遭受如此輕賤的對待,也從沒這麼氣憤過。可是牠的力氣消褪了;兩眼昏花了。當火車在揮舞的旗號中停下,兩名男孩將牠丟進行李車內時,牠已完全失去知覺。
等牠再度恢復意識後,巴克隱約感到自己的舌頭陣陣刺痛,身體在某種運輸工具中顛簸搖晃。通過平交道時火車發出的粗嘎尖叫,告訴牠自己身在何方。牠常常三天兩頭地跟法官出門去旅行,對於搭乘行李車早就習以為常了。牠睜開雙眼,眼中恣意流露遭綁架國王的怒氣。那人欺身而上要抓牠的喉嚨,但巴克的反應比他快多了。牠死命咬住他的手,直到又被勒得窒息才不得不鬆口。
扭打的聲音引來行李管理員,那人把手藏在後頭,對他說:「唉,這狗發病了。我正要替老板把牠帶到舊金山,那裡有個出色的獸醫應該可以治好牠的病。」
到了位於舊金山海濱的一家酒店棚屋後頭,那人又針對這趟夜車旅程,替自己滔滔雄辯。
「這一趟下來,也才不過拿到五十塊錢,」他嘀咕著:「以後就算出一千塊現金,我也絕對不幹了。」
他手上包著被血染紅了的手帕,右腳褲管從膝頭到腳踝處都被扯破了。
「另外那傢伙拿到多少?」酒店店主問。
「一百:青天為證,一個蹦子兒都不少。」那傢伙回答。
「加起來是一百五十元;」酒店老板估算了一下:「牠絕對值得;否則我就是個大笨蛋。」
那個綁匪解開血跡斑斑的包手巾,看著自己受傷的手:「就算不因此而得到了狂犬―—」
「那也是因為你注定該死的命啊!」店主哈哈大笑,又補上一句:「喂,在你把自己的份兒弄好之前,先助我一臂之力吧!」
頭昏眼花,喉嚨、舌頭劇痛難當,被勒得一條命只剩半條的巴克企圖對抗兩名施虐者,卻被他們一再掀翻、勒緊,直到他倆終於成功地銼開牠頸部沈甸甸的銅項圈,然後解開繩索,將牠丟進一個像籠子一樣的板條箱子裡。
牠躺在板條箱內調息自己的暴怒和受創的自尊,度過疲乏的殘夜。牠不曉得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陌生人要牠幹什麼?為什麼把牠禁閉在這又窄又小的板條箱子裡?牠不明所以,卻隱隱約約感到一股大難將屆的壓迫感。半夜裡,幾度棚屋門一嘩啦啦地打開,牠便一躍而起,希望見到法官,或者至少見到那些孩子們。但每次都只見酒店主人那張臃腫的臉,在藉著暈弱的油脂蠟燭光打量牠。每次在巴克喉頭顫動的喜悅吠叫,都在喉間扭轉為兇蠻的咆哮。
酒店主人任由牠去叫。到了天亮,四名男子進來抬起板條箱。看他們相貌兇惡、蓬頭亂髮、衣衫襤褸,巴克斷定這四個人也是迫害者,於是隔著板條對牠們怒目相向、猛吠猛叫。而這些人卻只是放聲大笑,拿著棍棒戳牠。巴克立即張口就咬,直到終於醒悟那正中他們的下懷,這才悻悻然地趴下來,任由他們將板條箱抬上一部貨馬車。於是,被囚禁在箱子裡的牠,開始了一段幾經轉手的旅程,途中由捷運貨物公司的職員負責照料。牠被轉到另一部貨馬車;後來又與許多各式各樣的箱子、包裹一塊兒由大卡車載上渡輪;下了船後大卡車把牠載到一座大火車站,最後終於被安置在一列特快車裡。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野性的呼喚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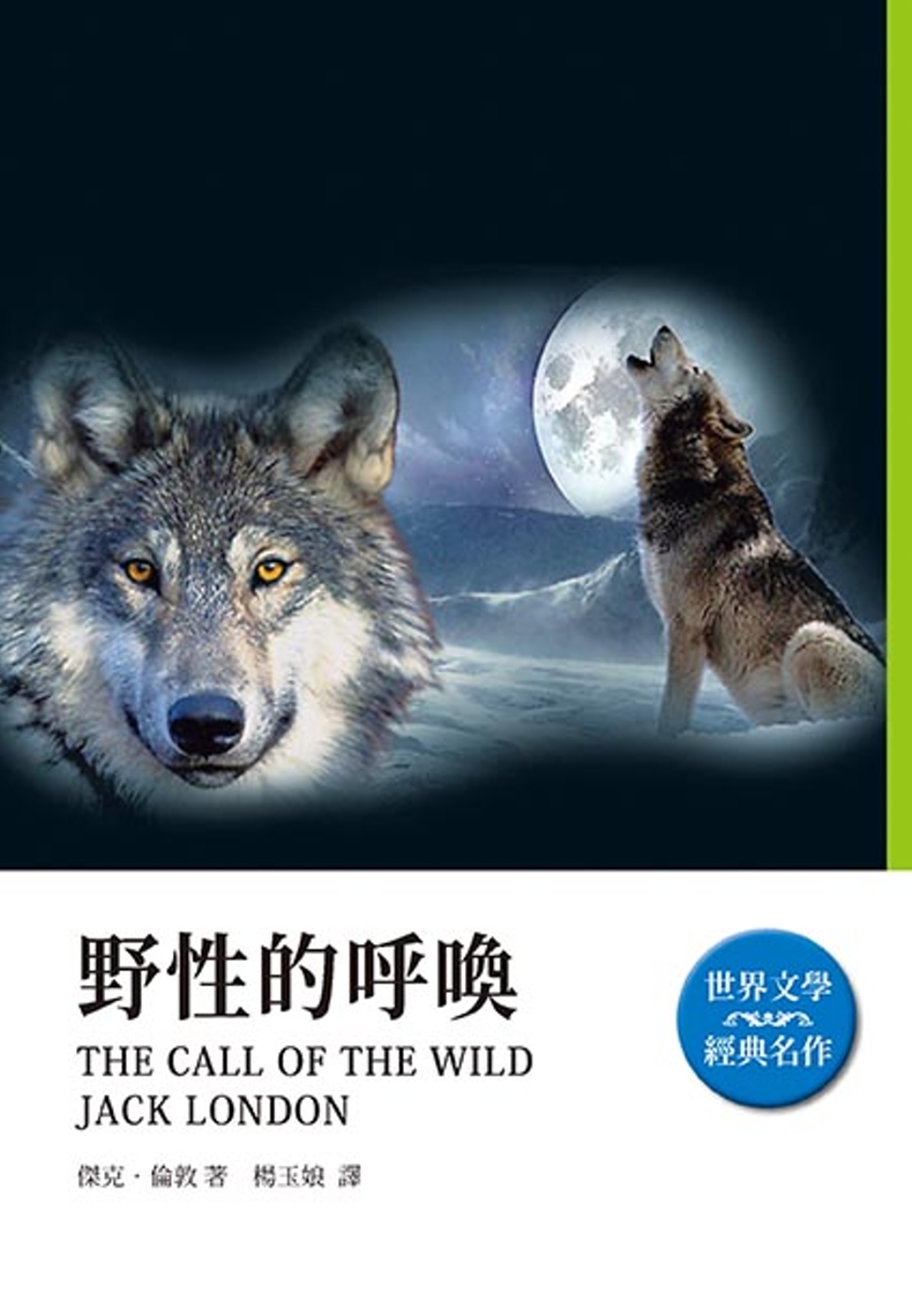 |
野性的呼喚 作者:原文 Jack Londo / 譯者:楊玉娘 出版社:天蠍座製作 出版日期:2020-10-0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92頁 / 15 x 21 x 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野性的呼喚
故事敘述一隻名叫巴克的狗歷經磨難,最終回到自然野生環境的故事。
從小生活在溫室環境中的巴克,被偷走賣到原始荒野輾轉成為雪橇犬,殘酷的現實觸動了巴克向大自然回歸的本能和意識,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巴克不斷成長,透過戰勝首領狗王而贏得了拉雪橇狗群中的頭把交椅,流落在不同主人之間,當殘暴的主人將巴克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時,新主人的解救讓巴克感受到溫暖並決定誓死效忠,但新主人的不幸遇害徹底打碎了巴克對於人類社會的留戀,從而促使巴克堅定決心,毅然走向荒野,回歸自然,成為最原始的自己……
作者簡介:
傑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12~1916.11.22),美國20世紀著名現實主義作家,1903年發表的著名動物冒險小說《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透過動物世界中人性的淪陷和野性的復發,以及彼此之間的勾心鬥角和殘酷奪權,反映了社會和心靈兩個世界的真實體驗,是美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
章節試閱
野性的呼喚
‧進入蠻荒
古老的流浪奔騰之渴望
摩擦著習性的鎖鏈;
再次從它的冬眠中
喚醒了不馴的野性。
巴克不看報,否則牠就會知道大禍正要臨頭――不僅對牠,而是遍及於由普吉灣到聖地牙哥這一大片濱海低地,每一條筋肉結實、毛長耐寒的狗身上。原因是跑到未開發的北極寒荒去探險的人們發現了金礦,加上輪船業者與運輸公司大肆鼓吹宣傳,促使成千上萬的人潮爭先湧向北地。這些人需要狗;需要筋骨強壯足以吃苦耐勞、毛皮厚密可以抵禦霜雪的粗壯大狗。
巴克生活在驕陽遍地的聖塔克萊拉谷中一幢大宅裡,人稱此處為米勒法官邸。它位於馬...
‧進入蠻荒
古老的流浪奔騰之渴望
摩擦著習性的鎖鏈;
再次從它的冬眠中
喚醒了不馴的野性。
巴克不看報,否則牠就會知道大禍正要臨頭――不僅對牠,而是遍及於由普吉灣到聖地牙哥這一大片濱海低地,每一條筋肉結實、毛長耐寒的狗身上。原因是跑到未開發的北極寒荒去探險的人們發現了金礦,加上輪船業者與運輸公司大肆鼓吹宣傳,促使成千上萬的人潮爭先湧向北地。這些人需要狗;需要筋骨強壯足以吃苦耐勞、毛皮厚密可以抵禦霜雪的粗壯大狗。
巴克生活在驕陽遍地的聖塔克萊拉谷中一幢大宅裡,人稱此處為米勒法官邸。它位於馬...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部
野性的呼喚
第二部
生火
第三部
妖怪
野性的呼喚
第二部
生火
第三部
妖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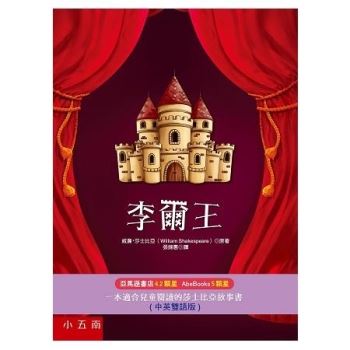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1[國民營事業]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1[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