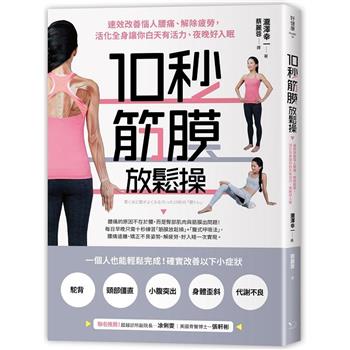在蓋內戈街的盡頭,倘若您是從碼頭上來,您就會見到新橋長廊。這是一條狹長而晦暗的走廊,從瑪扎里納街一直延伸到塞納河街。這條長廊至多有三十步長、兩步來寬;地面上鋪著淡黃色磨損、破裂的石板,時時散發著刺鼻難聞的潮濕味;尖頂玻璃天棚蓋住了長廊,上面積滿了污垢,顯得黑乎乎的。
在夏日的晴天,當驕陽灼燒著街道時,透過骯髒的玻璃天棚,一道蒼白的光在長廊上無力地蔓延開來。若是遇上冬季的壞天氣,在霧濛濛的清晨,從玻璃天棚投到粘濕的石板上的,就只是一片猥瑣而邋遢的夜色了。
左首,一些陰暗、低矮、像是被壓垮了的店鋪半埋在地下,從地下室裡不時冒出一陣陣逼人的寒氣。這兒開著舊書店、玩具店和紙板店。陳列的商品都蒙上了一層塵埃,在昏暗中毫無生氣地躺著。由一塊塊小方玻璃組成的櫥窗,折射出淺綠色的光,離奇古怪地照在這些商品上。再往裡看,在貨架後面,黑沉沉的店鋪卻像一個個陰森、淒涼的洞穴,裡面蠕動著奇形怪狀的東西。
在右首,沿著整條長廊,砌著一排牆。對面的小店主,把狹長的貨架靠牆放著,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商品,一些早在二十年前就無人問津的老古董,一順溜地擺在貨架細長的木板上,木板都漆上了非常難看的棕色。一位專賣假首飾的女店主占有了一個貨架,貨架上有一只桃心木製成的盒子,盒子上鋪著一層藍色的絲絨,店主人精心地在裡面擺上了一些只值十五個蘇(法國輔幣名,相當於二分之一法郎)的戒指。在玻璃天棚的上面,烏黑的牆繼續上砌,牆面馬馬虎虎地抹上了一道泥灰,像是染上了麻風似的,疤痕累累。
新橋長廊可不是散步的勝地。人們取道這裡,只是為了免走彎路、節省幾分鐘而已。路過這兒的都是一些忙忙碌碌的人,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快點幾抄近趕路。在這些人中,我們可以看到繫著圍裙的小伙計、帶著活兒的女工、腋下夾著大小包盒的男男女女,還有一些老頭兒,他們在從玻璃頂棚外投進來的黯淡暮色中移動著緩慢的步伐,以及一群群幼小的孩子,他們放學來到這裡奔跑喧鬧,木屐在石板上敲得震天響。
從早到晚,石板路上響著清脆、急促、凌亂的腳步聲,令人心煩意亂;沒有人說話,也沒有誰停留下來,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低著頭,急匆匆趕路,對店鋪不掃一眼。偶爾,如有過路行人在店鋪主的貨架前站定,這些小老板便會神色不安地望著他們。
傍晚,三盞煤氣燈透過方形、笨重的燈罩,照耀著長廊。這些煤氣燈嘴掛在玻璃燈罩裡,在上面投下了淡淡的黃褐色光斑,又在周圍灑下一圈圈暈白的光芒,搖搖曳曳,彷彿隨時都要熄滅似的。長廊確實像是一個凶多吉少的危險之地,巨大的陰影鋪蓋在石板上,街頭吹來了濕潤的風,它就像是三盞吊喪的燈隱隱約約照著的一條地下通道。有煤氣燈給他們的櫥窗送來一些暗淡的光做為照明,這些店鋪主也就心滿意足了。
鋪子裡,他們僅僅點亮了一盞帶著燈罩的燈,把它放在櫃台的一角,這樣,過路人就能分辨出這些在白天都顯得陰森森的洞穴裡擺設的東西。在一順排黑洞洞的鋪面上,有一家紙板店的櫥窗在閃爍,兩盞頁片形的燈放射出黃橙橙的火焰穿破了黑暗。此外,在另一頭,一支蠟燭插在葉片狀的玻璃罩裡,以它星星點點的燭光照亮了一只假首飾盒。店鋪的女主人在櫃台的裡端打瞌睡,雙手插在她的披肩裡。
幾年前,在這家店鋪的對面,也有一家小店,鋪子裡暗綠護牆板的所有縫隙裡散發著濕氣味兒。在又長又窄的一塊木板招牌上,黑色的字母拼成了一行字:
婦女服飾用品商店
而在一扇玻璃門上用紅色的字母,寫著一位婦人的名字:
泰蕾絲.拉甘
在門的兩邊,玻璃櫥窗向後深深地凹進去,櫥窗內襯著藍色的紙。
就是大白天,在半明半暗的朦朧的光線下,行人也僅能看清陳列的商品而已。
一邊,擺著一些零星的織物,如筒狀的褶子羅紗無沿帽,兩三個法郎就能買一頂;平紋細布的衣袖和衣領;還有一些手工針織品、長短襪和背帶。每件東西都已泛黃,並且皺巴巴的、孤零零地掛在鐵桿上。這樣,看起來櫥窗裡好像塞滿了白花花的破布碎片,在透明的夜色中顯得十分淒涼。有幾頂嶄新的帽子現著耀眼的白色,在櫥窗板上的藍紙映襯下,顯得非常突兀。一根金屬杆掛著有色的襪子,彷彿在平紋細布的灰白色和淺色的基調上,加上了幾點暗淡色彩。
在另一邊,在一面更為狹小的櫥窗裡,分層陳列著一團團綠色毛線、縫在白卡紙上的黑鈕子、各種尺寸和顏色的盒子、帶淡藍色圓襯墊的綴著鋼珠的線網、一束束毛線針、針織樣品,一卷卷飾帶。總之,是一大堆黯然失色的物品,它們躺在這兒大概已有五、六年了吧。塵土和潮濕已經腐蝕了這個貨架,而放在這貨架上的所有物品也都慢慢失去了光澤,變成了污穢的灰色。
夏天,將近中午時,烈日以其赤橙的火焰灼燒著廣場和街道,在另一扇櫥窗裡的帽子後面,路人可以看清一位神色莊重,臉色蒼白的少婦的側面。在陰暗的店鋪裡,大致顯露出了她的身影。她額頭低而乾癟,連著一根尖細的鼻梁,嘴唇就是淡紅色的薄薄兩片,下巴短而剛勁有力,由一條精巧而豐腴的曲線和頭頸相連。身體為陰影遮沒,只有臉部顯現出來,臉色蒼白無光,一隻睜得大大的黑眼珠子嵌在裡面,彷彿不堪忍受深褐色厚密的頭髮重壓似的。在兩頂無沿女帽之間,她能安靜地坐上幾個小時,一動不動。潮濕的金屬架已在這兩頂帽子上留下了斑斑鏽跡。
晚上,掌燈時分,可以看清店鋪裡的模樣。這家鋪子門面寬,但並不太深,在一端有一張小小的櫃台;在另一端,一架螺旋形樓梯通向二樓。四周貼著牆排列著玻璃櫥窗、貨架、一排排未加工的紙板。四張椅子和一張桌子算是全部家具了,整個房間顯得很空,冷冰冰的。打成包的商品緊緊地擠在角落裡,包裝紙雖是五顏六色很花俏,但堆放得倒很整齊。
通常,在櫃台後面坐著兩個女人:一個就是側影端莊的少婦;另一個是老太太,她在瞌睡時都帶著笑容。後者大約有六十歲上下,燈光下,她那張平靜而肥厚的臉也變白了。一隻碩大的虎斑貓蹲在櫃台一角,望著她打瞌睡。在櫃台下面,一個男人坐在一張椅子上,三十歲左右,他不是在讀書便是與少婦低聲交談。這個人長得十分瘦弱,舉止有氣無力,他的淺黃色頭髮毫無光澤,鬍鬚稀少,臉上佈滿了紅斑斑,他的模樣有點像被寵慣了的病態的孩子。
十點鐘不到一點兒,老太太醒了,於是他們關上店鋪門,全家上樓就寢。虎斑貓鼻子裡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跟在牠的主人後面,每上一級樓梯,就把頭向欄杆磨蹭一下。
二層樓的居室共三間,樓梯直通餐室兼會客室。餐室的左首是一個壁龕,壁龕裡有一只陶瓷火爐,對面,擺了一張餐櫥;沿著牆壁擺了一排椅子,一張沒有鋪台的圓餐桌位於餐室中央。在裡端的一層玻璃後面,就是一間黑漆漆的廚房。在餐室的兩側,各有一間臥室。
老太太抱吻了兒子和媳婦後,回到自己房裡。貓就在廚房的一張椅子上睡下。這對夫婦進了自己的臥房。這間臥房另有一扇門通長廊的那道樓梯,中間經過一條狹長、陰暗的小小通道。
丈夫老是在發燒,渾身打顫,先上床睡了。少婦打開窗戶,把外邊的百葉窗關上。她在那站了幾分鐘,對面是一面粗粗塗著泥灰的高大、黝黑的牆壁,它高出長廊並繼續在升高。她的目光在這面高牆上茫然地掃了一眼,接著帶著倨傲而冷漠的心情,也默默地上了床。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紅杏出牆的圖書 |
 |
紅杏出牆 作者:左拉 出版社: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9-08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歐美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法國文學 |
$ 252 |
世界古典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紅杏出牆
雜貨鋪老闆娘拉甘太太的獨生子卡米耶從小體弱多病,長大後拉甘太太做主,把侄女泰蕾絲嫁給他,婚後,泰蕾絲的情慾得不到滿足,於是和卡米耶的好友勞倫特私通,兩人為達到做長久夫妻的目的,設計淹死了卡米耶,事後他們的內心不能得到安寧,終於導致精神崩潰,最後雙雙服毒自盡……
作者簡介:
左拉(法語:Émile Édou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4.2~1902.9.29),19世紀法國寫實主義作家,《紅杏出牆》(Thérèse Raquin)發表於1867年,左拉用他那把鋒利的重量解剖刀淋漓盡致地剖析了人性中的情慾和犯罪後卑劣的靈魂,作品極富藝術感染力,是一部優秀代表作。
章節試閱
在蓋內戈街的盡頭,倘若您是從碼頭上來,您就會見到新橋長廊。這是一條狹長而晦暗的走廊,從瑪扎里納街一直延伸到塞納河街。這條長廊至多有三十步長、兩步來寬;地面上鋪著淡黃色磨損、破裂的石板,時時散發著刺鼻難聞的潮濕味;尖頂玻璃天棚蓋住了長廊,上面積滿了污垢,顯得黑乎乎的。
在夏日的晴天,當驕陽灼燒著街道時,透過骯髒的玻璃天棚,一道蒼白的光在長廊上無力地蔓延開來。若是遇上冬季的壞天氣,在霧濛濛的清晨,從玻璃天棚投到粘濕的石板上的,就只是一片猥瑣而邋遢的夜色了。
左首,一些陰暗、低矮、像是被壓垮了的店鋪半...
在夏日的晴天,當驕陽灼燒著街道時,透過骯髒的玻璃天棚,一道蒼白的光在長廊上無力地蔓延開來。若是遇上冬季的壞天氣,在霧濛濛的清晨,從玻璃天棚投到粘濕的石板上的,就只是一片猥瑣而邋遢的夜色了。
左首,一些陰暗、低矮、像是被壓垮了的店鋪半...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