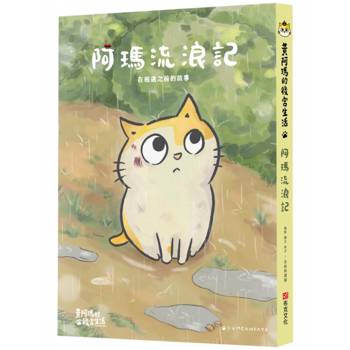復活
‧時代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個睿智的日子,也是個愚昧的日子;那是信心百倍的時期,也是疑慮重重的時期:那是陽光普照的季節,也是黑暗籠罩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讓人絕望的冬天;我們面前無所不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們大家都在直下地獄―—簡而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權威家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只能用「最……」來評價它。
當時,英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國王和一位容貌平常的王后;法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國王和一位容貌姣好的王后。這兩個國家那些坐食俸祿的權貴們心中,有一點比水晶還要明澈,那就是大局已定,江山永固了。
那是我主耶穌降生後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那上天恩寵的幸福年代,英國正如當今一樣,非常信奉神的啟示。索斯科特太太剛剛過了她的二十五歲大壽,禁衛軍中一個未卜先知的士兵早已預言她這位聖靈將降臨人間,宣稱諸事已安排就緒,倫敦和威斯敏斯特即將遭受滅頂之災。公雞巷的鬼魂用叩擊聲宣洩天機後被祓除,也只過去十二個年頭;而在剛過去的這一年中,又有精靈鬼怪用叩擊聲來宣洩天機了(驚人地毫無新穎之處)。不過也有一些世俗事件的消息,來自美洲大陸英國臣民的一次會議最近傳到了英國朝野。說來也怪,這些消息對於人類,要比公雞巷裡孵出的任何一隻小雞宣洩的天機重要得多。
總的說來,法國不如她那位一手持盾、一手執三叉戟的姊妹那麼熱衷於鬼神。可她濫發紙幣,揮霍無度,暢通無阻地走著下坡路。此外,她還在那些基督教牧師的指導下,以施行種種德政為樂,諸如剁去一個青年的雙手,用鉗子拔掉他的舌頭,然後把他活活燒死,只因他看見五、六十碼外有一行滿身齷齪的修道士走過,沒有在雨中跪下向他們行禮致敬。很有可能,在那個受難者被處決之時,長在法國和挪威森林中的一些樹木已被伐木人―—命運之神做上標記,準備砍倒鋸成木板,做成一種裝有口袋和刀斧,在歷史上曾令人膽戰心驚的活動裝置。很有可能,就在那一天,在巴黎近郊種著幾畝薄田的莊稼漢的簡陋外屋裡,也正停著幾輛製作粗糙的大車,在那兒躲風避雨,車子濺滿污泥,豬在周圍拱嗅,家禽在上面棲息,這就是那個莊稼漢—―死神留著用作大革命時押送死囚的囚車。可是那伐木人和莊稼漢雖然不停地幹活,卻默默無聲,連走起路來都躡手躡腳,誰也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由於對膽敢懷疑他們並已覺醒的人都要加上不信神明和有意謀叛的罪名,情況就更加如此了。
在英國,幾乎沒有多少可供國人誇耀的秩序與安寧了。每天晚上,堂堂的京城都有明火執仗的盜竊和攔路搶劫的案件發生。各家各戶都公開得到告誡:離家出城,須將家具送家具行倉庫保管。黑夜攔路搶劫的強盜乃是白天市區經商的買賣人,若是在當「大王」時被同行的生意人認出,受到指責,就豪爽地給他的腦袋送上一槍,然後逃之夭夭。七個強盜攔劫郵車,被押車的警衛打死三個:接著,「由於彈藥用盡」,警衛又被餘下的那四個強盜打死;之後,郵車被太太平平地洗劫一空。堂堂的倫敦市市長大人也在特恩海姆公園被一個強盜攔劫,當著他全體扈從的面,把這位顯赫人物搶了個精光。倫敦監獄裡的犯人和看守發生毆鬥,司法當局就用裝有實彈的大口徑短槍,朝他們一陣亂放。小偷在王宮的召見廳裡剪走王公大臣脖子上的鑽石十字架。武裝士兵到聖賈爾斯區搜查私貨,亂民向士民射擊,士兵也向亂民開火,誰也不認為這類事有多越乎常軌。在處理這些事件中,屢屢動用劊子手;儘管徒勞而有害,但仍照用不誤。一忽兒,絞殺幾大串各式各樣的罪犯;一忽兒,星期六吊死一個在星期二捕獲的盜賊;一忽兒,在新門監獄燒死成打剛抓到的人;一忽兒,又在威斯敏斯特大廈門前焚燒小冊子。今天處決一個罪大惡極的殺人犯,明天又處決一名偷了農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憐巴巴的小偷。
所有這些事情,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事情,都發生在那令人難忘、已成過去的一七七五年,以及臨近這一年的時候。就在那兩個大下巴的男人和兩個容貌平常與容貌姣好的女子忙於這些事情,熱衷於用高壓手段來維持他們的神聖權利時,那伐木人與莊稼漢也在神不知鬼不覺地操勞著。公元一七七五年就這樣引領著這些赫赫人主和芸芸小民—―其中包括本書所要記述的人物―—沿著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條條道路,向前走去。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雙城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0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歐美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英美文學 |
$ 334 |
Books |
$ 342 |
世界古典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雙城記
這是一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所寫成的長篇歷史小說,雙城,指的是巴黎倫敦,故事中將巴黎、倫敦兩個大城市連結起來,描寫了封建貴族敗壞,如何殘害百姓,人民心中積壓對貴族的刻骨仇恨,導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國大革命,書中不僅能看到社會現實,也能看到人性中最閃亮的一面,有的人為了正義,放棄自己貴族身份財產,有的人不願與罪惡同流合污,以致蒙冤入獄,有的人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拯救無辜,從巴黎到倫敦……
作者簡介: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2.7~1870.6.9),英國19世紀中期作家、評論家,1859年出版《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講述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和英國的社會生活,描述了貴族階級的糜爛墮落,以及他們對中下層人民的壓榨迫害,也正面描寫了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見證了血腥屠殺中一個時代的覆滅和新時代的誕生。
章節試閱
復活
‧時代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個睿智的日子,也是個愚昧的日子;那是信心百倍的時期,也是疑慮重重的時期:那是陽光普照的季節,也是黑暗籠罩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讓人絕望的冬天;我們面前無所不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們大家都在直下地獄―—簡而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權威家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只能用「最……」來評價它。
當時,英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國王和一位容貌平常的王后;法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
‧時代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個睿智的日子,也是個愚昧的日子;那是信心百倍的時期,也是疑慮重重的時期:那是陽光普照的季節,也是黑暗籠罩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讓人絕望的冬天;我們面前無所不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們大家都在直下地獄―—簡而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權威家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只能用「最……」來評價它。
當時,英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國王和一位容貌平常的王后;法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初版序
第一部‧復活
第一章‧時代
第二章‧郵車
第三章‧夜影
第四章‧準備
第五章‧酒店
第六章‧鞋匠
第二部‧金線
第一章‧五年以後
第二章‧看熱鬧
第三章‧失望
第四章‧慶賀
第五章‧胡狼
第六章‧成百的人
第七章‧候爵老爺的城裡
第八章‧候爵老爺在鄉下
第九章‧蛇髮女怪的頭
第十章‧兩個諾言
第十一章‧一幅伙伴圖
第十二章‧知趣的人
第十三章‧不知趣的人
第十四章‧本分的生意人
第十五章‧編織
第十六章‧仍在編織
第十七章‧一個夜晚
第十八章‧九天九夜
第十九章‧一條意見
第二十章‧一個請求
第二十一章‧回響的...
初版序
第一部‧復活
第一章‧時代
第二章‧郵車
第三章‧夜影
第四章‧準備
第五章‧酒店
第六章‧鞋匠
第二部‧金線
第一章‧五年以後
第二章‧看熱鬧
第三章‧失望
第四章‧慶賀
第五章‧胡狼
第六章‧成百的人
第七章‧候爵老爺的城裡
第八章‧候爵老爺在鄉下
第九章‧蛇髮女怪的頭
第十章‧兩個諾言
第十一章‧一幅伙伴圖
第十二章‧知趣的人
第十三章‧不知趣的人
第十四章‧本分的生意人
第十五章‧編織
第十六章‧仍在編織
第十七章‧一個夜晚
第十八章‧九天九夜
第十九章‧一條意見
第二十章‧一個請求
第二十一章‧回響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