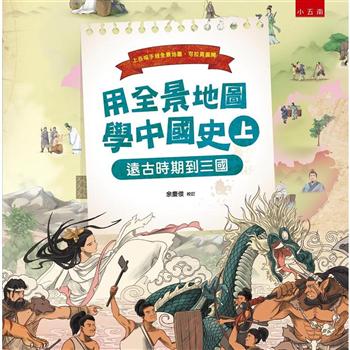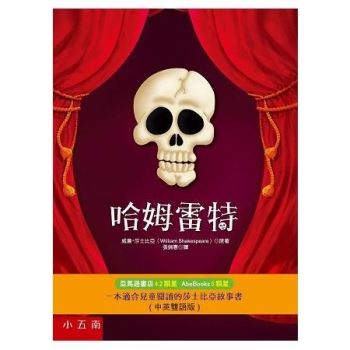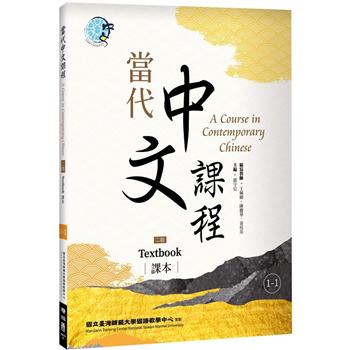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祕密花園的圖書 |
 |
祕密花園 作者: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 / 譯者:楊玉娘 出版社:天蠍座製作工作室 出版日期:2022-09-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0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歐美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英美文學 |
$ 288 |
世界古典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祕密花園
內容簡介
性情古怪孤僻的小女孩瑪麗在父母雙亡後,生活在姑丈神秘陰沉的大房子裡,在這裡遇見了農家小子廸肯和常年被關在陰暗房間的病態少爺柯林,一次神奇的經歷,使瑪麗闖入久已禁閉且荒蕪的花園,這個神祕的花園究竟隱藏著什麼秘密?又將為這三個孩子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呢?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法蘭西絲.霍森.柏納特(Frances Eliza Hodgson Burnett,1849.11.24~1924.10.29)
英美劇作家與作家,《秘密花園》(The Secret Garden)於1909年出版,以秘密花園的復活為襯托,細膩刻畫書中幾位主要人物性格從孤僻痛苦到健康快樂所發生的巨大轉變,告訴人們當面對挫折和痛苦時,要學會開啓心靈的秘密花園,敞開心扉,微笑面對人生,戰勝自己和磨難,每個人應該有樂觀的生活態度,永遠都不要放棄自己。
目錄
第一章 人海遺孤
第二章 反常的瑪麗小姐
第三章 穿越荒原
第四章 瑪莎
第五章 迴廊間的哭聲
第六章 「明明有人在哭!」
第七章 花園之鑰
第八章 報路的知更鳥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第十童 廸肯
第十一章 大鶇鳥之巢
第十二章 「我可不可以要一小片土地?」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第十四章 小霸王
第十五章 築巢
第十六章 「我就是不要!」
第十七章 大發脾氣
第十八章 「儂絕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第十九章 「春天來了!」
第二十章 「我會一直活到永永遠遠……」
第二十一章 班.韋勒斯泰
第二十二章 當夕陽西下
第二十三章 魔法
第二十四章 「就讓他們笑吧!」
第二十五章 簾幕
第二十六章 「是媽媽!」
第二十七章 在花園裡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168423
- 叢書系列:世界文學經典名作
- 規格:平裝 / 352頁 / 25k正 / 14.8 x 21 x 1.7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