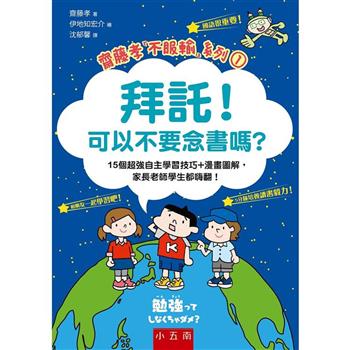沙米亞德
以前啊有四個孩子,他們在一所白屋子裡過暑假,這所白屋子恰好坐落在一個沙坑和一個白堊岩礦坑中間。有一天,他們碰巧在沙坑裡發現了一樣奇怪的動物。牠的眼睛像蝸牛的眼睛一樣生在長長的觸角上,能夠像望遠鏡一樣縮進伸出。牠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牠的圓滾滾的身體像蜘蛛,上面長滿了濃密的軟毛,牠的手腳就和猴子的手腳一樣。牠告訴四個孩子說――四個孩子的名字叫西里爾、羅伯特、安西雅和珍―—它是沙米亞德或砂之精靈。它非常非常老,牠的生日幾乎就在開天闢地那一陣子。牠埋在沙裡已經說不清有多少個年頭了。但是牠仍然保持著它的仙氣,一部分仙氣就在於:人們想要什麼,牠就能給他們什麼。你知道,仙人向來是有這種本領的。西里爾、羅伯特、安西雅和珍發現他們的願望一個個都實現了,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們總是想不出一個最最合乎心意的願望,事實上,他們的各種願望到頭來總是落得一個非常古怪的下場。他們最後的一個笨願望使他們處於羅伯特所謂「一個非常難堪的境地」,沙米亞德同意幫他們走出困境,條件是他們答應以後永遠不再要求牠實現他們更多的願望,而且絕對不把牠的存在告訴任何人,因為牠不願再花力氣使任何人的願望獲得實現。在分別的時候,珍很有禮貌地說:「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能和你再見。」
沙米亞德被這個友好的念頭感動了,就滿足了他們的願望。那本描寫所有這一切的書就叫《砂之精靈》,它的結尾是這樣的―—:
「孩子們真的又見到了沙米亞德,但不是在砂石場,而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那裡是—―」
其所以再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是因為我當時無法確切地知道孩子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能再和沙米亞德見面。當然我知道他們會和牠見面的,因為牠是隻說話算話的怪獸,牠如果說會發生一件事,那件事就肯定會發生。這和那些告訴我們下星期四倫敦、南海岸和英吉利海峽將會是什麼天氣的人比起來,情況是何等不同啊!
那個發現了沙米亞德並且說出了願望的暑假是在鄉下度過的,孩子們迫切希望明年夏天也能有這樣美好的假日。寒假過得愉快,是因為《火鳥和魔毯》中發生的種種稀奇古怪的事件,這兩樣寶物的喪失本來會使孩子們灰心失意,全靠明年在鄉下過暑假的美妙希望才使他們不致於這樣。他們覺得,而且確實有理由覺得,世界是充滿了不可思議的事件的―—而不可思議的事件確實會發生在他們這些人身上。因此他們伸長頭頸盼著暑假到來;但是暑假真的到來了,情況卻完全變了,變得非常可怕。爸爸要出國到滿洲去,把他採訪的戰爭消息用電報拍一張給他撰稿的報紙,這張討厭的報紙叫《每日吼叫》什麼的。媽媽,可憐的親愛的媽媽,遠在馬德拉群島,因為她病得很厲害。小弟弟――我是指嬰兒――和她在一起。愛瑪阿姨―—她是媽媽的妹妹――突然嫁給了雷濟諾德叔叔――他是爸爸的弟弟――他們雙雙到中國去了,中國實在太遠了,所以,無論阿姨和叔叔多麼疼愛你們,總不能指望他們會帶你們到那兒去度假呀。所以啊,四個孩子就被托給老保姆照管,老保姆在費茨羅伊街,就在大英博物館附近,儘管她一向待他們非常好,簡直把他們慣壞了,四個孩子都感到不幸極了,當馬車載了爸爸連同他所有的箱子、槍支、羊皮、毛毯和鋁餐具駛去時,最鐵石心腸的人也感到心酸,女孩們整個的垮了,互相摟抱著抽抽答答地哭,男孩們各自以客廳的長窗裡向外望著,竭力裝出沒有一個男孩子會膽小得哭的樣子。
我希望你們注意到,他們的膽子其實並不小,在爸爸走以前,他們並沒有哭出來;他們知道,即使不哭,爸爸也已經夠難受了。但是等爸爸一走,每個人都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了。
下午點心吃蝦和水芹,這使他們心情稍稍好了一點。水芹繞著一只大肚子玻璃鹽瓶排列成一圈,這種高雄的布置他們以前從未見過。不過這頓點心還是吃得不開心。
吃過點心,安西雅上樓到曾經是爸爸的房裡去,她看見爸爸不在的景象是多麼淒慘,想到爸爸每一分鐘離她越來越遠,離俄國人的砲火越來越近,就又哭了起來。接著她又想起了生病的媽媽,一個人孤零零地躺著,也許在那個當口正需要一個小女孩在她頭上抹點科隆香水,給她倒點兒茶,她就哭得更加厲害了。哭啊哭的,她忽然想起了媽媽臨走前一夜對她說的話,說安西雅是最大的女孩,應該盡力使弟弟妹妹快活,還對她說了一些諸如此類的事情,於是她就不哭了,相反地動起腦筋來了。她動了好一會兒腦筋,累了,就擦了把臉,梳了一下頭髮,下樓到弟弟妹妹那兒去,竭力裝得她甚至都沒有聽到這哭鼻子這碼事。
她發現客廳裡死氣沈沈,儘管羅伯特為了消磨時光,正在揪珍的頭髮―—揪得不輕不重,剛好達到戲弄的目的―—可是氣氛絲毫也沒有顯得輕鬆點。
「大家聽著,」安西雅說:「咱們來聊聊吧。」
這句話要追溯到去年可怕的一天,那天西里爾漫不經心地表示希望英國有北美印第安人,而果然有了。這句話使大家想起了去年暑假的情景,每個人都發出表示不滿的哼哼聲;他們想起了那幢白色的屋子,有一個美麗的花園,花園裡盛開著玫瑰花、紫菀花、木犀花,還有婀娜多姿的文竹。花園十分空曠,有人曾打算把它改建成一個果園,但現在,照父親說,僅僅是「五英畝大,小櫻桃樹的幽靈在其中出沒。」他們想起了山谷那邊的景色,那兒的白堊岩土採掘場在陽光下就像阿拉丁的宮殿。他們也想起了他們自己的沙坑,沙坑邊緣上長滿了發黃的草和莖杆纖細的野花,想起了懸崖裡一個個小洞,那是小小的崖沙燕的小小的前門。他們想起了散發著麝香草和野薔薇香味的新鮮空氣以及從村舍飄來的木紫煙的氣味。
他們環視了一下老保姆的悶熱的客廳,珍就開口了:
「唉,這一切真是大不一樣啊!」
真的是大不一樣。在父親叫老保姆照顧四個孩子之前,老保姆的房子一直是租給人家寄宿的。她的房間是附有家具「出租」的。奇怪的是,而今似乎人人都給房子裝備家具供自己居住,再沒有一個人給房子裝備家具供出租了。這個房間裡掛著厚厚的深紅色窗簾―—血在這種顏色上不會留下任何污跡―—裡面一層是粗網眼花邊。地毯是黃和紫的,有些地方露出灰色和棕色的油布。壁爐裡面有鉋花和金屬片。一只帶鏡子的桃花心木餐具櫃,漆得光亮,上面的鎖已經失靈。好幾把硬椅子,座墊上的鉤編套子已經破了,而且椅子的斜度都不對頭。桌子上罩著一塊墨綠色的台布,四周有黃顏色的繡花圖案。壁爐高頭有一面鏡子,使你變得比真正的你難看得多,無論開頭照出來是多麼晴淅。另外還有一塊壁爐台板,鋪著茶色絲絨以及絲絲不相稱的羊毛流蘇;一只破舊的鐘像一個黑大理石的墳,而且像墳一樣寂靜無聲,因為它早就忘了怎樣滴滴答答地走了。花瓶裡從來不插花,一只色彩鮮明的鈴鼓以前沒有人玩過,油漆過的壁架上空無一物。
鑲在楓木鐘框裡的女王肖像,
議會兩院、天堂樂土,
還有一個扁鼻子樵夫悠然歸來。
有兩本書—―一本是去年十二月份的火車時刻表,還有一本是普拉姆裡奇的《帖撒羅尼迦書評述》。另外還有—―可是這個令人痛心的景象我不能再描繪下去了。它的確像珍所說,大不一樣。
「咱們來聊一會兒吧。」安西雅又說了一遍。
「聊什麼呢?」西里爾打著呵欠問。
「沒什麼好聊的。」羅伯特說,一邊悶悶不樂地踢著桌子腿。
「我不想玩!」珍說,她的語調是含著怒氣的。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護身符的故事的圖書 |
 |
護身符的故事 作者:伊迪絲.內斯比特 出版社: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0-0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歐美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奇幻小說 |
$ 270 |
翻譯奇幻小說 |
$ 270 |
親子共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護身符的故事
孩子們發現半個有著神奇法力的護身符,獲取了指揮護身符的咒語,並藉助護身符的力量,去尋找另一半的護身符,他們分別去了八千年前的原始部落、富麗堂皇的古巴比倫國、偉大的亞特蘭提斯、遇到過古羅馬時代的凱撒、也曾謁見過古埃及的法老……等等,在這一系列神奇的穿越旅行中,他們遭遇過很驚險的拘捕以及戰鬥的恐慌,不過也領略了古文明的輝煌,並透過嚴密的邏輯思維推算出找到另外半個護身符的確切時間,最終結束了神奇之旅,實現了所有人的願望。
作者簡介:
伊迪絲.內斯比特(Edith Nesbit,1858.8.15~1924.5.4),英國小說作家和詩人,於1905年出版魔幻小說《護身符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ulet ),無意中獲得的護身符,竟成了孩子們穿越時空的法寶?在一次次的時空旅行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全書天馬行空,不斷的時空轉換讓本書充滿了濃濃的異域神秘色彩。
章節試閱
沙米亞德
以前啊有四個孩子,他們在一所白屋子裡過暑假,這所白屋子恰好坐落在一個沙坑和一個白堊岩礦坑中間。有一天,他們碰巧在沙坑裡發現了一樣奇怪的動物。牠的眼睛像蝸牛的眼睛一樣生在長長的觸角上,能夠像望遠鏡一樣縮進伸出。牠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牠的圓滾滾的身體像蜘蛛,上面長滿了濃密的軟毛,牠的手腳就和猴子的手腳一樣。牠告訴四個孩子說――四個孩子的名字叫西里爾、羅伯特、安西雅和珍―—它是沙米亞德或砂之精靈。它非常非常老,牠的生日幾乎就在開天闢地那一陣子。牠埋在沙裡已經說不清有多少個年頭了。但是牠仍然保持著...
以前啊有四個孩子,他們在一所白屋子裡過暑假,這所白屋子恰好坐落在一個沙坑和一個白堊岩礦坑中間。有一天,他們碰巧在沙坑裡發現了一樣奇怪的動物。牠的眼睛像蝸牛的眼睛一樣生在長長的觸角上,能夠像望遠鏡一樣縮進伸出。牠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牠的圓滾滾的身體像蜘蛛,上面長滿了濃密的軟毛,牠的手腳就和猴子的手腳一樣。牠告訴四個孩子說――四個孩子的名字叫西里爾、羅伯特、安西雅和珍―—它是沙米亞德或砂之精靈。它非常非常老,牠的生日幾乎就在開天闢地那一陣子。牠埋在沙裡已經說不清有多少個年頭了。但是牠仍然保持著...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沙米亞德
第二章 半塊護身符
第三章 過去
第四章 八千年前
第五章 村莊裡的戰鬥
第六章 到巴比倫之路
第七章 「護城河下面最深的地牢」
第八章 王后在倫敦
第九章 亞特蘭提斯
第十章 小黑女孩和凱撒
第十一章 在法老面前
第十二章 「對不起禮物」和被開除的小男孩
第十三章 馬口鐵島上的沈船
第十四章 衷心的願望
第一章 沙米亞德
第二章 半塊護身符
第三章 過去
第四章 八千年前
第五章 村莊裡的戰鬥
第六章 到巴比倫之路
第七章 「護城河下面最深的地牢」
第八章 王后在倫敦
第九章 亞特蘭提斯
第十章 小黑女孩和凱撒
第十一章 在法老面前
第十二章 「對不起禮物」和被開除的小男孩
第十三章 馬口鐵島上的沈船
第十四章 衷心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