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
鼴鼠在為自己的小小家園進行春季大掃除,一整個早上忙得天昏地暗。先是拿掃把掃地,接著撣撣灰塵;然後爬上短梯,踩著臺階,踏到椅子上粉刷四壁。搞得沙子進了喉嚨和眼睛,一身烏溜溜的毛皮濺得到處都是白石灰水,手也酸、背也疼。春意在頭頂上方的空氣中、腳底下的土地裡、還有周遭活動,就連他那昏暗低矮的小屋內,也瀰漫著春日絕頂的不滿和渴望的氣息。這也就難怪他會突然把刷子往地板上一摔,直嚷著:「好煩吶!」「討厭死嘍!」還有:「去他的春季大掃除!」隨即連外套也來不及穿,就迫不及待地衝出屋外。頭頂上方不知什麼東西在急切地呼喚他。鼴鼠三步併做兩步趕往通向碎石車道的峭直小地道;這條車道屬於那些住在更靠近空氣和陽光的動物們。他一面七手八腳地用他的小爪子又挖又刨,邊摸索邊擠;再挖再刨,再摸索再用力擠;一面喋喋不休地暗自嘮叨:「上啊!上啊!快上前吧!」最後終於:「噗!」他的口鼻鑽進陽光裡,身體在大草地裡暖洋洋的青草上連打好幾個滾。
「好棒哇!」他自言自語:「這比粉刷牆壁好多啦!」陽光熱烘烘地照在他的毛皮上,微風柔柔吹拂他被曬燙的額頭。在與世隔離的地洞裡蟄居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後,鼴鼠的聽力遲鈍了。快樂的鳥兒們婉囀的歌唱,在他耳裡聽來活像大呼小叫。在生氣蓬勃的喜悅和免除大掃除的春之歡欣中,他四肢同時彈躍,蹦蹦跳跳地跑到草地另一頭的樹籬前。
「站住!」一隻老兔子守在樹籬的缺口說:「通過私人道路先付六便士。」但他馬上就被既不耐煩又不把他放在眼裡的鼴鼠整得狼狽不堪。對方不但昂首闊步地沿著樹籬走,還滿口:「洋蔥醬!洋蔥醬!」(沾兔肉的佐料)地嚷嚷著,戲弄那些急急忙忙從洞裡蹦出來瞧瞧外頭在吵些什麼的兔子,而趁他們還沒來得及想出什麼理想的話回敬前跑掉了,丟下那些兔子彼此一如往常般互相抱怨:「你真笨喲!怎麼不告訴他說―—」「喂,那你自己為什麼不說—―」「你本來可以提醒他說—―」諸如此類等等的話;不過,當然啦,就像以往每一次一樣,太遲啦!
一切似乎都好得不像真實的。他忙忙碌碌地在大草地上四處逛,順著灌木樹籬,穿過一叢又一叢的矮樹,處處看到鳥兒在築巢,花兒在吐蕊,樹葉兒一葉葉舒放開來—―萬事萬物都是那麼快活忙碌、欣欣向榮。他不覺得不安的良心在鞭策著他,對他細聲叮嚀:「快粉刷牆壁啊!」卻又感到在這一大堆忙個不停的居民間當個懶骨頭是多麼快活呵!畢竟,也許假期中最棒的一部分並非好好休息,而是看到的傢伙全在忙著工作。
他漫無目標地到處閒逛,心想自己真是快活到頂點!猛不防,已經站在一條漲滿水的河流邊。他從小到大沒有見過任何河流―—這彎彎扭扭、光滑飽滿的動物,沿路追逐嬉笑,一會兒笑呵呵地抓住某樣東西,一會兒又哇哈哈地把它放走,衝上前去糾纏新玩伴。新的玩伴們掙脫開了,馬上又被抓住。一切都是搖搖盪盪、抖抖顫顫―—微光閃耀、浪光粼粼,打著漩渦、潺潺作響,嘰哩咕嚕、冒出水泡。鼴鼠困惑、著迷、如癡如醉了。就像個被某人的刺激故事吸引得入迷的小小人兒,老追在那人身邊跑來跑去一樣,鼴鼠也順著河畔快步奔跑;等到終於跑累了,他便坐在河岸。而河水依然不斷地對他潺潺細訴,訴說一則則世上最好的故事。它們來自地心,最後要說給永不知足的大海聽。
他坐在青草地上隔著河向對岸望,看見就在河水邊上有個暗暗的洞,於是朦朦朧朧地便思忖起對於一隻沒有什麼需求,喜歡在比最高洪水位高些、而又遠離塵囂的小巧河濱居處居住的動物來說,那該是多麼舒適的一個小住所啊!正當它凝望著那個洞穴時,似乎有個明亮的小東西在它的中心一閃而逝,緊接著又像顆小星星一樣再度閃閃發亮。但此時此地,那不可能是顆星星;而若是隻螢火蟲的話,卻又顯得太亮太小了。這時,正當鼴鼠朝著它凝望,那東西對它眨了眨,令他明白那是顆眼睛;漸漸地,一張小臉就像圖畫四周的框一樣,圍繞它的四周成形。
一顆長了鬍鬚,棕色的小臉。
一張莊嚴的臉,眼睛裡有著和首先吸引他注意的一模一樣的閃光。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柳林中的風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197 |
中文書 |
$ 198 |
歐美文學 |
$ 220 |
英美文學 |
$ 225 |
英國現代文學 |
$ 225 |
親子共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柳林中的風聲
這是一部以鼴鼠、河鼠、蛤蟆、獾……動物為主角,敘述了這四個好朋友在柳林河畔間的生活和奇幻驚險的故事,鼴鼠善良溫柔,河鼠熱情好客,蛤蟆冒失勇敢,獾沉穩睿智,每個動物的性格不同,但毫不影響他們建立起最真摯的友誼,同甘苦共患難,在經歷了幾次冒險與波折後,每個角色都獲得成長,最終迎來圓滿大結局。
作者簡介:
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1859.3.8~1932.7.6),英國作家,1908年出版《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一本關於友情與冒險的經典之作,以動物主角們所經歷的曲折探險故事,生動地刻畫柳林中縈繞的友誼與溫厚的情感,被譽為英國散文體作品的典範。
章節試閱
河岸
鼴鼠在為自己的小小家園進行春季大掃除,一整個早上忙得天昏地暗。先是拿掃把掃地,接著撣撣灰塵;然後爬上短梯,踩著臺階,踏到椅子上粉刷四壁。搞得沙子進了喉嚨和眼睛,一身烏溜溜的毛皮濺得到處都是白石灰水,手也酸、背也疼。春意在頭頂上方的空氣中、腳底下的土地裡、還有周遭活動,就連他那昏暗低矮的小屋內,也瀰漫著春日絕頂的不滿和渴望的氣息。這也就難怪他會突然把刷子往地板上一摔,直嚷著:「好煩吶!」「討厭死嘍!」還有:「去他的春季大掃除!」隨即連外套也來不及穿,就迫不及待地衝出屋外。頭頂上方不知什麼東西...
鼴鼠在為自己的小小家園進行春季大掃除,一整個早上忙得天昏地暗。先是拿掃把掃地,接著撣撣灰塵;然後爬上短梯,踩著臺階,踏到椅子上粉刷四壁。搞得沙子進了喉嚨和眼睛,一身烏溜溜的毛皮濺得到處都是白石灰水,手也酸、背也疼。春意在頭頂上方的空氣中、腳底下的土地裡、還有周遭活動,就連他那昏暗低矮的小屋內,也瀰漫著春日絕頂的不滿和渴望的氣息。這也就難怪他會突然把刷子往地板上一摔,直嚷著:「好煩吶!」「討厭死嘍!」還有:「去他的春季大掃除!」隨即連外套也來不及穿,就迫不及待地衝出屋外。頭頂上方不知什麼東西...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河岸
第二章‧通衢大道
第三章‧野樹林
第四章‧獾先生
第五章‧溫馨家園
第六章‧蛤蟆先生
第七章‧黎明大門前的吹笛人
第八章‧蛤蟆歷險記
第九章‧浪跡天涯的旅行者
第十章‧蛤蟆歷險續記
第十一章‧他的淚如夏日大雨滂沱
第十二章‧尤里西斯歸來
第二章‧通衢大道
第三章‧野樹林
第四章‧獾先生
第五章‧溫馨家園
第六章‧蛤蟆先生
第七章‧黎明大門前的吹笛人
第八章‧蛤蟆歷險記
第九章‧浪跡天涯的旅行者
第十章‧蛤蟆歷險續記
第十一章‧他的淚如夏日大雨滂沱
第十二章‧尤里西斯歸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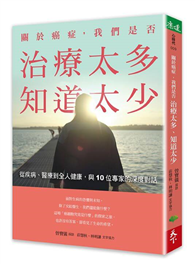


![114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金融證照] 114年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重點統整+歷年試題)[金融證照]](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