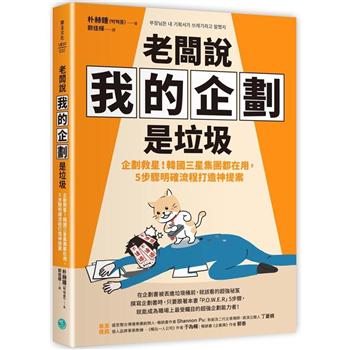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思想的政治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64 |
政治 |
$ 411 |
政治概論 |
$ 411 |
政治 |
$ 442 |
社會人文 |
$ 468 |
中文書 |
$ 468 |
社會人文 |
$ 468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思想的政治學
薩依德曾提及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說這是「英文中第一部完完全全呈現思想熱情的長篇小說」。
英美世界的年輕人是熟悉這書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熟悉這獨立自主與思想熱情。
本書作者寫作《思想的政治學》的核心價值,即是指向民主與科學,並鼓舞著正在形成中的社會良知——
那是在我們社會的靈魂作坊裡,尚未創造完成的「國民性」良知。
本書選文
・亞里斯多德德性優越意識批判
・諾貝爾經濟學獎到新自由主義
・美國歐巴馬總統的重建公共領域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托爾斯泰
・停留在單一民族國家的羅爾斯正義論
・走出新自由主義困境的韋依義務論
・走出地下室悲劇的卡拉馬助夫少年
・古希臘史詩精神的韋依思想
・真善美的人文主義者薩依德
作者介紹
王賀白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士、輔仁大學西洋史碩士與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新聞界擔任記者多年。
1999年2月起在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擔任政治學的教學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