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是和平崛起的中國,與世界各國共謀發展的輝煌年代,《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所闡述的「中國和平崛起」道路,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政策,是指導中國國際關係的中心思想。
本書收錄文章,以年代作為「中國和平崛起論」的演進依據,內容包括「中國和平崛起論」的由來、根據、內涵、前景以及深化;此外,和平崛起的中國,究竟該以何種態度面對與處理兩岸關係,則是本書另一個重點。
鄭必堅以務實的態度,提出「對外求和平、對內求和諧、兩岸求和解」的新政策,有力的反駁了「中國威脅論」,希望世界各國不以中國為假想敵,共同為世界的和平發展而努力。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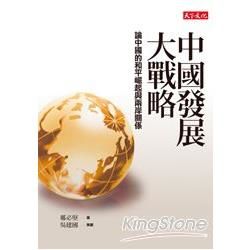 |
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出版日期:2014-03-31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鄭必堅
鄭必堅,四川省富順縣人,一九三二年出生,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四年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政治助理、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現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同時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理事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等社會職務。
著有《鄭必堅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思考的歷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天下文化)等書。
吳建國
吳建國,一九五○年生於台灣高雄。一九七二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一九七八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材料科學博士。曾任美國勞倫斯國家實驗室研究員、加州矽谷ZILOG電子公司半導體製程工程師。
一九八○年返台參加國立中山大學的建校工作,歷任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學研究所所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科技顧問、參事、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台灣文化人上海聯誼會會長、中華世紀文教發展協會理事長等職。
著有《向前看中國》、《來自柏城》、《唯盡我心》(時報文化)等書。
鄭必堅
鄭必堅,四川省富順縣人,一九三二年出生,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四年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政治助理、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現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同時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理事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等社會職務。
著有《鄭必堅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思考的歷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天下文化)等書。
吳建國
吳建國,一九五○年生於台灣高雄。一九七二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一九七八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材料科學博士。曾任美國勞倫斯國家實驗室研究員、加州矽谷ZILOG電子公司半導體製程工程師。
一九八○年返台參加國立中山大學的建校工作,歷任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學研究所所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科技顧問、參事、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台灣文化人上海聯誼會會長、中華世紀文教發展協會理事長等職。
著有《向前看中國》、《來自柏城》、《唯盡我心》(時報文化)等書。
目錄
出版者的話 中國和平崛起下的兩岸思索 高希均
作者序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鄭必堅
本書緣起 我們的鄭必堅在哪裡? 吳建國
第一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由來
第一章 圍繞國家安全,開展「大戰略」研究
第二章 綜合「大戰略」研究,抓住新世紀發展時機
第三章 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兩大歷史性追求
第四章 把握兩個大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二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根據
第五章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和新戰略機遇期
第六章 中國前所未有的戰略道路
第七章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向何處去
第三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內涵
第八章 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第九章 和平崛起的中國,是和平崛起的亞洲的一部分
第十章 和平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極重要的「中國特色」
第四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前景
第十一章 中國和平崛起為強國
第十二章 中國和平崛起與中華文明復興
第十三章 和平、文明與可親的新中國形象
第十四章 中國路‧中國夢‧中國心
第五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深化
第十五章 關於中美「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的幾點思考
第十六章 關於中歐「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的幾點思考
第十七章 關於中國戰略和「利益匯合點」、「利益共同體」問題的幾點思考
第十八章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構建利益共同體
第六部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第十九章 中國和平發展與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
第二十章 從兩個大局看兩岸關係
第二十一章 兩岸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世紀
作者序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鄭必堅
本書緣起 我們的鄭必堅在哪裡? 吳建國
第一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由來
第一章 圍繞國家安全,開展「大戰略」研究
第二章 綜合「大戰略」研究,抓住新世紀發展時機
第三章 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兩大歷史性追求
第四章 把握兩個大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二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根據
第五章 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和新戰略機遇期
第六章 中國前所未有的戰略道路
第七章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向何處去
第三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內涵
第八章 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第九章 和平崛起的中國,是和平崛起的亞洲的一部分
第十章 和平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極重要的「中國特色」
第四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前景
第十一章 中國和平崛起為強國
第十二章 中國和平崛起與中華文明復興
第十三章 和平、文明與可親的新中國形象
第十四章 中國路‧中國夢‧中國心
第五部 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深化
第十五章 關於中美「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的幾點思考
第十六章 關於中歐「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的幾點思考
第十七章 關於中國戰略和「利益匯合點」、「利益共同體」問題的幾點思考
第十八章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構建利益共同體
第六部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第十九章 中國和平發展與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
第二十章 從兩個大局看兩岸關係
第二十一章 兩岸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世紀
序
作者序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二○○九年十一月,我率大陸代表團到台北,參加由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在開幕式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的回顧和前瞻〉的主旨講演。代表團成員在台灣停留了一個星期,除了參加會議以外,還有機會與台灣各界人士,包括民進黨的一些政治人物,接觸交談,更用四天的時間,環島走了一趟。割捨不斷的民族親切之情,多姿多彩的台灣風土人情,以及一次次坦誠熱情的交流對話,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會後,「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的策劃者和主辦人,時任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的吳建國先生,多次來北京與我就國際形勢、中國和平崛起及兩岸關係等議題深入交談。他閱讀了我關於這方面的一些文章,遂向我提出由他策劃成書,在台灣出版的願望,盛情難卻。
呈獻給讀者的這部專題論集《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就是吳建國先生彙集了我自一九九一年六月至二○一三年底的有關論文和講演,精心策劃而成的。本書分為六個部分,即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由來、根據、內涵、前景、深化,以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每一部分吳建國先生都寫了前言簡介。
中國的和平崛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道路,是以前總書記胡錦濤為主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後,用科學總結和繼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經驗,精闢分析和把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重大戰略機遇,針對國際輿論中此起彼伏的「中國崛起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而鄭重提出的。應當說,「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提出和確立,乃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一個深刻的揭示,也是中國政府和國家,對內對外方針相統一的一個鮮明體現。
從歷史角度看,這一重大決策,歸根到底,是來自鄧小平先生帶領中國政府,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一九七八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果斷決策下,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抉擇,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政府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
三十六年來,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與習近平,一以貫之,薪火相傳,接力推進,領導中國政府和國家在各種複雜形勢下,始終努力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從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世界近代史上,一切後興大國所從未有過的獨特道路——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這一重大決策,受到世界各國政治家、戰略家、外交家、企業家,和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普遍關注和重視,在國際上產生了幾乎可說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和平崛起發展道路」需要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這方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重大方針,就是「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全方位地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建立和發展不同領域與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特別是「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已經明確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前總書記胡錦濤和前總理溫家寶也多次在重要的國際場合鄭重提出這一理念。
實際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利益匯合點」,已是一種客觀存在。二○○八年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家和經濟體,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就是特定條件下各方利益的最大匯合點。現在,中國與美國等主要經濟體之間,需要相互適應與調整,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變化,和各自國內結構調整,這又應成為各方新的利益匯合點。這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就是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互補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貿易領域向投資領域擴展,國際投資合作正在進一步加強。
總之,在共同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之後,中國與世界的「利益匯合點」較之以前是更多,而不是更少了;中國與世界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上構建「利益共同體」的條件是更加充分,而不是更為欠缺了。
寫到這裡,我還想順帶說明一點,就是關於「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這兩個說法的問題。人們閱讀這部專題論集時會發現,我從二○○二年起,曾多次使用「中國和平崛起」的提法。既然是闡發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為什麼又要提「中國和平崛起」呢?
首先,這是因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雖然用語不同,其實是同一個意思,本質內涵完全一致。其次,在那時提出「中國和平崛起」,有其現實針對性。「和平」是針對某些國際輿論正開始起勁鼓吹的「中國崛起威脅論」,而「崛起」則是針對「中國崩潰論」。第三,這一說法還反映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特點。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這無疑應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過程;而在當前階段,即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國的和平發展具有抓住機遇,而實現由不發達到中等發達的歷史性飛躍的重要特點。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九點四,估計今後在「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總要求下,相當時期大約也不會低於百分之八。這是一個在中央和國家自覺推動,和廣大人民共同努力下的飛躍和突變的過程,是一個全民奮起、艱苦創業、擺脫貧困、實現小康,進而從不發達國家轉變為中等發達國家的過程。歸根到底,是一個為著和平的目的而發展、抓住和平的機遇而崛起的過程。總之,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這兩個說法,用語不同,針對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不同語境而互為通用或選擇使用。當然,作為一條體現中央和國家,對內對外方針相統一的國家發展戰略道路,其說法又應是統一的,這就是「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我一直強調,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就是和平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對外求和平、對內求和諧、兩岸求和解為其本質特徵。承認一國兩制,就意味著兩岸之間,不再有意識形態之爭與社會制度之爭,而是謀求雙方和平相處、兩岸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六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發生了重大深刻的變化,最鮮明的特點是由軍事對峙、隔絕對立,走向交流合作、對話協商。這種轉折儘管歷經曲折坎坷,但畢竟取得了重大進展,一種新型的兩岸關係正在逐步加速形成。在此過程中,雙方政策的不斷調整,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我以為,兩岸關係三十多年的發展積累的全部成果,最重要也最寶貴的是,兩岸同胞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上,第一次有難得的機遇和良好的條件,在全球競爭中攜手合作,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共同奮鬥。
兩岸長期以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全新的交集,面臨著匯聚到實現民族振興的共同大道上的重要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兩岸關係,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前總書記胡錦濤在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篇重要講話中說,「回顧近代民族之艱難奮鬥歷程,展望未來民族之光明發展前景,我們應該登高望遠、審時度勢,本著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以更遠大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勇氣、更務實的思路,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
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著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開闢兩岸關係嶄新格局的重要時刻即將到來。我衷心希望,兩岸同胞能以不懈的努力,迎來一個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時期。
謹向策劃此書的吳建國先生,和出版此書的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致以謝忱。
鄭必堅
二○一四年一月於北京
出版者的話
中國和平崛起下的兩岸思索──寫在鄭必堅新書在台出版前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革命家、思想家、政治人物及追隨者與反對者,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與離合。
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沒有歷史,哪有家國?只有失敗的歷史,何來家國?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半世紀來在台灣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先後出版了實際參與改變中國命運與台灣發展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都是廣義的英雄,他們或有英雄的志業、或有英雄的功績、或有英雄的失落。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黨國元老、軍事將領、政治人物、企業家、專家學者,以歷史的見證,細述他們的經歷軌跡與成敗得失。
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如果因此引起的爭論,我們同樣尊重,但也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每一位人物寫下他們的經歷、觀察,甚至後見之明,為歷史留下紀錄。
兩岸分隔六十餘年,已從對峙走向交流。二○一三年二月,我們出版了黃年撰述的《大屋頂下的中國》,此時出版曾擔任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智囊,及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先生的新書,意義重大。此書表達了一位中國大陸倡導「和平崛起」的戰略思想家,對兩岸關係與全球發展的長期思維,值得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及華人讀者閱讀與深思。
高希均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緣起
我們的鄭必堅在那裏?
初識鄭必堅先生,是在二○○九年十一月。他以團長的身分,率領一個包括退役將軍、退休大使在內,共二十八人的中國高層代表團,到台北出席被譽為六十餘年來,對兩岸關係影響最深遠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
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開幕典禮上發表的主旨講演,開宗明義且清晰的將台灣當前所處困境與侷限的原因點了出來:「直到今天,儘管冷戰格局早已崩潰,但台灣還沒有真正擺脫對舊格局的依附,冷戰思維依然像揮之不去的陰影影響著台海形勢」。
在結束講演前,鄭必堅特別引用一九九七年,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以「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兩大歷史性追求」為題發表講演時的一段話,總結他的發言:「中國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算起,幾代人直到今天的處境和心態,是深重的危機感,是爭取生存、發展權利不受侵害,是謀求一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二要發展和現代化,而不是什麽擴張,更不是什麽侵略」。
身為此次研討會的策劃者與主辦人,我坐在台下,聆聽鄭必堅如此真誠及語重心長的講話,心中的震撼是難以言喻。尤其,對於他最後所說的那段話,讓我回憶起與從小接受的父祖輩教訓,內容毫無二致。只是這樣的話,在今天的台灣已沒有人再說了。這是由於台灣近年來在強烈本土意識主導下,「去中國化」的結果,使得政府與人民均已放棄,過去曾長期代表中國正統政權的角色任務,甘於偏安一隅,自外於中國,不復當年正氣凜然的大漢雄風,怎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在「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之後,我於二○一○年曾多次前往北京當面請教鄭必堅先生,對當前世局與兩岸關係的意見。每次他都親切的向我詳盡說明他獨到的見解,使我獲益匪淺。他還贈送了一套《鄭必堅論集》與《思考的歷程》等著作給我,使我得以完整瞭解他思想的精髓,與「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發展的整個過程,由此激發我編輯策劃本書在台出版的動機,並得到遠見‧天下文化出版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同仁們的全力支持,終於使本書得以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中國新領導班子提出新的政策方向之時,在台灣順利出版發行,具有不同的意義,格外引人矚目。
坦白說,對於中國和平崛起所代表的意義與內涵,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清楚,也不十分關心。長期深受西方輿論影響下的台灣讀者,還經常接受諸如「中國崛起威脅論」之類的訊息,甚至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因此導致兩岸關係的緊張,使得台灣的安全備受威脅。
尤其過去兩年,由於南海與釣魚台主權爭議日益尖銳,大陸當局為了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迫不得已,採取了一系列較強硬應對的措施,引來國際上別有用心人士的批評與醜化,認為中國的崛起,必將向外擴張侵略,危害世界和平。
因此,我們選擇這個時候,在台灣出版這本書,可說適得其時。因為本書作者就是「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創始人,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理論與名詞的創造者。本書著作的時間跨距,從一九九一年六月到二○一三年十一月,長達二十二年。透過作者系統性的帶領與分析,可以讓台灣讀者正確的認識與明瞭,什麽是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又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為了充實本書的內容,鄭必堅將中國和平崛起後,與世界各國形成「利益匯合點」與「利益共同體」的新觀點,在本書做首次的正式發表。同時,他也明確指出,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勢將帶動台灣的崛起,對兩岸關係絕對具有正面的意義。這是鄭必堅首次公開,將台灣與中國和平崛起之間的關係,做完整的闡述,值得台灣讀者的注意與重視。他也針對兩岸間尚存在的一些歧異,諸如意識形態、民主化、一個中國原則等問題,坦率的提出了他的意見,很有參考的價值。
鄭必堅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就參與中共中央的機要工作,他曾經擔任前主席華國鋒與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祕書,也是前總書記胡錦濤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時的常務副校長,實際主持校務工作。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談話稿,就是由他負責整理發表的。這些難得的機遇與歷練,若非具有相當的素養與能力,是無法得到歷任國家領導人長期信任而勝任的。在這方面,鄭必堅是當之無愧,不負使命。
我對鄭必堅理論思想最為折服的一點,就是他往往可將許多由於錯綜複雜原因造成的歷史或近代事件,化簡馭繁,進行整理歸納,使讀者隨著他的敘述,得以對事件的發展一目瞭然。例如他對「諸子百家」,對「經濟全球化」,對「歷史大變局」,都以相同的方法,做了最精闢的分析。這是他的治學功力使然,非一般學者可以望其項背也。
以「經濟全球化」為例,我很驚訝的發現,鄭必堅早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就已經看到「經濟全球化」與「資訊科技化」,將對世界產業帶來的巨大衝擊。而世界諸多知名的趨勢大師或經濟學者,卻多數是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才看到這點。鄭必堅要比其他人早十餘年洞見此事,足證他的高瞻遠矚,已超越世界級的學者之上。
他又形容經濟全球化像是「一刃的兩面」,既能利人,亦能傷人。所以,他建議中國當局,還是應採取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做法,但同時要採取「趨利避害」的防範措施。正因為如此,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與二○○八年國際金融海嘯的災難中,不但能持盈保泰,安度難關,還成為拯救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希望所在。可見鄭必堅的真知灼見,足以「一言興邦」。
他在二○○六年率先提出的「中國夢」,現在已成為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全體中國人共同追求的理想。鄭必堅雖已年過八十,卻仍能不斷創新思維,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發展指引新的方向,並廣為大家所認同接受,令人欽佩。
同時,他的言論許多地方都是直言不諱,充分體現他實事求是的真性情,有別於大多數政治人物語多含蓄隱晦的風格。我在這裡特別節錄一些讀來有大快人心之感的名言,與各位讀者分享:
「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與蘇共以及東歐那一大批黨完全不同。經過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但自己起來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而且重新思考中國問題,重新思考國際、國內這兩個大局。」(126頁)
「中國共產黨的重新思考,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是『被迫』的。這又是一個『勢逼處此』!——我們自己的嚴重挫折,加上第三輪經濟全球化,『逼』出了鄧小平理論。」(126頁)
「共產主義的綱領,我們要堅持;但是實際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那在很長很長歷史時期內是不可能實施的。」(172頁)
「中國只輸出商品,不輸出革命。」(243頁)
走筆至此,心中憂國之情難免油然而生。想到台灣,想到中華民國,我們的兩岸政策,曾幾何時落得只剩下短短的二十一個字:「台灣未來的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之」,完全無法精確表達台灣到底期待怎樣的兩岸關係,以及期望從中得到如何的利益與結果。台灣應盡速擺脫只知依附美、日,以及與大陸對抗的冷戰舊思維,在當今新型的大國關係中,遊走其中,謀取最大利益,才是符合馬英九總統「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政策應有的正確做法。唯有如此,才能再造台灣的輝煌。
這確是當前台灣人民與政府均需嚴肅面對,認真思考的問題。
吳建國
二○一四年一月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二○○九年十一月,我率大陸代表團到台北,參加由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在開幕式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的回顧和前瞻〉的主旨講演。代表團成員在台灣停留了一個星期,除了參加會議以外,還有機會與台灣各界人士,包括民進黨的一些政治人物,接觸交談,更用四天的時間,環島走了一趟。割捨不斷的民族親切之情,多姿多彩的台灣風土人情,以及一次次坦誠熱情的交流對話,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會後,「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的策劃者和主辦人,時任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的吳建國先生,多次來北京與我就國際形勢、中國和平崛起及兩岸關係等議題深入交談。他閱讀了我關於這方面的一些文章,遂向我提出由他策劃成書,在台灣出版的願望,盛情難卻。
呈獻給讀者的這部專題論集《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就是吳建國先生彙集了我自一九九一年六月至二○一三年底的有關論文和講演,精心策劃而成的。本書分為六個部分,即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由來、根據、內涵、前景、深化,以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每一部分吳建國先生都寫了前言簡介。
中國的和平崛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道路,是以前總書記胡錦濤為主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後,用科學總結和繼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經驗,精闢分析和把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重大戰略機遇,針對國際輿論中此起彼伏的「中國崛起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而鄭重提出的。應當說,「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提出和確立,乃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一個深刻的揭示,也是中國政府和國家,對內對外方針相統一的一個鮮明體現。
從歷史角度看,這一重大決策,歸根到底,是來自鄧小平先生帶領中國政府,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一九七八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果斷決策下,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抉擇,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政府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
三十六年來,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與習近平,一以貫之,薪火相傳,接力推進,領導中國政府和國家在各種複雜形勢下,始終努力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從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世界近代史上,一切後興大國所從未有過的獨特道路——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我們還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這一重大決策,受到世界各國政治家、戰略家、外交家、企業家,和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普遍關注和重視,在國際上產生了幾乎可說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和平崛起發展道路」需要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這方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重大方針,就是「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全方位地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建立和發展不同領域與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特別是「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已經明確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前總書記胡錦濤和前總理溫家寶也多次在重要的國際場合鄭重提出這一理念。
實際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利益匯合點」,已是一種客觀存在。二○○八年以來,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家和經濟體,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就是特定條件下各方利益的最大匯合點。現在,中國與美國等主要經濟體之間,需要相互適應與調整,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變化,和各自國內結構調整,這又應成為各方新的利益匯合點。這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就是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互補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貿易領域向投資領域擴展,國際投資合作正在進一步加強。
總之,在共同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之後,中國與世界的「利益匯合點」較之以前是更多,而不是更少了;中國與世界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上構建「利益共同體」的條件是更加充分,而不是更為欠缺了。
寫到這裡,我還想順帶說明一點,就是關於「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這兩個說法的問題。人們閱讀這部專題論集時會發現,我從二○○二年起,曾多次使用「中國和平崛起」的提法。既然是闡發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為什麼又要提「中國和平崛起」呢?
首先,這是因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雖然用語不同,其實是同一個意思,本質內涵完全一致。其次,在那時提出「中國和平崛起」,有其現實針對性。「和平」是針對某些國際輿論正開始起勁鼓吹的「中國崛起威脅論」,而「崛起」則是針對「中國崩潰論」。第三,這一說法還反映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特點。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這無疑應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過程;而在當前階段,即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國的和平發展具有抓住機遇,而實現由不發達到中等發達的歷史性飛躍的重要特點。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九點四,估計今後在「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總要求下,相當時期大約也不會低於百分之八。這是一個在中央和國家自覺推動,和廣大人民共同努力下的飛躍和突變的過程,是一個全民奮起、艱苦創業、擺脫貧困、實現小康,進而從不發達國家轉變為中等發達國家的過程。歸根到底,是一個為著和平的目的而發展、抓住和平的機遇而崛起的過程。總之,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這兩個說法,用語不同,針對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不同語境而互為通用或選擇使用。當然,作為一條體現中央和國家,對內對外方針相統一的國家發展戰略道路,其說法又應是統一的,這就是「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我一直強調,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就是和平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對外求和平、對內求和諧、兩岸求和解為其本質特徵。承認一國兩制,就意味著兩岸之間,不再有意識形態之爭與社會制度之爭,而是謀求雙方和平相處、兩岸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六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發生了重大深刻的變化,最鮮明的特點是由軍事對峙、隔絕對立,走向交流合作、對話協商。這種轉折儘管歷經曲折坎坷,但畢竟取得了重大進展,一種新型的兩岸關係正在逐步加速形成。在此過程中,雙方政策的不斷調整,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我以為,兩岸關係三十多年的發展積累的全部成果,最重要也最寶貴的是,兩岸同胞在一百多年的歷史上,第一次有難得的機遇和良好的條件,在全球競爭中攜手合作,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共同奮鬥。
兩岸長期以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全新的交集,面臨著匯聚到實現民族振興的共同大道上的重要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兩岸關係,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前總書記胡錦濤在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篇重要講話中說,「回顧近代民族之艱難奮鬥歷程,展望未來民族之光明發展前景,我們應該登高望遠、審時度勢,本著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以更遠大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勇氣、更務實的思路,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
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著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開闢兩岸關係嶄新格局的重要時刻即將到來。我衷心希望,兩岸同胞能以不懈的努力,迎來一個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時期。
謹向策劃此書的吳建國先生,和出版此書的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致以謝忱。
鄭必堅
二○一四年一月於北京
出版者的話
中國和平崛起下的兩岸思索──寫在鄭必堅新書在台出版前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革命家、思想家、政治人物及追隨者與反對者,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與離合。
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沒有歷史,哪有家國?只有失敗的歷史,何來家國?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半世紀來在台灣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先後出版了實際參與改變中國命運與台灣發展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都是廣義的英雄,他們或有英雄的志業、或有英雄的功績、或有英雄的失落。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黨國元老、軍事將領、政治人物、企業家、專家學者,以歷史的見證,細述他們的經歷軌跡與成敗得失。
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如果因此引起的爭論,我們同樣尊重,但也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每一位人物寫下他們的經歷、觀察,甚至後見之明,為歷史留下紀錄。
兩岸分隔六十餘年,已從對峙走向交流。二○一三年二月,我們出版了黃年撰述的《大屋頂下的中國》,此時出版曾擔任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智囊,及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先生的新書,意義重大。此書表達了一位中國大陸倡導「和平崛起」的戰略思想家,對兩岸關係與全球發展的長期思維,值得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及華人讀者閱讀與深思。
高希均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緣起
我們的鄭必堅在那裏?
初識鄭必堅先生,是在二○○九年十一月。他以團長的身分,率領一個包括退役將軍、退休大使在內,共二十八人的中國高層代表團,到台北出席被譽為六十餘年來,對兩岸關係影響最深遠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
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開幕典禮上發表的主旨講演,開宗明義且清晰的將台灣當前所處困境與侷限的原因點了出來:「直到今天,儘管冷戰格局早已崩潰,但台灣還沒有真正擺脫對舊格局的依附,冷戰思維依然像揮之不去的陰影影響著台海形勢」。
在結束講演前,鄭必堅特別引用一九九七年,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以「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兩大歷史性追求」為題發表講演時的一段話,總結他的發言:「中國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算起,幾代人直到今天的處境和心態,是深重的危機感,是爭取生存、發展權利不受侵害,是謀求一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二要發展和現代化,而不是什麽擴張,更不是什麽侵略」。
身為此次研討會的策劃者與主辦人,我坐在台下,聆聽鄭必堅如此真誠及語重心長的講話,心中的震撼是難以言喻。尤其,對於他最後所說的那段話,讓我回憶起與從小接受的父祖輩教訓,內容毫無二致。只是這樣的話,在今天的台灣已沒有人再說了。這是由於台灣近年來在強烈本土意識主導下,「去中國化」的結果,使得政府與人民均已放棄,過去曾長期代表中國正統政權的角色任務,甘於偏安一隅,自外於中國,不復當年正氣凜然的大漢雄風,怎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在「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之後,我於二○一○年曾多次前往北京當面請教鄭必堅先生,對當前世局與兩岸關係的意見。每次他都親切的向我詳盡說明他獨到的見解,使我獲益匪淺。他還贈送了一套《鄭必堅論集》與《思考的歷程》等著作給我,使我得以完整瞭解他思想的精髓,與「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發展的整個過程,由此激發我編輯策劃本書在台出版的動機,並得到遠見‧天下文化出版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同仁們的全力支持,終於使本書得以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中國新領導班子提出新的政策方向之時,在台灣順利出版發行,具有不同的意義,格外引人矚目。
坦白說,對於中國和平崛起所代表的意義與內涵,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清楚,也不十分關心。長期深受西方輿論影響下的台灣讀者,還經常接受諸如「中國崛起威脅論」之類的訊息,甚至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因此導致兩岸關係的緊張,使得台灣的安全備受威脅。
尤其過去兩年,由於南海與釣魚台主權爭議日益尖銳,大陸當局為了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迫不得已,採取了一系列較強硬應對的措施,引來國際上別有用心人士的批評與醜化,認為中國的崛起,必將向外擴張侵略,危害世界和平。
因此,我們選擇這個時候,在台灣出版這本書,可說適得其時。因為本書作者就是「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創始人,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理論與名詞的創造者。本書著作的時間跨距,從一九九一年六月到二○一三年十一月,長達二十二年。透過作者系統性的帶領與分析,可以讓台灣讀者正確的認識與明瞭,什麽是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又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為了充實本書的內容,鄭必堅將中國和平崛起後,與世界各國形成「利益匯合點」與「利益共同體」的新觀點,在本書做首次的正式發表。同時,他也明確指出,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勢將帶動台灣的崛起,對兩岸關係絕對具有正面的意義。這是鄭必堅首次公開,將台灣與中國和平崛起之間的關係,做完整的闡述,值得台灣讀者的注意與重視。他也針對兩岸間尚存在的一些歧異,諸如意識形態、民主化、一個中國原則等問題,坦率的提出了他的意見,很有參考的價值。
鄭必堅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就參與中共中央的機要工作,他曾經擔任前主席華國鋒與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祕書,也是前總書記胡錦濤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時的常務副校長,實際主持校務工作。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談話稿,就是由他負責整理發表的。這些難得的機遇與歷練,若非具有相當的素養與能力,是無法得到歷任國家領導人長期信任而勝任的。在這方面,鄭必堅是當之無愧,不負使命。
我對鄭必堅理論思想最為折服的一點,就是他往往可將許多由於錯綜複雜原因造成的歷史或近代事件,化簡馭繁,進行整理歸納,使讀者隨著他的敘述,得以對事件的發展一目瞭然。例如他對「諸子百家」,對「經濟全球化」,對「歷史大變局」,都以相同的方法,做了最精闢的分析。這是他的治學功力使然,非一般學者可以望其項背也。
以「經濟全球化」為例,我很驚訝的發現,鄭必堅早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就已經看到「經濟全球化」與「資訊科技化」,將對世界產業帶來的巨大衝擊。而世界諸多知名的趨勢大師或經濟學者,卻多數是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才看到這點。鄭必堅要比其他人早十餘年洞見此事,足證他的高瞻遠矚,已超越世界級的學者之上。
他又形容經濟全球化像是「一刃的兩面」,既能利人,亦能傷人。所以,他建議中國當局,還是應採取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做法,但同時要採取「趨利避害」的防範措施。正因為如此,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與二○○八年國際金融海嘯的災難中,不但能持盈保泰,安度難關,還成為拯救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希望所在。可見鄭必堅的真知灼見,足以「一言興邦」。
他在二○○六年率先提出的「中國夢」,現在已成為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全體中國人共同追求的理想。鄭必堅雖已年過八十,卻仍能不斷創新思維,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發展指引新的方向,並廣為大家所認同接受,令人欽佩。
同時,他的言論許多地方都是直言不諱,充分體現他實事求是的真性情,有別於大多數政治人物語多含蓄隱晦的風格。我在這裡特別節錄一些讀來有大快人心之感的名言,與各位讀者分享:
「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與蘇共以及東歐那一大批黨完全不同。經過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但自己起來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而且重新思考中國問題,重新思考國際、國內這兩個大局。」(126頁)
「中國共產黨的重新思考,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是『被迫』的。這又是一個『勢逼處此』!——我們自己的嚴重挫折,加上第三輪經濟全球化,『逼』出了鄧小平理論。」(126頁)
「共產主義的綱領,我們要堅持;但是實際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那在很長很長歷史時期內是不可能實施的。」(172頁)
「中國只輸出商品,不輸出革命。」(243頁)
走筆至此,心中憂國之情難免油然而生。想到台灣,想到中華民國,我們的兩岸政策,曾幾何時落得只剩下短短的二十一個字:「台灣未來的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之」,完全無法精確表達台灣到底期待怎樣的兩岸關係,以及期望從中得到如何的利益與結果。台灣應盡速擺脫只知依附美、日,以及與大陸對抗的冷戰舊思維,在當今新型的大國關係中,遊走其中,謀取最大利益,才是符合馬英九總統「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政策應有的正確做法。唯有如此,才能再造台灣的輝煌。
這確是當前台灣人民與政府均需嚴肅面對,認真思考的問題。
吳建國
二○一四年一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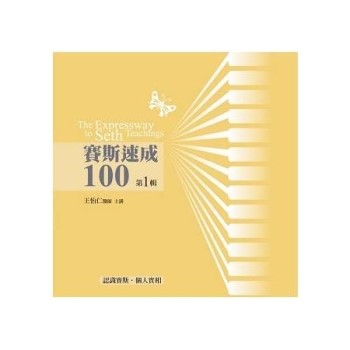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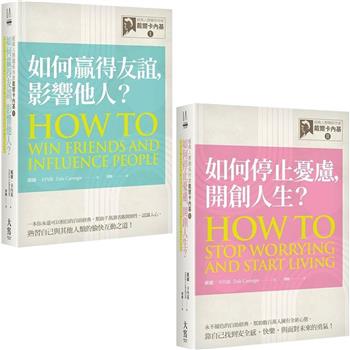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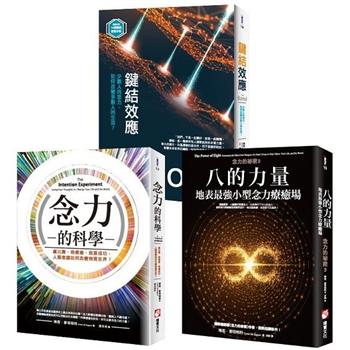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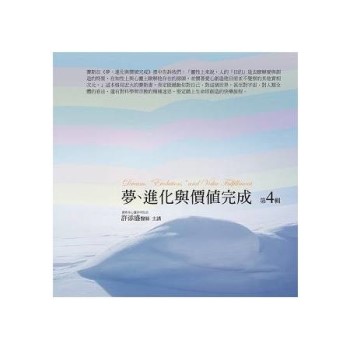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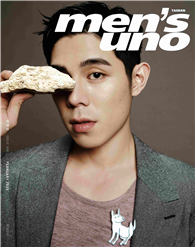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快速上手+歷年試題](記帳士)](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