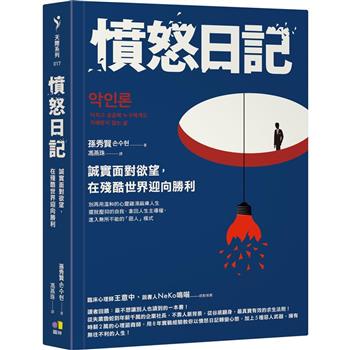第一章
險惡社會的博弈法則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東西,從政客演講、主管視察、宗教禮儀、商品展銷、電視廣告、房間裝飾,到開業典禮、教學培訓、請客送禮、請示報告……等無數現象,本質上都是表演,也是隱祕或殘酷的心理博弈。
善於偽裝、控制信息,就是博奕之道
世界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世界的真相是不可穿透的黑暗。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世界看起來像什麼,它就是什麼。
一隻小老虎也曾經如此認為。
某年某月某日,一頭驢被好事之徒用船帶到了山高林密、瘴氣彌漫的貴州,見沒什麼用處,便把牠放養在山下。有隻沒見過世面的小老虎正要出來覓食,一見驢那龐然大物的樣子,差點嚇暈,心想:哪兒來的怪獸?太強大了吧!
你一定看出來了,這就是文學家柳宗元《黔之驢》的故事。
這其實是一篇博弈論的經典文獻、一個識破偽裝的經典教程。它告訴我們:你在一個人面前心理弱小,其實是因為你不知道他是在偽裝強大,或僅僅長相強大!
了解別人在「裝」,心理就強大
反過來說,當你意識到這個社會是依靠「裝」而烘托出它的存在,並且能夠進行分析,你在它面前就會變得心理強大!因為「裝」的本質就是虛弱,它缺乏與真實聯繫在一起的力量。
驢長得確實很「裝」,又高又大,吼一聲震耳欲聾,似乎很強大,把小老虎嚇得半死,趕快夾起尾巴逃命。按照我們的理論,就是驢很裝酷的那種樣子,在被小老虎看見時,發出了一個資訊,快速地繞過小老虎的智力結構,刺激起牠的恐懼,然後驅動牠逃跑。
就「看上去像什麼,它就是什麼」的思維而言,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小老虎在心裡如何推理:驢長得那麼「裝」,連聲音聽起來都那麼強大,那它一定很強大;既然如此,那它要咬人,不趕快跑,難道想找死?
這一番推理自然與驢毫無關係。它僅僅發生在小老虎的心裡,是小老虎在心理弱小狀態下的妄想性推理。
驢長得那麼強大或許很無辜。但人長得很強大,卻可以利用這一點。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看電影、電視時,最喜歡觀察判斷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好像看電影、電視,就是為了找出誰好人,誰是壞人。回想一下,這種可憐的思維都是小時候看電影給害的,誰是混進革命隊伍裡的反動派,誰是在敵人心臟裡的地下工作者,從眼神、相貌上就一目了然:「好人」必然相貌堂堂,盡是帥哥美女;而「壞人」則猥瑣醜陋、獐頭鼠目。作為演員,長得這麼具有表演性,要演「好人」、「壞人」,早已事半功倍。
幸運的是,小老虎很快明白,驢的樣子或許只是長得很「裝」,而自己的害怕源於信息不對稱。因此,必須保持心理定力,以智力結構去和驢博弈,透過試探、反應,搞清楚驢是否厲害。這樣一來,注定了驢的悲劇結局。
驢的悲劇在於,牠從來沒有意識到,只要有兩個以上動物的場景,就有演員和觀眾。在小老虎的注視下,牠的存在就是一種展示、一種表演,所有的資訊都會傳遞給小老虎並被捕捉、解讀。因此,自己必須善於偽裝、控制資訊,這就是博弈之道。表演而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表演,最終的結果往往不是變得很厲害,而是看起來很愚蠢。
成功在某種意義上,取決於誰更會演戲
「世界是一個大舞臺」、「人生就是一場表演」……這是誰都知道的廢話。但很遺憾,大多數人常常會忘記自己是一個演員。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東西,從政客演講、主管視察、宗教禮儀、商品展銷、電視廣告、房間裝飾,到開業典禮、教學培訓、請客送禮、請示報告……等無數現象,本質上都是表演,也是隱祕或殘酷的心理博弈。
在特定情境中,表演往往暗藏著博弈。
像《黔之驢》中驢子的角色只是少數。社會上的表演行為,大多數時候都是有意識的產物。以下我描畫邏輯結構,捅破這裡面的玄機。
第一,社會是一個「合作—競爭」體系。一個人無法獨自生存,所以大家組成了社會,一起合作生產資源。
由於人的自私,以及誰都想獲得那種比別人厲害的感覺,因此對資源的分配,誰都想搶得多一點。
第二,資源的分配由各種遊戲規則決定,最厲害的是暴力。但在一個和平而有秩序的社會,遊戲規則只是戰略武器,不能公開使用。
能夠有效運行的遊戲規則,一定要提供讓大家遵守的理由,辯護自己的合理性。
第三,也就是說,遊戲規則在觀念和內容上必須展示給人看,因此必須表演出它的合理性;此外,在運用中,一個人或一個集團,必須透過語言、動作、粉飾等,提醒大家這個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的存在,並且必須受人遵守。
第四,因此,表演是一場又一場社會遊戲能夠繼續玩下去的靈魂。
從古至今,能夠在「社會」這個舞台上作主角的,從來只是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只有看戲的份。而這些少數人,幾乎都是善於表演,能夠制定、解釋、影響遊戲規則的人,絕不是巧合!
毫不誇張地說,表演是從古至今支配社會資源配置最核心、最隱祕的精巧技術,它打造影響力、構造權力、操縱人的心理,是政治、商業、宗教的「第一謀略」。
說出這一點讓人痛苦:成功在某種意義上取決於誰更會演戲,而失敗則是表演的失敗,暴發戶在別人眼中不是「貴族」,以及求職者無法獲得職位,本質上都是表演的失敗!
權力是種支配關係,不偽裝就等著出局
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的東西,或許也是在表演。請看下面的例子。
場景一:你走進一家服裝店,店裡裝修豪華,售貨員統一穿著制服,保持著不卑不亢的態度,裡面各種服裝擺放有致,顯得極為氣派。你的第一反應是:水準不低!
場景二:主管對你發了一通脾氣,你很委屈,然後他又好言撫慰你,這個時候,你覺得對他又敬又怕,甚至有莫名的親切感。
場景三:你從來沒有想過,主管的辦公室為什麼要單獨一間,並且裝潢高級,這不是基於建構權力的有意設置,而是很自然也不需要多想的一種現象。
場景四:你出席了某個聚會,某個你不認識的人暗示或吹噓某某長官或名人和他有某種關係。
場景五:你從來沒有想過,大專生沒有什麼「學位帽」(因為沒學位),而本科、碩士、博士有不同的學位帽,這是一種禮儀上的包裝,目的在於確認身份地位的區別。
場景六:在辦公室裡,當上司當著很多同事的面說你工作不錯時,你認為,上司只是在表揚你,你心裡樂滋滋的,越沒有想到他是在利用你打壓其他人,並可能把你推到全民公敵的境地裡。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很多我們覺得稀鬆平常卻從未加以反思的東西。越是不能引起我們反思的東西,一旦它準備操縱我們,往往輕而易舉。
比如,除非實在條件不允許,否則主管絕對會有一間單獨的辦公室,而不會和員工擠在一間大辦公室裡辦公。這麼做的目的,不僅僅是展現主管的地位、權威,尤其重要的是必須保持權力的神祕感。不設置神祕感,就無法確立權力的有效性。
權力不獨立存在,而是一種統治/被統治、管理/被管理的支配關係。維持這種關係固然需要以懲罰為後盾、以獎勵為誘導,但如果不偽裝,並不會比柳宗元筆下的那頭驢子更讓人敬畏。
成功者總能冷靜,嗅到機會
秦二世元年,也就是西元前二○九年的一個夜晚,劉邦作為秦帝國的一個鄉長,感覺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
想當初,他是一個逍遙自在的流氓,平時和人賭博,發了工資就去休閒娛樂;沒錢吃飯了,還可以領一幫豬朋狗友去自己嫂嫂家混吃混喝。但是,自從接了個押一幫罪犯去驪山充苦役的差事,這種中產階級的美好生活就成為了往事。
當時的情況是,雨一直下,氣氛不算融洽,罪犯們利用大雨的掩護,一會兒就逃走幾個,氣焰有點兒囂張。而邦哥當時只有兩名小跟班,想砍罪犯,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不砍,罪犯逃光了,自己只能等著被上級砍。
人,有時候是被逼的。在社會改變的關頭,很多人的處境大致相同。但成功者比別人占據一個優勢,就是他總能冷靜下來,嗅到機會。
站在秦朝末年的那個夜晚裡,劉邦透過歲月的煙霧,好像看到了那個將端坐於「漢朝有限公司」總裁寶座上威風八面的自己。現在,他被逼著要做一筆風險投資。他要挖到第一桶金!
辦法是:裝!
還原一下當時劉演員的動作和語言。他猛灌一杯酒,很決絕、瀟灑地把碗一砸,然後充滿豪氣地對罪犯說:「弟兄們,你們要是到驪山,絕對死路一條,我現在把你們放了,逃命去吧!我也走了。」眾罪犯一愣,然後有人帶頭,其他人也跟著一起高呼:「老大,我們不走,你去哪兒,我們都跟著,給你提鞋都行!」
為什麼會有這種效果?我們來分析一下。
假定劉演員大義凜然地號召「大家一起反了」,可以判定這是一個愚蠢的策略。原因很簡單,罪犯雖然無論逃走還是革命,死亡的幾率都非常大,但僅僅是靠生命本能來驅動自己的選擇的話,選擇公然反抗,在心理上只會感覺到死得更快、更慘!石頭砸雞蛋當然無完卵,但雞蛋自己去砸石頭,豈不很蠢?
注入情感因素呢?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注入情感就給選擇注入了意義,注入了道德因素,就把他們從一個怕死的個人變成了要演一齣戲給別人看的演員!
而劉演員在那種情況下,恰恰就可以利用他的身份來給他們注入情感因素。 「放」掉罪犯逃命,儘管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但在罪犯的心裡,卻等於是劉邦冒著殺頭的危險,執意要救自己一命!
對這樣會裝的大哥,不跟著他混,跟誰?
在秦朝末年爭奪天下的殘酷較量中,僅僅從演戲的素質上來講,就決定了項霸王最終只能被劉先生淘汰出局。原因很簡單,項是「本色演員」,演的是真實的自己,因此在智力結構上缺乏防禦,而劉演的只是一個「情境角色」,真實的自己隱匿在黑暗之中,一直在窺視著對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世界如此險惡,你要懂得博奕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5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哲學 |
$ 213 |
社會人文 |
$ 220 |
成功學 |
$ 220 |
成功學 |
$ 225 |
心靈勵志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世界如此險惡,你要懂得博奕
會「裝」才不會被「唬」,這就是博奕之道!
只要懂得 識破偽裝、善於偽裝
就能在殘酷世局的心理博奕中變得強大、取得資源,一步步走向成功
上一本《世界如此險惡,你要內心強大》,分析了讓人內心弱小的原因、進而強大心靈的方法,
還獲得陶晶瑩在華人星光大道節目中,以此書勉勵所有參賽者要內心強大,讓本書不斷受到關注。
這次緊接著推出《世界如此險惡,你要懂得博奕》,作者石勇將所謂的社會「博奕法則」,詳細的說明了運作方式與破解方法,更剖析六大人格真相,以及從男人的角度如何看待女人的心理結構等生動有趣的篇章。
世界如此險惡
為什麼我們被指責時,大腦會突然一片空白?有人來借錢時,我該怎麼辦?怎樣才能戰勝自己?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東西,從政客演講、主管視察、宗教禮儀、商品展銷、電視廣告,到教學培訓、請客送禮、請示報告……等無數現象,本質上都是隱祕或殘酷的心理博弈。如果不懂得破解這些心理遊戲中控制我們的法則,就會永遠處於弱勢。
你要懂得博奕
善於博奕,首先,你要懂得識破偽裝。因為,你不知道別人在偽裝強大,才會在他面前心理弱小,注定了出局的命運。其次,你自己要善於偽裝,才能控制資訊,取得有利的遊戲規則。因為,遊戲規則在解釋中有利於誰,博奕的格局就向誰傾斜。
劉必榮(東吳大政治系教授.和風談判學院主持人) 侯友宜(新北市副市長) 強力推薦
作者簡介:
石勇
本名石求陽,青年學者,為中國多家權威媒體撰稿。
關注當代中國精神危機、社會心理變遷集結構轉型下人的命運。一隻眼睛盯著階級制度的暴力,另一隻眼睛盯著觀念歧視的暴力,用心理分析之刀,準確地插入中國社會。
出版有《被遮蔽的真相》、《心理危機》等心理、社會、政治分析著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險惡社會的博弈法則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東西,從政客演講、主管視察、宗教禮儀、商品展銷、電視廣告、房間裝飾,到開業典禮、教學培訓、請客送禮、請示報告……等無數現象,本質上都是表演,也是隱祕或殘酷的心理博弈。
善於偽裝、控制信息,就是博奕之道
世界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世界的真相是不可穿透的黑暗。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世界看起來像什麼,它就是什麼。
一隻小老虎也曾經如此認為。
某年某月某日,一頭驢被好事之徒用船帶到了山高林密、瘴氣彌漫的貴州,見沒什...
險惡社會的博弈法則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東西,從政客演講、主管視察、宗教禮儀、商品展銷、電視廣告、房間裝飾,到開業典禮、教學培訓、請客送禮、請示報告……等無數現象,本質上都是表演,也是隱祕或殘酷的心理博弈。
善於偽裝、控制信息,就是博奕之道
世界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世界的真相是不可穿透的黑暗。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世界看起來像什麼,它就是什麼。
一隻小老虎也曾經如此認為。
某年某月某日,一頭驢被好事之徒用船帶到了山高林密、瘴氣彌漫的貴州,見沒什...
»看全部
作者序
從今天起,做強大自我的主人/石勇
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困惑於人類心理的這些現象:
為什麼一個有權或有錢的人,要去羞辱一個弱者?
為什麼一個人僅僅因為沒錢,就被眾人貶損,活得屈辱不堪?
為什麼一個人因為在心理上對一些事情無法承受,就發瘋甚至自殺?
如今,人類早已走出了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筆下的原始叢林,在這個原始叢林裡,人對人是狼。但是,現實讓人沮喪,今天這個時代,人們在心理上越來越陷入「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
在等級制度的暴力、價值觀念的歧視以及心理競爭的殘酷遊戲中,我痛苦...
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困惑於人類心理的這些現象:
為什麼一個有權或有錢的人,要去羞辱一個弱者?
為什麼一個人僅僅因為沒錢,就被眾人貶損,活得屈辱不堪?
為什麼一個人因為在心理上對一些事情無法承受,就發瘋甚至自殺?
如今,人類早已走出了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筆下的原始叢林,在這個原始叢林裡,人對人是狼。但是,現實讓人沮喪,今天這個時代,人們在心理上越來越陷入「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
在等級制度的暴力、價值觀念的歧視以及心理競爭的殘酷遊戲中,我痛苦...
»看全部
目錄
作者序 從今天起,做強大自我的主人
第一章 險惡社會的博弈法則
善於偽裝、控制信息,就是博奕之道
權力是種支配關係,不偽裝就等著出局
一個人會「裝」,是厲害的必要手段
每一次博弈,都需要偽裝
稱兄道弟,往往只是一個藉口
第二章 調動最有利的資源
透過表演,掌握遊戲規則
角色不復存在,繼續演戲是愚蠢的
面試考的,是一個人對能力的表演
第三章 智性思維,破除假自我
保持冷靜和敏銳,假自我就無法支配我們
獲取心理優勢,大腦必須攔截別人的言行
權力的衝動,來自虛弱
驅散劇場氣氛,就能看清一切
第...
第一章 險惡社會的博弈法則
善於偽裝、控制信息,就是博奕之道
權力是種支配關係,不偽裝就等著出局
一個人會「裝」,是厲害的必要手段
每一次博弈,都需要偽裝
稱兄道弟,往往只是一個藉口
第二章 調動最有利的資源
透過表演,掌握遊戲規則
角色不復存在,繼續演戲是愚蠢的
面試考的,是一個人對能力的表演
第三章 智性思維,破除假自我
保持冷靜和敏銳,假自我就無法支配我們
獲取心理優勢,大腦必須攔截別人的言行
權力的衝動,來自虛弱
驅散劇場氣氛,就能看清一切
第...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石勇
- 出版社: 就是創意 出版日期:2012-11-28 ISBN/ISSN:978986320071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成功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