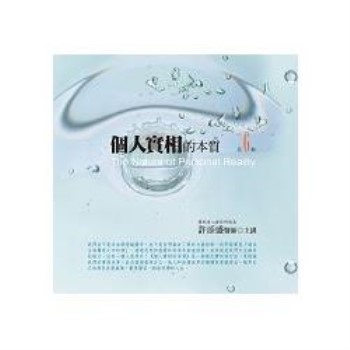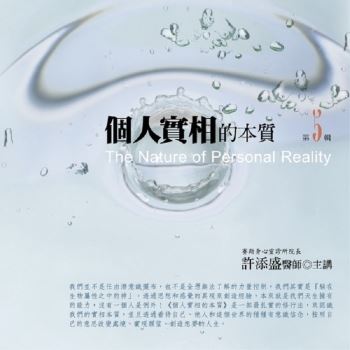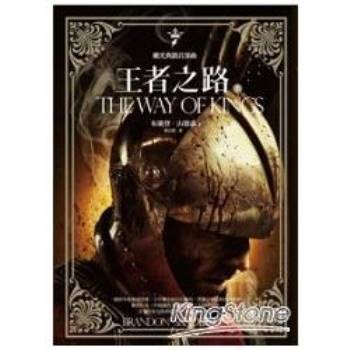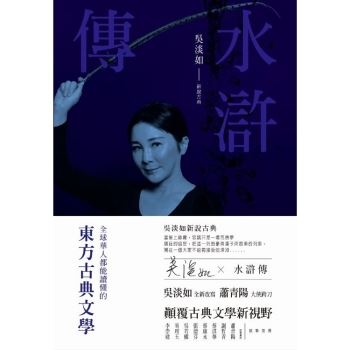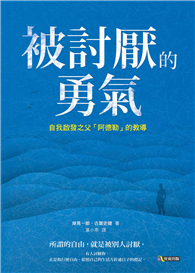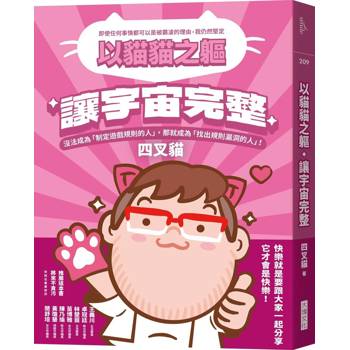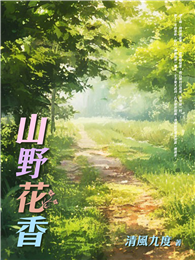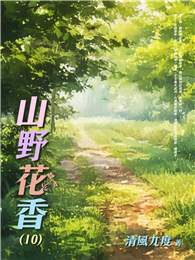蔣勳現場Scenes
創世紀
米開朗基羅在梵蒂岡西斯汀禮拜堂的屋頂溼壁畫「創世紀」,你能夠找出下列圖像嗎?
九幅 創世紀的故事
四幅 角落圖
四幅 角落圖上端的一對裸像
八幅 邊圖
八幅 邊圖上端的一對裸像
七位先知
五位女先知
二十位ignudi裸男
十幅大圓飾章
四十八位天使
米開朗基羅也在其中,你知道他在哪裡?
米蘭「聖殤」 高195公分 1563-64修改 米蘭斯佛沙古堡
這是最後的作品了,傳記上記錄八十九歲的米開朗基羅在逝世前兩三天還在雕刻這件作品。
依然是「聖殤」,是信仰與死亡的主題。
比先前一件作品去除了多餘的部分,他使單純的母與子緊緊依靠在一起。
兒子的身體細瘦修長,好像背負著母親,一起往天上升去。
死亡會是一種解脫嗎?
死亡解除了沉重的負擔,可以輕盈飛升起來嗎?
但是,只要一改換角度,作品的內容就變了,祂們不是升起,是母親用大腿的力量托著兒子的臀部,要兒子站起來,她悲傷的臉緊緊依靠孩子,好像要把所有的體溫和生活的力量都交給孩子。
這是「未完成」的作品,卻是一個偉大的美學思考者最完美的一個句點,他沒有在意作品的完成,他在意生命的完成。
第二部 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他孤獨地攀爬在屋頂上,距離地面時八公尺,他仰望著一大片空白的屋頂,想像宇宙之初,空白裏有了光,有了日月,有了水和陸地,有了最初的人類,從漫長的沉睡中甦醒,生命開始了,美,使他顫抖悸動…..
十七、西斯汀禮拜堂濕壁畫
許多記錄上顯示,米開朗基羅與教皇朱利斯二世的衝突關係,米開朗基羅被數次中斷教皇陵墓的計畫,拿不到預算,得不到支持,種種不順遂的過程,都是因為一個人的作梗,那就是聖彼得教堂的建築師布拉曼帖。
布拉曼帖在米開朗基羅的親自口述以及他人著述的米氏傳記裏,都被描述為一個充滿嫉妒心,心胸狹窄,以陰謀陷害他人的角色。
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或許有他人難以了解的複雜個性。米開朗基羅本身也對達文西充滿敵意,他多疑與易怒的性格也使我們謹慎評估他對布拉曼帖的負面看法。
布拉曼帖當時是教皇身邊紅人,負責整個大教堂改建工程,也負責許多羅馬城重建的都市計畫公共工程計畫,牽涉到巨大昂貴經費預算,或許與米開朗基羅的陵墓計畫是會有利益上的實際衝突。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皇身邊的藝術家群,明顯有派系上的鬥爭,米開朗基羅屬於翡冷翠派系,這一派的藝術家長久以來表現傑出,曾經受歷任教皇重視。而布拉曼帖則來自烏爾比諾,在北方米蘭工作過,初到羅馬,起初很受翡冷翠派系藝術家的排擠,但布拉曼帖很懂交際,結交了不少非翡冷翠派系的藝術家,共同對抗勢力龐大的翡冷翠派,贏得了教皇執政團隊的信任,取得了許多重大工程案件,因此當然對翡冷翠派有防範之心。
米開朗基羅卻一口咬定布拉曼帖是出於惡意的陰謀,從陵墓計畫的擱置,一直到接手西斯汀禮拜堂天篷壁畫製作,他都認定是布拉曼帖一手製造的陰謀陷害。
史家的說法不一,我們看到了同一個時代的菁英,在不同創作領域,形成對立,也形成激盪。
我們關心的,也許應該是作品本身,無論如何對立衝突,無可否認,布拉曼帖是西方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築師之一,米開朗基羅是最偉大的畫家,他們同時在羅馬工作,留下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傑作,或許是比任何「八卦」更有力的雄辯罷。
在一切的是非衝突之上,教皇朱利斯二世更表現出他的精明睿智。
他一定聽到各方面的意見,聽到藝術家之間惡意的彼此攻擊,但是,他做了決定,他把教皇私人進行儀式的最重要的禮拜堂的壁畫工作交給了米開朗基羅。
西斯汀禮拜堂是一座長方形的建築,夾在梵帝岡教皇宮殿與聖彼得大教堂中間,是教堂舉行重要彌撒儀式的地方,選舉新任教皇的會議也在這裏舉行,可以說是梵帝岡所有高階層神職人員的會聚所,教皇也常在這裏接見各國重要國王大臣。
這座等同於教皇私人會客室的小禮拜堂在一四七七年修建,修建的決策者是教皇西斯特四世(Sixtus IV),也就是朱利斯二世的伯父,他一手提拔自己的姪子,培養他掌權,繼任教皇。
這座小禮拜堂形式特別,為了符合傳說裏古代所羅門王的聖殿,長度有三十九公尺,寬十三公尺,高度有十九公尺多。
牆的厚度有三公尺,顯然,不只有禮拜儀式及會客的功能,也同時是維護教皇及重要權貴安全的秘密城堡。
小禮拜堂在一四八○年代建築完成,教皇西斯特四世邀請了一批藝術家在牆壁繪製壁畫,其中包括著名的波提切立,以及米開朗基羅的老師吉蘭達歐。
天篷的部分依據當時的習慣,以寶藍色做背景,彷彿天空,上面綴滿金色的點點星光。
朱利斯二世在一五○三年繼任教皇,這個小禮拜堂因為地基下陷,天篷出現裂痕。
教皇立即派人穩住建築結構,做了很多彌補的工作,但天篷上原來美麗的藍色星空則出現了很難補全的補土痕跡。
朱利斯二世因此想到在天篷壁畫上重新繪製聖經故事,他想到了米開朗基羅。
米開朗基羅在一五○八年春天接下了教皇的委托,他站在小禮拜堂中,仰望十九公尺高的天篷,看到寶藍色的美麗星空,看到星空出現破裂的隙縫,好像宇宙初始,他三十三歲,卻遠比實際年齡看來衰老許多,好像從古老的洪荒活到現代,他思索著星空,思索著「創世紀」的亙古之初,如同舊約聖經中的描述,混沌中有了光,有了日與夜,有了陸地與海洋……他凝視著三十九公尺長,十三公尺寬的巨大空間,這是一張無與倫比的空白,達文西的「最後晚餐」只有十公尺長,五公尺高,米開朗基羅顫慄著,他要在這巨大的空間中如神一般開始創造……
十八、創世紀
基督教聖經分新約與舊約兩部分,傳達的情感與信仰也非常不同。
新約是耶穌宣示的道理,充滿歷史的、人性的愛與溫暖。
舊約則不同,舊約是希伯萊民族古老的神話,是洪荒之初的宇宙成形的寓言,充滿了巨大的創世的張力,很難以邏輯理性思考。
舊約像初民凝視著渾沌的宇宙、雷火、閃電、大海嘯與大地震,生命在懼怖中活著,經驗著不可知的神的救贖或懲罰,恩寵或災難都沒有原因……
米開朗基羅是熟知「舊約」的,他年輕時聽過沙弗納羅拉的佈道,他隱約感覺到那嚴厲的罪與罰的宣告中有舊約傳述下來的初民的驚恐。
人類在走向文明嗎?人類在走向理知嗎?
米開朗基羅似乎在西斯汀小禮拜堂重新思考起舊約裏的渾沌、黑暗、鬱怒,宇宙是一片茫昧的生命最初的顫動。
宇宙中有了光,有黑暗,有了日與夜的交替,渾沌中分出了最初的秩序,彷彿生與死,彷彿春與秋,彷彿盛放與凋零,彷彿升起與降落,沒有任何原因,只是一種虛罔的輪迴……
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似乎是在用異教的思維詮釋基督信仰,他重回舊約,重回耶穌還沒有誕生之前遠古的茫昧混沌。
宇宙初開
一個巨大的人體浮在空中,上方用大筆刷過淺色調,下方刷過暗色調,非常抽象地代表了光明與黑暗,彷彿東方說的「上清為天,下濁為地」,宇宙有了陰陽。
天篷被米開朗基羅分為九個長方形空間,一大一小,交錯著,彷彿樂章的節奏,當我們抬頭仰望,我們可以看到九個長方格連成的一條長河,時而寧靜,時而澎湃。
九個長方格分成三組,每一組三個空間。
第一組順序是1. 宇宙初開 2.星球的出現 3.水與陸地分開
這一組的三個畫面都是宇宙的創造,是從無到有的最初的創世紀故事。
畫面上都只有一個長鬚的中年男子,浮沉在空中。
第一個畫面,祂好像長睡初醒,懵懂中翻身,宇宙渾沌中間有了秩序,有了黎明的光,有了黑夜。
星球的出現
第二個畫面,祂彷彿遠遠飛馳而來,以極大的權威喝斥星球出現。星球出現了,祂也耗盡了所有氣力,轉身遠遠離去。
米開朗基羅在同一個空間裏置放了不同的時間,星球創造之前,星球創造之後,他以極自由的方法表達著創造的大膽與活潑生命力。
第三個畫面,又回到較小的空間,神浮在空中,分開了陸地與水,分開了天與地。
水與陸地分開
這三個畫面,兩小一大,構成「宇宙初始」,很想易經裏的陰陽乾坤的定位。
十九、 濕壁畫
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禮拜堂的作品,材料上的歸類是「濕壁畫」(Fresco)。
濕壁畫是義大利的繪畫傳統,和歐洲北方的油畫材料不同,是以「水」調和色粉在未乾的壁畫上作畫。
作畫的過程,其實非常像工匠。米開朗基羅自己設計了一個大約十八公尺高的鷹架,攀爬在這麼高的鷹架上(差不多是六層樓的高度!),還要馱運大量的灰泥。
米開朗基羅聘請了一批故鄉翡冷翠的壁畫助手,幫助他清理壁面,清除掉舊壁畫的殘跡,塗上大約兩公分厚的灰泥底層,把牆壁處理成平滑的表面。
但是「濕」壁畫,顧名思義,必須在「濕」的壁面上作畫,因此,米開朗基羅先做完了素描草稿,把草稿上圖像的輪廓的線條打上釘孔,用白粉摹印在濕的壁畫上,接著,就必須在一天之內,趁壁畫沒有乾透,快速用水性顏料作畫,因為壁面是濕的,顏料才會被吸收,滲透固定在灰泥中,只要壁面一乾透,顏料就吃不進壁面,只浮在乾硬的表面,很容易脫落。
濕壁畫的製作過程因此註定存在著許多「工匠」的技術、材料,甚至體力的勞動,與一般繪畫的精緻優雅性質有所不同。
米開朗基羅,放掉了敲打岩石的斧、鑿,拿起調和灰泥的鏝刀,完全像工匠,站在鷹架上,仰著頭,把濕軟的灰泥塗抹在處理好的平滑壁面上。他必須計算一天之內可以畫完的大小面積,一旦灰泥塗抹好,他要抓緊時間,在灰泥未乾之前,快速用顏料完成作品。
這種速度的衝刺,好像給他一種創作的亢奮。站在高高的鷹架上,他完全像一個孤獨的君王,材料的限制,短暫的時間,他不能猶疑,不能修改,像中國水墨畫的筆觸,千錘百鍊,胸有成竹,下筆時才有大氣渾成的準確。
米開朗基羅的壁畫,也像他的雕刻,大刀闊斧,他不屑於細節斤斤計較的修飾,他使色彩與筆觸如波濤洶湧的海濤,他要使站在禮拜堂下面,距離十九公尺遠的觀看者,可以感受到色彩與筆觸的力量;這麼高的天篷、這麼遠的視覺,細節變得沒有意義,他擺脫了所有瑣碎的細節部分,使圖像成為大塊面的色彩與光影糾纏在一起的強大力量。
那樣的高度,五百年來,使所有在下面的仰望者從心底震顫起來。「創世紀」,宇宙的初始,所有的生命都聆聽著神的呼喚,所有的生命一剎那從沉睡中醒來,天地甦醒,日月甦醒,陸地與海洋甦醒,然後,在最巨大的呼喚中,人要甦醒了……
米開朗基羅創造了第一個人類──亞當,亞當甦醒了,從懵懂中醒來,一個健康壯碩的男體,如此壯碩,卻純真一如嬰孩,在天地的子宮中孕育,如同舊約聖經中說的:原來是一堆泥土,神賦予他生命,神以自己的形貌創造了人。
米開朗基羅以大筆觸勾劃出人類的初始,他如同神一般有力量的手,賦予了濕壁畫的泥土永恆不朽的生命。
二十、 人的初始與犯罪
米開朗基羅在九段連續故事的中段,以「創造亞當」、「創造夏娃」,以及「伊甸園人類原罪」構成「創世紀」鉅作的第二主題。
或許對米開朗基羅而言,在宇宙的創造中,人類的出現是最動人心魄的畫面。人類的出現,比光的出現,比日月的出現,比大地與海洋的出現更具備生命的意義,也更具備創造的意義。
他苦思構想第一個人類出現時的莊嚴。
神以巨大的威力創造了宇宙天地,但是,當祂創造了日月天地,依據舊約的傳述,祂在自己創造的萬物中覺得孤獨,因此祂以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
神也覺得孤獨嗎?神也在寂寞中需要陪伴嗎?
在十八公尺高的鷹架上的米開朗基羅,趕走了很多助手,他孤癖的性格,難以忍受愚庸的人的干擾;他無法忍受他人的錯誤或懶惰,他工作起來可以不吃不睡,創作的狂熱燃燒著他,如同烈焰,他對逼迫他工作的教皇朱利斯二世也一樣叫囂咆哮,沒有任何卑微的妥協。
他,高高站在鷹架上,教皇在他的腳下,如此渺小,他才是真正的君王,不會受任何人指使命令。
他如同神,孤獨地在他的世界中,如此孤獨,他要人陪伴,不是現世中愚庸的附和者,他要以最大的愛創造最完美的伴侶。
亞當出現了,躺臥在大地上,右手支撐上身,凝視著遠方;左手向前伸,無限等待,無限渴望的手,彷彿正等待著勃起的生命,等待著另一隻手的觸碰,使生命顫抖起來的觸碰。
創造亞當
神從遠處緩緩飛翔起來,四周圍繞著天使,拉起被風膨脹起來的衣袍,鬚髮蒼蒼,好像在宇宙的創造裏耗盡了最初的力氣,如今,祂只剩下最深的愛,用這樣的凝視,用這樣安靜的凝視,渴望著伴侶的出現,伸出右手,彷彿好幾世紀以來,所有的等待都在指尖上,一股生命的暖流源源貫注,最輕微、最細膩的生命的觸碰,亞當甦醒了,宇宙的混沌中有了人,有了肉體與性靈的愛與美。
無疑地,西斯汀「創世紀」壁畫中最驚人的傑作是「創造亞當」,這個符號成為世界性的象徵,手指與手指觸碰,隔著天與地的距離,如此遙遠,但只要有渴望,便有了愛。
近代電影「E.T」裏,人類與外星人的接觸用了同樣的手勢,米開朗基羅創造了永恆不朽的「愛」的符號。
亞當的健碩男體是米氏人體美的典範,他以濕壁畫特有的快速畫法,抓住大塊肌肉明暗的傳達,使亞當的身上流動著華貴瑩潤的光。肉體如此壯碩飽滿,精神上卻安靜內斂一如嬰孩,一種無欲念的純真,結合著希臘異教的肉體之美,與基督信仰的性靈純淨。米氏再一次完美體現了「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在希臘與基督,在俗世與天國,在肉體欲望與性靈昇華之間絕對平衡和諧的追求。
緊接在「創造亞當」之後,「創造夏娃」一幅,不僅尺寸較小,在力度上顯然也弱很多,米開朗基羅全心關注在男性的肉體上,對「創造夏娃」少了很多關心。
創造夏娃
夏娃初得肉身,有一點卑屈,屈膝合掌,彷彿向神謝恩,亞當沉睡一旁,也似乎此事與他無關。
偉大的創造者不會掩飾他真實的愛與關心,米開朗基羅如此坦然於他的「性別歧視」。
中段的「創世紀」,以人類的創造開始,也以人類的墮落結束。
在中段的第三幅作品中,米開朗基羅以「伊甸園」為主題。畫面中央是「伊甸園」的知識之樹,伊甸園中只有這棵樹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會有知識,有了知識就失去了「無知的幸福」。
舊約聖經精彩地隱喻了人類對神的禁令的背叛。
知識之樹上纏著蛇,蛇是惡魔,引誘人類犯罪,蛇也是人自己心中底層的欲望,渴望背叛,渴望出走,渴望犯罪……
米開朗基羅以同樣一個畫面空間表現犯罪前的人類與犯罪後的人類。
一邊是亞當夏娃被誘惑,另一邊是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天使以木棍驅趕,亞當夏娃羞愧恐慌,米開朗基羅沿襲馬沙奇歐的形像,使人類以犯罪的驕傲背叛神,以犯罪的自信完成自己的解放。
人類不會是受豢養的寵物,人類寧可從養尊處優的伊甸園出走,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不是神的寵物。
廿一、 災難與救贖
人類背叛之後,引發了「懲罰」、「災難」、「救贖」等第三個主題。
米開朗基羅以舊約「諾亞」(Noah)這個人物為主題闡釋人類在災難中的信仰,救贖與沉淪。
神創造了人類,人類卻背叛了神,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繁衍了子孫,子孫卻都帶著祖先的「原罪」(Original Sin)。
神對人類的犯罪充滿怒意,一心要懲罰人類,決定發起大洪水,淹沒消滅所有的人類,以示懲罰,也洗清祂創造的天地。
希伯來人相信大洪水是神的詛咒。
但是信仰可以獲得救贖,諾亞正是充滿信仰的人。因此神派遣使者通知諾亞,在大洪水來臨前,趕造方舟,並且把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各擇一公一母,放入方舟,以為大災難後交配繁殖。
米開朗基羅在第三個主題裏選擇了三個畫面:「諾亞獻祭」、「大洪水」、「諾亞醉酒」。
諾亞獻祭
「諾亞獻祭」白鬍鬚的挪亞在祭台上,祭台前方有裸體男子,有的抓住祭祀的犧牲羔羊,有人抱著木柴,似乎要準備建造方舟。
米開朗基羅以抽象拼圖的方法組織出諾亞在信仰虔誠中獲救贖的故事。
但是人類真的有救贖的可能嗎?
第三段的三幅作品,最初強調的是第二幅「大洪水」。
米開朗基羅一向喜好以單一或不多的人體構成單純的視覺力量。這或許來自於他雕刻的經驗,雕刻總是不擅長故事敘述,而往往以單一人體做為力量的象徵。
在「大洪水」中,米氏卻一反常態,營造了眾多人物構成的巨大場景。
「大洪水」
米開朗基羅不喜歡風景的描述,他沒有誇張洪水的驚濤駭浪,畫面上的「驚濤駭浪」事實上是人類自己的驚慌與怖懼,是人類自己內心深處罪的恐慌。
畫面有「方舟」,方舟卻很遙遠,米開朗基羅似乎並不相信神的救贖,他在畫面中重複著人與人肉身的依靠、擁抱、背負、牽連、扶老攜幼,那長長的在災難中的流亡的隊伍,好像是依靠著身體與身體的互相支持,通過恐懼,通過驚慌,通過致死的沮喪與疲倦。
救贖完全在人與人自己的依靠。
在基督的禮拜堂,米開朗基羅卻一貫持續讚美與謳歌人自身的價值。
災難使人類靠近,如果災難對人類有意義,便是重新使人類領悟:救贖的意義,並不在神的慈悲饒恕,而是人類自己彼此學會靠近。
米開朗基羅在「創世紀」神話的偉大作品,其實宣示的是「人」的覺醒,而不是神的權威。
最後一幅作品或許別具暗示的意義,「諾亞醉酒」,為什麼諾亞喝醉了酒呢?
「諾亞醉酒」
舊約聖經描述大洪水的災難過去,諾亞已是年邁老人,子孫承歡膝下,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一向虔誠節制的諾亞卻喝得酩酊大醉,被孫子們發現,都跑來窺看。
米開朗基羅處理了裸體的諾亞,遠處有一名紅衣男子,正勤勞耕種,好像也是諾亞。
米開朗基羅看到人性的兩面,勤勞的自己與放縱的自己,虔誠的自己與背叛的自己,信仰的自己與虛無的自己。
「創世紀」的九段畫面,沒有結束在信仰,而是結束在虛無、放縱、沉淪。
人性的價值如此艱難,使米開朗基羅不願意以膚淺的喜劇結束,他或許寧願使人類的生命的虛無、沉淪、沮喪中深沉思考存在的意義罷。
「創世紀」神話是一幅人類前所未有的史詩鉅作,繪畫裏最偉大的人性交響詩,使所有抬頭仰望的人看到自己的生死變滅。
他在長卷式的史詩繪畫兩側與周邊加入了許多以色列古代的先知、歷代君王,以及裸體的巨大男性肉身,彷彿在凝視與見證宇宙的完成,凝視著人的出現,犯罪,出走,凝視著懲罰與災難,信仰與沉淪……,自古至今,一部人類存活的艱難故事,五百年後仍然使成千上萬的人抬頭仰望。
一五○八到一五一二年,米開朗基羅以四年的時間完成「創世紀」壁畫,大部分時候他一個人在這孤獨的空間,沒有朋友,沒有助手,他把禮拜堂的門鎖起來,一個人在高高的鷹架上,常常不吃不睡,思索著,猶疑著,時而狂喜,時而沮喪。
一五一二年十月,整個作品完成,三十一日揭幕,使眾人震驚,米開朗基羅三十七歲,看起來蒼老疲倦,他像耗盡力氣的神,剛剛完成「創世紀」神話,在巨大的孤獨中聽不到任何他人的讚美掌聲。
不到半年,一五一三年的二月二十一日,教皇朱利斯二世死亡,這個不斷激發米開朗基羅挑戰更高的生命難度的統治者,在他短短的執政時間留下了輝煌的羅馬,布拉曼帖的聖彼得大教堂,米開朗基羅的西斯汀禮拜堂天篷創世紀壁畫,拉斐爾在斯坦茲宮(Stanze)的「雅典學派」鉅作,他把同時代的達文西、布拉曼帖、米開朗基羅都畫進了時代的鉅作中;朱利斯二世的名字與這些文藝復興的傑出人物一起傳世不朽,他不是一般膚淺的威權統治者,他創造一個偉大的時代,使生命可以激發出最大的潛能,他像一塊巨石,全力碰撞同一時代如同巨石的精英,激發出火花。因為朱利斯二世,建築、繪畫、雕刻……都留下了最不朽的作品。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破解米開朗基羅(隨行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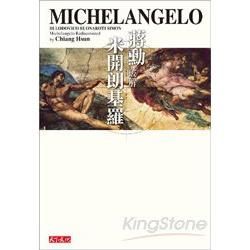 |
破解米開朗基羅(隨行版) 作者:蔣勳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2-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總論 |
$ 298 |
社會人文 |
$ 298 |
社會人文 |
$ 298 |
藝術設計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美術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破解米開朗基羅(隨行版)
米開朗基羅漫長的創作生涯,雕刻出人性的狂喜與劇痛。
米開朗基羅相信,創造的手,才是具備生命的手…如何使我們的手成為創造的手,成為給予生命的手?
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
兩個超越人類智能極限的天才,生於同一時代,相差二十三歲。
他們都深知,對方是歷史上唯一的勁敵。
五百年過去了,的確,他們還沒有找到別的對手。
時代的潮流早已翻了好多翻,
達文西以全人全腦全才通貫過去未來,
米開朗基羅純粹以無古人無來者的靈肉聖境藝術絕美,並列不朽。
創世紀以來,
只有一個米開朗基羅。
本書是蔣勳與米開朗基羅,跨越五百年後的心靈相撞!
作者簡介:
蔣勳,福建長樂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古都西安,成長於寶島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二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一九七六年返台。專攻中西洋藝術史研究,亦從事繪畫創作。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並先後執教於台大、文化、輔仁大學及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警察廣播電台「文化廣場」節目主持人、時報會館講師。近年專事美學教育推廣。
章節試閱
蔣勳現場Scenes
創世紀
米開朗基羅在梵蒂岡西斯汀禮拜堂的屋頂溼壁畫「創世紀」,你能夠找出下列圖像嗎?
九幅 創世紀的故事
四幅 角落圖
四幅 角落圖上端的一對裸像
八幅 邊圖
八幅 邊圖上端的一對裸像
七位先知
五位女先知
二十位ignudi裸男
十幅大圓飾章
四十八位天使
米開朗基羅也在其中,你知道他在哪裡?
米蘭「聖殤」 高195公分 1563-64修改 米蘭斯佛沙古堡
這是最後的作品了,傳記上記錄八十九歲的米開朗基羅在逝世前兩三天還在雕刻這件作品。
依然是「聖殤」,是信仰與死亡的主題。
比先前一件作品去除了多...
創世紀
米開朗基羅在梵蒂岡西斯汀禮拜堂的屋頂溼壁畫「創世紀」,你能夠找出下列圖像嗎?
九幅 創世紀的故事
四幅 角落圖
四幅 角落圖上端的一對裸像
八幅 邊圖
八幅 邊圖上端的一對裸像
七位先知
五位女先知
二十位ignudi裸男
十幅大圓飾章
四十八位天使
米開朗基羅也在其中,你知道他在哪裡?
米蘭「聖殤」 高195公分 1563-64修改 米蘭斯佛沙古堡
這是最後的作品了,傳記上記錄八十九歲的米開朗基羅在逝世前兩三天還在雕刻這件作品。
依然是「聖殤」,是信仰與死亡的主題。
比先前一件作品去除了多...
»看全部
作者序
大約在一九七三年,為了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我第一次去了義大利。
從巴黎出發,一路搭便車,經過阿爾卑斯山,第一站就到了米蘭。
身上只有兩件換洗的T恤,一條牛仔褲,投宿在青年民宿,有時候青年民宿也客滿,就睡教堂或火車站。
隨身比較重要的東西是一本筆記。
在巴黎翻了很多書,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料的了解有一個基礎。因此,我刻意不帶書,搭便車,四處為家的流浪,也不適合帶太多書。
我因此有機會完全直接面對一件作品,沒有史料,沒有評論,沒有考證。
作品直接在你面前,「美」這麼具體,這麼真實。
載我到米蘭的義...
從巴黎出發,一路搭便車,經過阿爾卑斯山,第一站就到了米蘭。
身上只有兩件換洗的T恤,一條牛仔褲,投宿在青年民宿,有時候青年民宿也客滿,就睡教堂或火車站。
隨身比較重要的東西是一本筆記。
在巴黎翻了很多書,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料的了解有一個基礎。因此,我刻意不帶書,搭便車,四處為家的流浪,也不適合帶太多書。
我因此有機會完全直接面對一件作品,沒有史料,沒有評論,沒有考證。
作品直接在你面前,「美」這麼具體,這麼真實。
載我到米蘭的義...
»看全部
目錄
《破解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Rediscovered by Chiang Hsun
出版緣起 井水與汪洋──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 陳怡蓁
序 為美落淚 蔣勳
第一部 蔣勳現場Scenes
1. 創世紀
2. 梵蒂岡「聖殤」
3. 戰鬥
4. 酒神
5. 大衛
6. 垂死的奴隸
7. 摩西
8. 勞倫佐之墓
9. 四件「囚」
10. 翡冷翠「聖殤」
11. 米蘭「聖殤」
第二部 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一、Michel, Angelo,米開,天使
二、奶媽是石匠的妻子...
Michelangelo Rediscovered by Chiang Hsun
出版緣起 井水與汪洋──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 陳怡蓁
序 為美落淚 蔣勳
第一部 蔣勳現場Scenes
1. 創世紀
2. 梵蒂岡「聖殤」
3. 戰鬥
4. 酒神
5. 大衛
6. 垂死的奴隸
7. 摩西
8. 勞倫佐之墓
9. 四件「囚」
10. 翡冷翠「聖殤」
11. 米蘭「聖殤」
第二部 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一、Michel, Angelo,米開,天使
二、奶媽是石匠的妻子...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勳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2-05 ISBN/ISSN:978986320124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0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美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