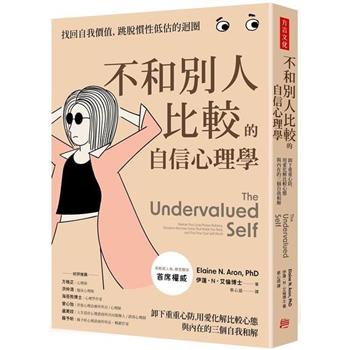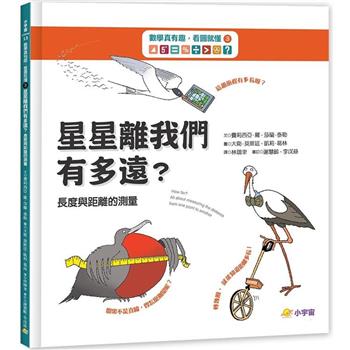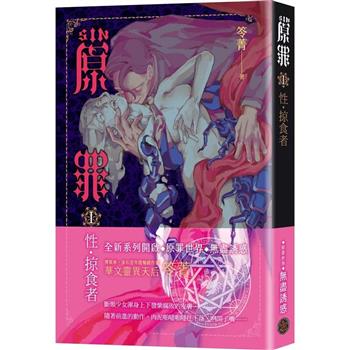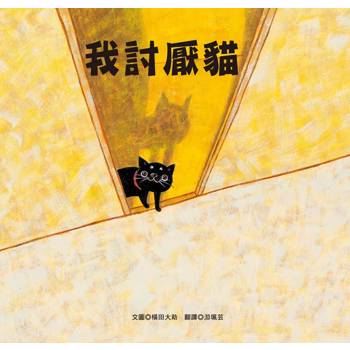序
受苦與救贖
大概還記得,中學時代,讀到余光中先生譯的《梵谷傳》,心中激盪的情緒。
那時沒有看到梵谷的原作,複製的畫作也多是黑白,印刷模糊,但還是很震撼。
讀到史東寫到:梵谷在煤礦區為工人佈道,在礦災慘劇之後,梵谷回到家,把自己僅有的衣物一份一份分好,全部捨給最需要的受難者,我仍那麼清晰記得,十幾歲的年齡,竟然掩卷無以卒讀,熱淚盈眶的記憶。
那是梵谷,是余光中先生典雅譯筆下的梵谷,是史東傳奇小說筆下的梵谷。
那個梵谷,陪伴著我通過青澀夢想的年代,夢想一個為人類救贖的心靈,這樣燃燒著自己,走進那麼孤獨純粹的世界,走進一個世人無法理解的「瘋子」的世界,走進絕望,走進死亡。
我不太分得清楚,我認識的是藝術上的梵谷,或是生命實質上的梵谷。
我分不清楚,是梵谷那一件作品打動了我,還是他整個生命燃燒的形式才是真正的作品。
我走向了文學,藝術,到了巴黎學習藝術史,那個梵谷一直跟著我。
大學的時候,我沒有讀美術系,但是整天跟美術系同學混在一起,有時候會央求他們:「讓我揹一下畫架罷!」
也許我在夢想梵谷的某一種生命吧!
在巴黎有許多機會看到梵谷的原作,看到他初到巴黎,受點描畫派影響的色彩的炫爛,但是,常常彷彿有一個聲音在耳邊輕聲說:那不是技巧!
「那是什麼?」
我想問,回頭卻沒有人。
我又去了荷蘭,從阿姆斯特丹到庫拉.穆勒,梵谷早期線條粗重的筆觸,勾勒著重勞動下軀體變形的工人或農民,我彷彿聽到如牛馬一般沉重的喘息聲音。
回程經過海牙,想到他邂逅了西嬿(Siam)一個拖著幾個孩子要養活的過了氣的老妓女。他們同居了,梵谷負擔起了西嬿一家老老小小的生活,這個故事一點也不像「戀愛」,難堪、卑微、邋遢可笑的生活。
沒有人能理解梵谷為什麼把生活搞得一團糟!
西嬿最後還是走到街頭去接客維生,彷彿重重嘲諷了梵谷:你要救贖別人?你能救贖自己嗎?
梵谷的故事是一個「失敗者」的故事。
我們要美化梵谷嗎?
是的,他看到了世界上最美麗的事物,他看到了初春大片大片綻放的杏花,他看到了起伏的山巒與麥浪,他看到了夏夜天空星辰的流轉…
但是,那是他「發瘋」之後。
他被鄰居聯名控告,要求警局逮捕強迫治療。
站在聖.瑞米的精神病房前,我從梵谷眺望風景的窗口看出去,我在問我自己:如果當時我也是鄰居,我會不會也是聯名簽署的人之一?
我愛梵谷嗎?
我了解梵谷嗎?
我知道梵谷存在的意義嗎?
但是,我隔壁的鄰人割了耳朵,一臉血跡,我能夠接受包容嗎?
梵谷丟給我們許多問題,在他自殺離開人世後,人們用一百多年的時間試圖回答,仍然無法有完滿解答。
梵谷是精神病患,但是他看到了最純粹的美的事物。
我們很正常,但是我們看不見。
正常,意謂著我們有太多妥協嗎?
我們不知道,一再妥協,我們已經流失了真正純粹的自我。
我們可能在一張「向日葵」前掩面而泣,我們可能在一張「自畫像」前驚叫起來,我們可能在一張「星夜」之前熱淚盈眶。
梵谷揭發了所有「正常人」的妥協,他明確宣告:沒有某一種瘋狂,看不見美。
但是梵谷的美太危險,我們只能面對他的畫,不敢面對他真實的生命。
二○○七年的五月,我帶著一疊稿紙,經由泰國到葡萄牙里斯本、Cascais,sintra,到倫敦,再到西班牙,在巴塞隆那,大約兩個月,寫完這本書。
其實不是「寫」,而是「整理」。
梵谷的故事,畫作,太多儲存在腦海裡,那些一本一本傳記裡的細節,那些在他畫作現場前的記憶,都留在多年來的筆記本中。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是梵谷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在巴黎,H是畫家,提議要去歐維,祭拜梵谷的墓,她的日本丈夫,雖然不學美術,也非常愛梵谷,便主動排出時間,親自開車,做一次向梵谷致敬之旅。
很熱的夏天,車子從巴黎出發,上了外環道,向北,大約兩小時可以到歐維。
歐維是個小鎮,上個世紀的七○年代還沒有很多光客,寧靜,樸素。
我們到了歐維,因為小鎮不大,很快找到了教堂,夏天午後,湛藍發紫的天空,壓迫著教堂塔尖,很像梵谷的畫
梵谷的墓就在教堂後面,與弟弟迪奧的墓並排,青灰色的石板,平貼著草地,上面簡單銘刻著VincentVanGogh1853-1890.
空氣中有松柏沉重的樹木的香味,有遠處麥田隨風吹來濃郁的麥草氣味,有烏鴉飛起來呱呱的驚叫。
忽然間,炎熱的天空中捲起一陣狂風,我還沒弄清楚,一大片石子大的冰雹劈頭劈臉擊打下來。
我跟H一家人趕忙躲進車子,冰雹打在車頂,乒乒乓乓,像是鬱怒的孩子在發洩受不了的情緒。
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次祭奠梵谷的歐維之旅。
因為整理這本書,記起了許多往事!
二○○七年七月三十日於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