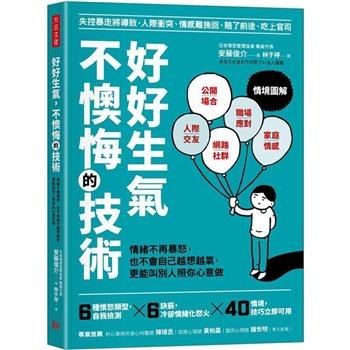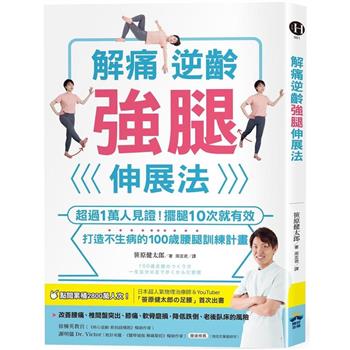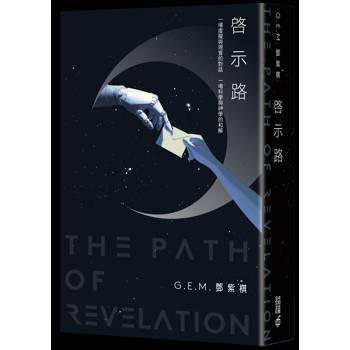蔣勳現場1
垂柳 1918–1919 140×150 cm 私人收藏
我特別喜愛莫內在接近八十歲高齡時創作的「垂柳」系列(也常常被稱為「水仙」系列(Nymphaea)或「睡蓮」(waterlilies))。
在好幾個美術館面對原作,濃厚的顏料油彩,流動隨性的筆觸線條,看來抽象率性的色彩,看久了畫面會出現極為微妙複雜的光。
高明度的黃色是眼科醫學上認為莫內白內障以後出現的「病變」色彩。但是,有一件「垂柳」裡的明黃色,讓我看了很久,像是看到莫內淚光閃爍的剎那。
那夾在絲絲垂柳之間的明黃色塊,那浮動在蔭綠水波上的一片一片的金黃,是一剎那就會消逝的光,是瞬間的神蹟,是陽光突然破雲而出,是夕陽餘暉剎那的反照,我們常常被這樣的光驚動,在迂迴的山路上,在黃昏的海邊,被驚動了,一回首那光就逝去了,什麼也沒有留下。
只有一生尋找光的畫家,到了老年,會領悟一切的尋找,都只是徒然。
驀然回首,在放棄沮喪的邊緣,那光瞬間出現,還來不及驚叫,頃刻就不見了。
莫內畫出了這樣的光。
畫中的明黃色比花朵更鮮明,比垂柳更鮮明,比藍色池水更鮮明,那一片一片的金黃,稍縱即逝,那是歲月之光,是時間,是生命本身。
書摘1
卡蜜兒──莫內的第一個女性
一八六二年莫內到巴黎,進入葛雷畫室(Charles Gleyre)。
葛雷畫室當時聚集了一批最優秀的畫家,像不多久後在印象派美術運動中嶄露頭角的雷諾瓦、西斯里、巴其爾。他們年齡相近,都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對繪畫充滿熱情。他們也大多是由外省剛到巴黎,對都會與工業現代化的一切充滿好奇。他們也一樣不滿當時國家官方美術評審制度的迂腐保守,經常在落選後聚集在一起,批評評審。一八六五年以後更因為馬奈的「醜聞」事件,使他們更有了凝聚力,經常請馬奈到畫室來看畫,彼此切磋,也逐漸討論出了新的美學觀點,如何表現自己的時代,如何堅持戶外畫畫,如何不用黑色……等等,印象派的一些主要美學論點已經在這畫室中逐漸醞釀成功。
這時莫內認識了十八歲的卡蜜兒,莫內二十五歲,他們相差七歲。
年輕的卡蜜兒在畫室擔任模特兒,他不只在莫內畫中不斷出現,也在雷諾瓦、塞尚,和其他畫家的畫中出現,能夠同時被如此多重量級的畫家畫過,卡蜜兒因此也成為那一時代被藝術史研究的人物。
不多久卡蜜兒熱戀起當時經濟條件頗困窘的年輕畫家莫內,充當莫內的模特兒,也不時給莫內財務上的幫助。
卡蜜兒因此在莫內早期畫作中不斷出現,一直到一八七九年卡蜜兒逝世,莫內還在臨終的病床前畫了卡蜜兒最後一張畫像。
一八六六年一幅「綠裙女子」(la femme en robe verte)莫內以卡蜜兒為模特兒畫的全身像,室內幽暗的光,這是一向以戶外光繪畫的莫內少見的一件室內光作品。卡蜜兒側身站立,微微轉頭向後看。上身穿深色短外套,裙裾下垂的絲緞上流動著華麗的綠色的光。
「綠裙女子」曾經參加國家沙龍展出,著名的作家左拉評論這件作品,認為是「冰冷而空洞的展場」唯一使他矚目的作品。左拉常常抨擊當時官方美術充斥古代神化歷史題材,複製抄襲古典,缺乏創意,缺乏當代現代生活的反映。這件「綠裙女子」正是莫內表現了當代人物,是他熟悉的愛人,畫家處理自己親密的主題,表現生活的現實,因此被敏感的左拉感覺到了。
卡蜜兒在一八六七年跟莫內生下第一個男孩「讓」(Jean),但是他們一直到一八七○年才正式登記結婚。雙方的家庭對這一件婚事似乎都不支持,莫內的母親早逝,父親不贊成他學畫,希望他能繼承家族經營雜貨的生意。因此莫內在巴黎學畫的前幾年完全沒有家庭的經濟援助,他的父親擺明只要莫內走繪畫一途,就不給他錢。這個婚禮父親沒有參加,支持莫內去巴黎學畫的姑姑,也似乎不願捲入家庭糾紛,同樣沒有出席婚禮。
卡蜜兒的父母對未來的女婿深感不安,擔心女兒跟著這樣一個三餐不繼的落魄畫家,會一生沒有幸福保障。女方給卡蜜兒一筆嫁妝,但要莫內簽署一份法律文件,指定這一筆錢是用來保障卡蜜兒的未來生活,莫內不能私自動用。
莫內把所有的錢都花在學畫、買畫布、顏料,租用畫室上。他對生活不講究、不關心,使卡蜜兒的父母大為擔心,也為女兒受的委屈抱怨。
然而卡蜜兒似乎不在意莫內的貧窮,她扮演著藝術家畫裡那個盡職的模特兒的角色,啟發莫內的靈感,依據莫內的要求,穿不同服裝,擺不同的姿勢,在烈日下一站數小時,一動不動,讓莫內可以安心觀察、畫畫。
把莫內早期一系列以卡蜜兒為模特兒畫下的作品排列起來,可以看到如此溫馴篤定的愛情,提供自己的身體,提供自己的生命,讓自己愛的人創作。
一般人容易看到被誇張的藝術家對模特兒的浪漫愛情,然而,卡蜜兒可能讓我們看到模特兒對畫家的愛,安靜深沉,不喧譁,不囂張,充滿內心與包容。當然那已經不是模特兒對畫家的愛,而是一個妻子對丈夫的愛,一種母性的寬容的愛。
前面提過的「公園女子」畫面裡四個不同動作的女性,一般學者認為都是卡蜜兒。卡蜜兒穿不同的衣服,做不同的姿態,坐著、站著,或動或靜,配合莫內的要求,在畫裡重複出現不同姿態。
也許今天的觀賞者不能只是讚歎莫內的畫作的偉大了,卡蜜兒做為一名模特兒的盡職、敬業、認真與耐性,也都讓人歎為觀止。
雷諾瓦畫過一張卡蜜兒,黑色長髮盤在頭上,卡蜜兒年輕美麗,穿著華麗的藍色絲綢長袍,袍子上有精細的像是波斯或印度的繡花圖案。卡蜜兒舒適地斜躺在長沙發上,後面靠著軟墊,正在讀報紙。
比較雷諾瓦筆下的卡蜜兒與莫內筆下的卡蜜兒,也許是一件有趣的事。
做為朋友,雷諾瓦畫出卡蜜兒閒適、優雅、美麗,雍容華貴的一面。
然而在莫內的畫裡,總覺得卡蜜兒在做「苦工」,她努力做出各種姿勢,為了滿足莫內畫畫的需求。卡蜜兒不再是美麗的女子,她是妻子、母親,是職業模特兒,是無怨無悔的「苦工」。
如果不是雷諾瓦留下一張如此精采的卡蜜兒畫像,只從莫內的作品中是看不到卡蜜兒的另一種美麗的。
當時畫家流行蒐集東方的服飾,特別是日本扇子、和服等等,莫內有一張畫是讓卡蜜兒穿上日本和服,手中拿著摺扇,這張畫裡,卡蜜兒不再是主角,她身上色彩豔麗的日本和服才是畫家關心的主題。莫內以極精密的技法筆觸畫下和服上線繡的圖案,有日本武士、花朵與飛鳥。連牆上一把一把扇子都仔細描寫,而卡蜜兒手執摺扇,轉身回眸,也許只是莫內要她做的一個動作。大概也可以想像,為了這一張畫卡蜜兒要站立多少時間。
莫內與卡蜜兒一八七○年結婚以後經歷了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他們雙方的長輩都不贊成這個婚姻,經濟來源被切斷,房租常常付不出,靠借貸抵押維生。
最不幸的是在一八七五年前後卡蜜兒發現罹患骨盆癌,身體一日日衰弱下去,無法工作,夫婦二人度過了生命最艱難的時刻。
就在這幾年,莫內創作突飛猛進,他創作了「日出印象」,捕捉黎明瞬間的光,大膽用快速筆觸創造印象式的描繪,顛覆了歐洲學院傳統,建立革命性的印象畫派,影響全世界的藝術發展。
然而他的畫作還是不斷被世俗保守勢力批評,畫也賣不出去。陷入生活低潮的莫內經驗著妻子重病與創作的備受責難,一個創造歷史、改變歷史的人物,卻經歷這現實生活最難堪的考驗。
書摘2
一八七二,「日出印象」
一八七一年莫內從倫敦、荷蘭一路遊歷回到法國,這一年十一月他定居在哈佛港,在這個塞納河的河口港灣一直住到一八七八年。哈佛港的風景對他產生了具體的影響,包括他一八七二年創作的「日出印象」,也是以哈佛港為背景。
哈佛港在巴黎西北邊,是風景優美的地方。巴黎最早有了火車,巴黎市民可以從聖拉札(saint Lazare)火車站方便地乘火車到達這裡。
哈佛港與巴黎的關係,很像淡水與台北的關係,都是河流出海口,都離大都會不遠,都有現代化火車可以方便到達,哈佛港聚集了印象派畫家,淡水也是日據時代到光復初期台灣印象主義畫家最愛寫生的地方,陳澄波、楊三郎、廖繼春的畫作裡都常常看到淡水,如同馬奈、莫內、雷諾瓦、西斯里等印象派畫家的畫中也總是看到哈佛港的風景。
哈佛港一到假日就都是坐火車從巴黎來度假的遊客,他們在這裡散步、戲水、游泳、玩風帆船,形成有趣而活潑的歡樂畫面。
莫內常常來往於巴黎和哈佛港之間,聖拉札火車站也變成他經常出入的地方。他感覺到現代工業對生活的改變,一種因為工業而改變的速度感、空間感,讓莫內的視覺經驗著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感覺到光的跳躍,感覺到光的閃爍,感覺到光無所不在的力量,感覺到光的不可捉摸,感覺都會市民度假時視覺的愉悅興奮與臉孔上洋溢的光。
他感覺到的光其實不只是自然光,而更接近透納在「雨‧蒸氣‧速度」這張畫裡表現的光,他試圖更積極表現與工業革命的速度感空間感有關的心理層面的光――光是視覺的迷離,但是,光同時也是心理上的感官記憶。
他在哈佛港的河口邊,架起畫架,從黑夜的盡頭開始等待,等待黎明,等待破曉,等待黑暗中一點點微微的光亮起來,是自然宇宙間的黎明日出之光,然而也是一個工業革命初期期待全新美學革命的青年畫家的興奮、好奇,與狂喜。
現在收藏在巴黎瑪摩丹美術館(Marmottan)的「日出印象」是莫內在哈佛港的一頁黎明日記。
他也許沒有想到這將是一件劃時代的偉大鉅作,他也許沒有想到這張畫將為一個藝術史上最重要的畫派命名。
站在黎明前的哈佛港邊,看到港灣裡的船隻,看到港灣碼頭一些起重的工程吊具,他全神貫注,等待水面上第一道日出的光,凝視那一道光拉長,閃爍,在水波上顫動,他拿起畫筆快速在畫布上記錄著,不斷凝視,不斷記錄,每一次記錄完,抬起頭再看那一道光,光的色彩、色溫、強度、位置,又都改變了。
莫內頑固地記錄著,他堅決要畫下日出的每一秒鐘的變化,他要抓住日出每一秒鐘光的瞬間變化。
但是當一輪紅日高高升起,一身是汗的莫內或許覺得無力而沮喪,因為他徹底發現日出之光是無法複製的。
所有傳統學院繪畫處理的日出其實都只是謊言,「日出」根本是畫不出來的。
莫內看著自己實驗的手稿,匆促的筆觸,模糊不確定的色彩,朦朧的光,一點都不清晰的物體輪廓,然而這的確是他看到的日出之光,是他完完整整面對日出記錄下來的「印象」。
他想大膽地把這張實驗性的手稿送到國家官方美術沙龍參加比賽,他知道,這將是多麼大的一個震撼彈,他知道這將引起保守的學院派多麼大的反擊、誣蔑與嘲諷。但是他不在意了,有過與真正日出最真實的對話,他自信一切誤解與批判的後果自己都可以承當。
一八七四年「日出印象」參加了比賽,當然落選,這張畫又在「落選展」展出,被眾人當話柄嘲笑,然後保守派的媒體評論家勒華(L. Leroy)撰文大肆諷刺,侮辱一個世代的年輕畫家不認真學習古典技巧,只會胡亂塗抹「印象」。
莫內的畫作名稱被拿來做嘲諷侮辱的標題,篇幅刊登在報章上。報紙傳到一群年輕藝術家手中,他們聚集在一起,朗讀這篇用意惡毒的文章,公開宣稱與官方沙龍美展的決裂,他們公開宣稱:我們就是要走向戶外、走向光、走向現代,我們就是――「印象派」。
一個被敵人用來攻擊的詞彙反而變成了新美學的歷史名稱。
長期在國家官方沙龍落選備受打擊的青年畫家,終於有了為自己團體命名的自信與勇氣。
書摘3
莫內花園
一九二二年前後是莫內受白內障拖累最辛苦的時候,在這一年他寫信給朋友,敘述到他視力衰弱到幾乎全盲,無法分辨色彩。對於一個以視覺為專業,一生努力追光與色彩的畫家,失去視覺是多麼大的恐懼與打擊。但是,他還是持續畫畫,憑藉著對色彩的記憶畫畫,像貝多芬憑藉著對聲音的記憶作曲。 記憶裡的華麗色彩,記憶裡的光,記憶裡綠色閃爍如翡翠,如孔雀的尾羽,藍色澄淨如印度夜空,金紅色如夕陽霞彩的燦爛,這些,他都看不見了,視覺裡看不見,卻在記憶裡存在著,如今他只能憑藉著記憶來畫畫了。 視覺眼科醫學無法完全解讀莫內最後晚年畫作的色彩,因為那色彩已經不純然是色彩,而是生命裡忘不掉的一片一片光的記憶。 他凝視著自己最熟悉的庭院,凝視著一縷一縷的垂柳,凝視著水池的波紋,凝視著一片一片的蓮葉,凝視著一朵一朵的睡蓮綻放,然而,都是沒有色彩的,像貝多芬凝視著那喧譁而無聲的世界。 喧譁,卻如此寂靜,或許那就是接近天籟的聲音了。 莫內也凝視著繽紛,卻是無色的繽紛,他看到了光,抽離了一切色彩的光的純粹。 他憑藉著記憶為這無色的世界加入色彩,被醫學界認為色彩異變的莫內,他在一九二〇年還是留下了令人驚嘆的絢爛繽紛色彩的畫作。 我們都悲憫聾人,因為他們聽不到我們聽到的聲音。然而,我們或許也忽略了,我們一樣「聽」不到聾人的寂靜之聲。 我們都悲憫盲人,他們看不到我們看到的色彩,然而,我們或許沒有想過,我們也看不到盲人「看」到的物象與色彩。 莫內在最後的生命從「看見」昇華到「看不見」。 老子哲學裡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意境,或許並不只是抽象理論,或許也是具體而真實的感官昇華吧。 莫內在視覺的極限痛苦過,而後他超越了視覺,他最後的畫作像一場無法記憶的夢,很確定夢過,卻沒有細節,常常只是一種光,靈光乍現,一剎那就消逝了。 光消逝了,視網膜上卻停留著記憶,我多次站在莫內畫前,那些長度到達一百兩百公尺的大畫,固定在四面牆壁上,你被畫包圍,你不再是「看」畫,而是經驗「看」與「遺忘」,「看」與「記憶」之間微妙的關係。 如同把玩中國一件長卷畫,一面「看」,一面「捲收」,我們其實在經歷「看」與「記憶」的連接。「視覺暫留」的影像,拼接、重疊、交互出現或消逝,組織成我們真實的視覺記憶,視覺記憶不全然只是「看」。 莫內的白內障要他停止「看」,而在「看」停止之後才出現了心靈上繽紛璀璨的視覺記憶。 最後幾年,莫內幾乎不再畫其他任何題材,他專注地看吉凡尼莫內花園的每一棵樹,每一株花草,每一朵花。吉凡尼是他最後的烏托邦,他要跟這相處達半世紀之久的烏托邦裡每一個黎明黃昏告別,跟水波靜靜蕩漾的池塘告別,跟一朵一朵開放又凋謝的睡蓮告別。他退回到這小小的烏托邦裡,在生命最後的六年,安靜,孤獨,寂寞,如果視覺不允許他向外眺望,他就向內靜靜觀想。觀想水池,觀想垂柳,觀想花,觀想雲影,觀想夕陽,觀想黎明。 凝視著自己小小庭園的莫內,彷彿不再是用眼睛凝視,而是用最深的記憶凝視,記憶裡的每一分每一吋移轉的光,使色彩出現,又使色彩消失。 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寫信給朋友說:我毀壞自己的畫,我瞎了! 那是在極度絕望裡的哀號的聲音,然而他始終沒有放棄畫畫,他一直拿著畫筆,一直堅持站在畫布前面。
一九二〇年開始莫內計畫畫一張大畫,是為羅浮宮杜勒麗花園中的「橘園」畫的,這期間,一九二三年,他動了眼科手術,去除白內障,視力又清晰了,一九二四年他又配戴了新的眼鏡,在幾度視覺的改變中,清晰-模糊,模糊-清晰,他一直在調整「看」東西的焦距角度,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去世,這一件如今還在橘園的最後作品「四季睡蓮」已經成為莫內留給世界最後的偉大禮物。 許多畫家在四、五十歲達到高峰,接下來是下坡,或完全終止創作,只是重複自己,而莫內在八十歲以後再一次創造了自己生命的高峰。 我們應該很認真地凝視這一組「四季睡蓮」,像凝視莫內的一生。 畫面上有看得清晰的部分,有朦朧模糊的部分,有可以一一指點辨認的部分──這是睡蓮,含苞的、綻放的、凋零的,一瓣一瓣墜落水池的。這是垂柳,飛揚的細絲,嫩黃的新芽,焦枯的枝葉,這是水波,微風中蕩漾的,月光下靜止如死的,像鏡面一樣反照一切的,那紫色淡淡的霧,微紅的旭日,夏日最後霞光的燦爛,逼到眼睛張不開來的強度,無法逼視的光,── 一切可以辨認的物象最後都無法辨認,是物象的全然解體,分解成最小最小的分子,分解成光,一片光,一縷光,一線光,都在逝去幻化的光。 一生尋找光的畫家,在離開人世之前帶領我們再看一次他看到的光,再一次感覺他在光前面的狂喜的驚叫與看到光無奈逝去的深長喟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破解莫內(隨行版)的圖書 |
 |
破解莫內(隨行版) 作者:蔣勳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6-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書畫 |
$ 277 |
繪畫 |
$ 298 |
社會人文 |
$ 298 |
社會人文 |
$ 298 |
藝術設計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藝術人物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破解莫內(隨行版)
要在西洋近代美術史上選一個大眾最熟悉的畫家,可能一定是莫內吧。
莫內的一張畫誕生了一個畫派,成為歷史上一個最重要的畫派命名,現在收藏在巴黎瑪摩丹美術館的「日出印象」,是劃時代的標誌,印象派的開啟。
莫內的時代也剛好是一個風和日麗、雲淡風輕、自由解放、沒有太大憂傷痛苦的時代,他對於光的追尋的美學信仰,也是生命的信仰,把現代人從歷史暗鬱嚴肅的魔咒中解脫出來。
為了寫這本書,蔣勳在花蓮東華大學美崙校區住了兩個月。清晨六點在鳥的叫聲裡醒來,看太魯閣大山雄峙天空,雲來雲去,千變萬化。下午工作到六點,他到四八高地散步,俯瞰遼闊的七星潭海灣,落日餘暉的反光在無限延長的海面閃爍變幻。「每一天都像是莫內的畫,每一片光都像是莫內畫裡的渴望。覺得莫內近在身邊,覺得莫內彷彿就在身體裡面。」
這不只是一本談名畫的書,而是透過蔣勳的敏感善述,活生生重現一個偉大且迷人的藝術生命。
作者簡介:
蔣勳,福建長樂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古都西安,成長於寶島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一九七二年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一九七六年返台。專攻中西洋藝術史研究,亦從事繪畫創作。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並先後執教於台大、文化、輔仁大學及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警察廣播電台「文化廣場」節目主持人、時報會館講師。近年專事美學教育推廣。
章節試閱
蔣勳現場1
垂柳 1918–1919 140×150 cm 私人收藏
我特別喜愛莫內在接近八十歲高齡時創作的「垂柳」系列(也常常被稱為「水仙」系列(Nymphaea)或「睡蓮」(waterlilies))。
在好幾個美術館面對原作,濃厚的顏料油彩,流動隨性的筆觸線條,看來抽象率性的色彩,看久了畫面會出現極為微妙複雜的光。
高明度的黃色是眼科醫學上認為莫內白內障以後出現的「病變」色彩。但是,有一件「垂柳」裡的明黃色,讓我看了很久,像是看到莫內淚光閃爍的剎那。
那夾在絲絲垂柳之間的明黃色塊,那浮動在蔭綠水波上的一片一片的...
垂柳 1918–1919 140×150 cm 私人收藏
我特別喜愛莫內在接近八十歲高齡時創作的「垂柳」系列(也常常被稱為「水仙」系列(Nymphaea)或「睡蓮」(waterlilies))。
在好幾個美術館面對原作,濃厚的顏料油彩,流動隨性的筆觸線條,看來抽象率性的色彩,看久了畫面會出現極為微妙複雜的光。
高明度的黃色是眼科醫學上認為莫內白內障以後出現的「病變」色彩。但是,有一件「垂柳」裡的明黃色,讓我看了很久,像是看到莫內淚光閃爍的剎那。
那夾在絲絲垂柳之間的明黃色塊,那浮動在蔭綠水波上的一片一片的...
»看全部
作者序
印象派的命名者──莫內
要在西洋近代美術史上選一個大眾最熟悉的畫家,可能一定是莫內吧。
因此我也常常在思考:為什麼是莫內?
有什麼原因使莫內的繪畫和大眾有了這麼密切的關係?
在巴黎讀書的時候,常常會一個人,或約三兩朋友,坐火車到奧維(Auver),在梵谷最後長眠的墓地旁靜坐,看他在生命最後兩個月畫的教堂,以及麥田裡飛起的烏鴉。
風景的沉靜荒涼,像是畫家留在空氣中的回聲,還在迴盪呢喃。
我也去過吉凡尼(Giverny)莫內後半生居住與創作的地方,有他親手經營的蓮花池,有他設計的日本式拱橋,...
要在西洋近代美術史上選一個大眾最熟悉的畫家,可能一定是莫內吧。
因此我也常常在思考:為什麼是莫內?
有什麼原因使莫內的繪畫和大眾有了這麼密切的關係?
在巴黎讀書的時候,常常會一個人,或約三兩朋友,坐火車到奧維(Auver),在梵谷最後長眠的墓地旁靜坐,看他在生命最後兩個月畫的教堂,以及麥田裡飛起的烏鴉。
風景的沉靜荒涼,像是畫家留在空氣中的回聲,還在迴盪呢喃。
我也去過吉凡尼(Giverny)莫內後半生居住與創作的地方,有他親手經營的蓮花池,有他設計的日本式拱橋,...
»看全部
目錄
出版緣起 井水與汪洋──企業界與文化界的匯流 陳怡蓁
序 印象派的命名者── 莫內 蔣勳
第一部 蔣勳現場 Scenes
聖拉札火車站
乾草堆
垂柳
睡蓮
四季睡蓮.垂柳
第二部 莫內 Claude Monet
莫內童年
莫內與漫畫
莫內與布丹
莫內走向巴黎
聖亞德斯的庭院
最初的巴黎──馬奈的影響
草地野餐
卡蜜兒──莫內的第一個女性
一八七○,莫內在倫敦與荷蘭
莫內與巴其爾
一八七二,「日出印象」
一八七五,哈佛港與阿...
序 印象派的命名者── 莫內 蔣勳
第一部 蔣勳現場 Scenes
聖拉札火車站
乾草堆
垂柳
睡蓮
四季睡蓮.垂柳
第二部 莫內 Claude Monet
莫內童年
莫內與漫畫
莫內與布丹
莫內走向巴黎
聖亞德斯的庭院
最初的巴黎──馬奈的影響
草地野餐
卡蜜兒──莫內的第一個女性
一八七○,莫內在倫敦與荷蘭
莫內與巴其爾
一八七二,「日出印象」
一八七五,哈佛港與阿...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勳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6-10 ISBN/ISSN:978986320210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0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藝術人物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