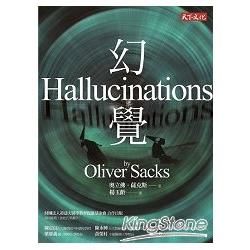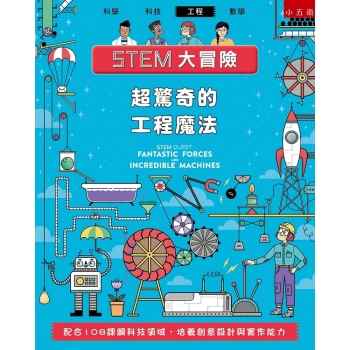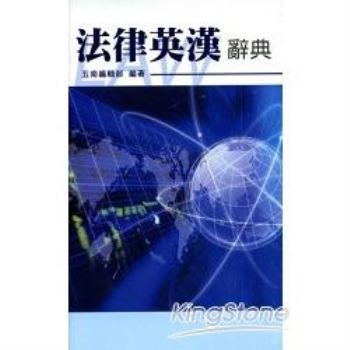神經醫學作家奧利佛.薩克斯
繼《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睡人》、
《腦袋裝了二○○○齣歌劇的人》、《看得見的盲人》之後的最新力作
你曾經看到不存在的東西嗎?
你曾經在空無一物的房間裡,聽到有人呼喚你的名字嗎?
你曾經感覺有人跟在你背後,但是轉身卻沒有看到人?
幻覺並非精神病人獨有,反而更常與感覺剝奪、中毒、疾病,或是受傷有關。
有偏頭痛的人,會看見閃亮的光弧,或是彷彿來自小人國的人物。
視力日益衰退的人,說來反常,可能會沉浸在幻視的世界裡。
幻覺,可以只是因著一次發燒,甚至是將醒或快要睡著時,而被激發,
讓人產生各式各樣的幻視,從發光的色塊,到細膩美麗的臉龐,
到恐怖的食人魔,應有盡有。
那些喪親的人,則可能會受到「已逝者」的安慰探視。
在某些情況下,幻覺有可能導致宗教上的顯靈,甚至產生靈魂出竅的感覺。
人類總是在尋求這種能改變一生的幻覺,
而且幾千年來,已經利用致幻化合物達到這個目的了。
身為1960年代加州地區的年輕醫生,薩克斯對於迷幻藥所抱持的興趣,
既是屬於個人的,也是屬於專業上的。
這些,加上他早年偏頭痛的經驗,促使他一輩子鑽研各式各樣的幻覺經驗。
在本書裡,薩克斯醫生以一貫的優雅、好奇與熱情,
將他的病人以及他自己意識狀態改變的經驗,編織成故事,
藉以闡明,幻覺向我們透露了哪些與人腦組織和結構有關的事,
幻覺又是如何影響每一種文化裡的民間故事與藝術,
以及為何產生幻覺的潛能存在我們所有人身上,是人類生存條件當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作者簡介:
奧立佛‧薩克斯
1933年生於倫敦,出身科學家與醫生世家。在牛津大學接受醫學教育,
然後在加州大學洛衫磯分校以及舊金山錫安山醫院,接受醫師養成訓練。
從1965年起,他便定居紐約市,擔任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教授,
以及安貧姐妹會(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的神經科學諮商顧問。
薩克斯醫生的文章經常刊載於《紐約書評》和《紐約客》雜誌,
以及各種醫學期刊。他也是十一本書的作者,
包括《看得見的盲人》、《腦袋裝了二○○○齣歌劇的人》、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
以及《睡人》(獲得奧斯卡獎提名的同名影片「睡人」,就是根據本書改編)。
想要更深入了解薩克斯醫生,歡迎蒞臨www.oliversacks.com網站。
譯者簡介:
楊玉齡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推薦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兒腦開竅手冊》、《奇蹟》、《念力:讓腦波直接操控機器的新科技‧新世界》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奧利佛.薩克斯是位神經科學家,一個講求人道、口才流利、而且真心誠意的溝通專家。
——《觀察家報》(Observer)
薩克斯所寫的,基本上是冒險故事,是航向無法解釋的大腦領域的故事。
藉此航程,他揭露了一片新天地,那兒的複雜和奇異,
遠勝過我們從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所能做出的推想。
——《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薩克斯首先是一位臨床醫生,可他寫起書來充滿熱情、說理清晰……
結果,便形成了某種人道的論述,探討我們心靈的脆弱,
探討引發那脆弱的身體,以及由此創造出來的世界。
——《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薩克斯用散文筆法,字斟句酌,但避用術語(幸好如此!),
來探索個人在面對怪異的神經系統疾病時,精妙的應對之道……
人道與同情兼備,他會是你想要的醫生。
——《獨立報》(Independent)
薩克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神經學家。
他針對破碎心靈的個案研究,為神祕的人類意識,提供了精采的洞見。
——《衛報》(Guardian)
媒體推薦:奧利佛.薩克斯是位神經科學家,一個講求人道、口才流利、而且真心誠意的溝通專家。
——《觀察家報》(Observer)
薩克斯所寫的,基本上是冒險故事,是航向無法解釋的大腦領域的故事。
藉此航程,他揭露了一片新天地,那兒的複雜和奇異,
遠勝過我們從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所能做出的推想。
——《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薩克斯首先是一位臨床醫生,可他寫起書來充滿熱情、說理清晰……
結果,便形成了某種人道的論述,探討我們心靈的脆弱,
探討引發那脆弱的身體,以及由此創造出來的世界。
——《每日電訊報》(D...
章節試閱
第六章 變異的精神狀態:嗑藥
一九六四年,我爸媽的朋友兼同事——精神分析師歐蓋絲特,輪休一年,要到洛杉磯來,很自然的我們覺得應該碰個面。於是我請她到我位在托潘加的小屋,一起吃了頓溫馨的晚餐。在餐後喝咖啡和抽菸時(她是個老菸槍;我很好奇她會不會一邊進行心理分析,一邊還在抽菸),她的語氣變了,她那被香菸燻得沙啞的嗓門說道:「奧立佛,你需要人幫忙。你有麻煩了。」
我答道:「胡扯,我好得很,沒什麼可抱怨的,工作和愛情都很順利。」歐蓋絲特懷疑的哼了一聲,但是沒有再提這事。
這時我已經開始服用LSD,而且要是拿不到的話,我就會改用牽牛子。(和現在不一樣,當時還沒有人用殺蟲劑處理牽牛子,以防止濫用。)星期天早晨通常都是我的用藥時間,差不多在歐蓋絲特來訪後兩到三個月,有一次我服用大量的天堂藍牽牛子。這些種子烏黑發亮,硬得像瑪瑙似的,所以我得用杵和研缽來磨成粉末,然後拌進香草冰淇淋裡。吃下肚之後約二十分鐘,我有反胃的感覺,但是當這感覺消退之後,我發覺自己置身於一個彷彿天堂般寂靜與美麗的疆域,一個沒有時間的疆域,然而,這寂靜忽然被人莽撞的打破了,一輛計程車衝上通往我家的陡坡,發出刺耳又尖銳的聲音。一個老婦人踏出計程車,受到刺激的我,立即採取行動。我奔向她,大聲吼道:「我知道你是誰,你是歐蓋絲特的複製品。你長得像她,你的姿勢和動作像她,但你不是她!」歐蓋絲特舉起雙手摀著太陽穴說道:「噢!比我想的還糟糕。」她回到計程車上,沒有多說一個字就離開了。
下一次碰面時,我們有很多東西要談了。在她認為,我之所以認不出她,把她看成「複製品」,是一種防衛情結,是一種只能稱之為精神病的分裂狀態。但是我不同意,我堅稱,把她看成複製品或冒牌貨,是神經科學方面的原因,是感覺與感情脫鉤所致,是因為辨識能力(那是完整的)沒有伴隨應有的溫暖和熟悉感情。這種矛盾,導致那個符合邏輯但卻荒謬的結論:「她是複製品」。(這種症候群稱為「凱卜葛拉斯症候群」,有可能發生在精神分裂患者身上,但也可能伴隨失智症或精神錯亂一起出現。)歐蓋絲特說,不論哪一種觀點正確,每個週末都服用改變精神狀態的高劑量致幻藥,單單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我內心具有某種程度的需求或衝突,而我真的應該去找位治療師來探討這個問題。(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道她說得對,而我也在和她談話後一年,開始去看一位分析師。)
※
一九六五年夏天有點過渡時期的味道:我已經完成加大洛杉磯分校的住院醫師訓練,離開了加州,但是還要再等三個月,才會去紐約接一個研究醫師的職位。這原本應當是一段甜美的自由時光,是我在加大每週工作六十甚至八十小時之後,格外需要的美好假期。但是我卻不覺得自由;沒工作,反而令我失了重心,有一種空虛和無架構的感覺。當我住在加州時,危險的是週末時段,那是服藥的時段。如今回到家鄉倫敦,眼前有整個暑假等著我,有如一個延長為三個月的週末。
於是,在這段閒散胡搞的時光,我濫用藥物的程度又更深了,因為不必再局限於週末。我想試試靜脈注射,那是我以前從來沒做過的。我爸媽都是醫生,當時不在倫敦,整棟屋子都是我的天下,我決定到他們設在一樓的診療室藥櫃裡挖寶,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貨,來慶祝我的三十二歲生日。在那之前,我從未服用過嗎啡或任何鴉片劑。我選了大號注射器——何必在意劑量呢?把自己舒舒服服的安置在床上後,我抽取了好幾小瓶藥物,將針頭刺入靜脈,緩緩注入嗎啡。
不過一兩分鐘,我的注意力就被一陣騷動給吸引了,騷動來自我掛在門上的一件晨衣的袖子。我專心凝視著那袖子,而在我的凝視下,袖子慢慢演變成一幅迷你、但極為詳細的戰爭場景。我可以看見各種顏色的錦繡帳篷,其中最大的一頂飄揚著一面皇家錦旗。場上還有很多披掛馬飾、精神抖擻的馬匹,騎在馬背上的士兵,身上的盔甲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另外還有拿著長弓的人。我看到吹笛手將長長的銀色笛子舉到嘴邊,然後,我忽然聽到隱約傳來的吹笛聲。我看到成百上千個人——兩支軍隊,兩個國家,正準備決一死戰。這時,我完全忘記那只是我晨衣袖子上頭的一個小點,忘記我其實人在倫敦,躺在床上,時間是一九六五年。注射嗎啡之前,我在看傅華薩的《聞見錄》和《亨利五世》,如今兩書的情節在我的幻覺中合併起來了。我察覺到自己從空中鳥瞰的場景,原來是一四一五年底的亞金科特,是即將開戰的英國與法國大軍。而且我知道,在那頂飄揚著旗幟的大帳篷裡,正是亨利五世本尊。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想像或幻覺這一切;我覺得眼前這一切都是真的。
過了一陣子,整個場景開始變淡,而我也開始有一點察覺到,我其實身在倫敦,嗑藥嗑得發昏,在我的晨衣袖子上幻覺亞金科特。這真是一趟令人迷惑又忘我的體驗,但是現在已經結束了。藥效退得很快,亞金科特幾乎完全消失無蹤。我瞥一眼手錶。我是在九點半打嗎啡的,現在是十點。但我總覺得有點怪怪的,我打嗎啡的時候是晚上九點多,現在天色應該更暗才對呀。可是不然。戶外變得更亮,而非更暗。這時我方才明白,現在的確是十點,只不過是上午十點。原來,我動也不動的凝視著亞金科特超過十二個小時了。這令我大為震驚,也把我澆醒了。我終於明白,人有可能將生命裡的好幾天、幾夜、幾週,乃至幾年,全都浪擲在鴉片的恍惚狀態中。我一定要讓我的鴉片初體驗就等於我的鴉片終體驗。
※
一九六五年夏末,我回到紐約,開始從事神經病理學以及神經化學的博士後研究。這年十二月,我諸事不順:在加州住了幾年之後,我發覺很難適應紐約的生活,一場戀愛也走調了,我的研究更是糟糕,而且我發現自己不是實驗科學家的料。沮喪又失眠的我,為了要入睡,一再增加安眠藥水合氯醛的劑量,高達一般用量的十五倍。雖然我設法屯積了一大批貨(在我工作的實驗室裡,到處搜刮),但是在聖誕節前不久的一個陰霾的星期二,終於還是用光了,於是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在沒有安眠藥相助之下,上床睡覺。我睡得很不安穩,一直被噩夢或是怪夢打斷,而且我發覺在還沒睡著時,對聲音極為敏感。紐約西村的砌石街道上,總是有卡車轟隆轟隆駛過;這種時刻聽起來,聲音響亮得簡直就像要把石頭碾成粉末似的。
感覺自己有點不穩,於是我決定改搭地鐵和巴士去上班,不要像往常一樣騎機車。在神經病理科,星期三是切腦的日子,而且這天輪到由我來為一個腦子進行水平切片;在切片同時,一邊辨識其主要結構,順便觀察是否有任何不正常之處。這些事我通常很拿手,但是那天我發覺自己的手明顯在抖,令我很難堪,而且也很慢才想得出那些解剖名詞。
這部分工作結束後,我和以往一樣,到對街買杯咖啡和三明治。然而,在我攪拌咖啡時,突然發現咖啡變成綠色,接著又變成紫色。我抬起頭,嚇了一跳,我看見一個在櫃臺結帳的顧客,竟然頂著長鼻目動物的腦袋,有如一隻象海豹。我慌了,趕緊丟了張五元鈔票在桌上,跑回對街去搭巴士。但是巴士上所有乘客似乎都長著一顆光滑潔白的腦袋,就像一顆顆大雞蛋,上面嵌著閃閃發光的大眼睛,宛如昆蟲的多面複眼。他們的眼睛好像能突然彈出,更增添了恐怖和詭異的感覺。我知道自己是在幻覺中,或是正在經歷某種怪異的感知障礙,我沒有辦法阻止腦裡的狀況,但至少得控制外表,在面對身邊的昆蟲眼乘客時,不要驚慌或是尖叫或是發作緊張症。要做到這一點,我發現,最好的辦法是書寫,清楚描述我的幻覺,詳盡得有如臨床觀察。藉由這樣做,化身為觀察者,甚至是探險家,我就不再是個內心發狂的無助受害者。我一向隨身攜帶筆和筆記本,在幻覺一波接一波席捲上身之際,我開始拚命的寫。
描述,書寫,一向是我面對複雜或恐怖情境的最佳對策,雖說從沒在這麼可怕的環境下測試過,但是很有效。藉由在實驗筆記本裡描述正在發生的狀況,我總算能保持表面的自制,雖則幻覺依舊存在,依舊不停變化。
我設法在正確的巴士站下了車,換乘地鐵,即使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在動,要不轉得讓我暈眩,要不就是傾斜,甚至上下顛倒。而且我也設法在正確的地鐵站下車,也就是我家附近的格林威治村。當我走出地鐵站,周圍的建築物好像都在搖擺,從一邊飄到另一邊,就像狂風中的旗幟。我總算平安回到公寓,沒有遭攻擊或逮捕,或是被路上呼嘯而過的車子撞死,這讓我大大鬆了一口氣。一進到家裡,我就覺得必須與人聯絡——一個和我很熟的人,一個既是醫生也是朋友的人。凱蘿是理想的人選,五年前,我們一同在舊金山當實習醫生,並結為好友,現在我們又都在紐約市。凱蘿會了解的;她會知道該怎麼辦。
我用顫抖的手撥了她的號碼。
「凱蘿,」她一拿起聽筒,我就說:「我要跟你說再見。我瘋了,精神錯亂,我得了精神病。是今天早上開始的,而且愈來愈嚴重。」
「奧立佛!你剛才吃了什麼?」凱蘿叫道。
「沒有啊,所以我才這麼害怕。」我答道。
凱蘿想了一下,又問:「還是你剛剛停吃了什麼?」
我說:「給你說中了!我最近一直在服用高劑量的水合氯醛,但是昨天晚上沒貨了。」
凱蘿說:「奧立佛,你這個傻瓜!你做什麼事情都做過頭。你得了典型的震顫性譫妄。」
這真令人鬆了一口氣,震顫性譫妄(也就是酒精戒斷症候群)總比精神分裂好。但是我也很清楚那個危險性:像是思緒紊亂、失去定向力、幻覺、妄想、脫水、發燒、心跳加快、虛脫、發作疾病、死亡。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別人身上,我一定會建議馬上去醫院掛急診,但是換作我自己,我希望能夠熬過去,順便體驗這整個過程。凱蘿答應今天過來看顧我;之後,如果她覺得我獨處沒問題,她就改成每隔一段時間過來看一下,或是打個電話來;如果她覺得有必要,再向外界求助。有了這層安全網,我的焦慮感大部分都煙消雲散,甚至還有一點兒享受震顫性譫妄裡的幻象(雖然無數的小動物或昆蟲一點都不令人愉快)。幻覺持續了將近九十六個小時,等到終於停止後,我已經虛脫得不省人事了。
第六章 變異的精神狀態:嗑藥
一九六四年,我爸媽的朋友兼同事——精神分析師歐蓋絲特,輪休一年,要到洛杉磯來,很自然的我們覺得應該碰個面。於是我請她到我位在托潘加的小屋,一起吃了頓溫馨的晚餐。在餐後喝咖啡和抽菸時(她是個老菸槍;我很好奇她會不會一邊進行心理分析,一邊還在抽菸),她的語氣變了,她那被香菸燻得沙啞的嗓門說道:「奧立佛,你需要人幫忙。你有麻煩了。」
我答道:「胡扯,我好得很,沒什麼可抱怨的,工作和愛情都很順利。」歐蓋絲特懷疑的哼了一聲,但是沒有再提這事。
這時我已經開始服用LSD,而且要是拿...
作者序
【前言】領會幻覺的力量
十六世紀初,第一次有人使用hallucination(幻覺)這個字時,代表的意思只是「神遊的心思」。直到一八三○年代,法國精神病學家艾斯基羅(Jean-Étienne Esquirol)才賦予此字現在的意思——在那之前,hallucination就只被當做是「幻影」。hallucination的精確定義還滿多變的,主要是因為不容易釐清幻覺、錯覺與幻象之間的界線。但是一般說來,hallucination定義為「對於不存在現實世界之事物的知覺」,也就是「看見或聽見不存在的事物」。1
就某個程度而言,知覺是可以分享的,比如你我都同意那兒有棵樹;但是如果我說,「我看到那裡有一棵樹,」可是你看不到,你就會認為我的「樹」是幻覺,是我腦裡或心裡捏造出來的東西,是你或其他人感覺不到的。不過,對於幻覺者來說,幻覺看起來十分逼真,能從各方面模仿知覺,首先就是,幻覺都能投射到外在世界。
幻覺常常會嚇到人。有時候是因為內容的關係,例如房間裡有隻大蜘蛛,或是有個身高只有十五公分的小矮人,但是,更基本的問題在於「沒有一致同意的確認」;沒有人看見你看見的東西,於是你很驚駭的發覺,那隻大蜘蛛或小人兒必定是「在你的腦袋裡」。
當你想到一般的影像,例如一個四方形,或是某位朋友的臉,或是艾菲爾鐵塔,那個影像只會留在你的腦海裡,並不會像幻覺般投射到外部空間,而且也不會像知覺或幻覺那般詳細。你能主動創造這樣的自發影像,而且可以隨喜好來修改。然而幻覺不同,你是被動的,而且無法操控。幻覺自作主張的駕到,而且高興出現就出現,高興消失就消失,不管你喜不喜歡。
還有另一種幻覺,有時候稱為假性幻覺,這種幻覺並沒有投射到外部空間,而是呈現在當事人的眼瞼內。這類型的幻覺通常發生在快睡著前、眼睛閉著的時候。但是這種幻覺具有所有幻覺的特徵:非自主、不能控制,而且可能具有超自然的色彩和細節,或是詭異的形狀和變形,與正常視覺意象很不相同。
幻覺有可能和錯覺或是幻象部分重疊。譬如說,當我看著某人的臉時,如果只看見半張臉,這叫做錯覺。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分界線就不那麼清楚了。如我看到某人站在我面前,但是我看到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模一樣的五個人,那麼這種「視物顯多症」可以算是錯覺或幻覺嗎?如果我看到某人從左到右穿越房間,然後看到這人不斷重複同樣的動作,一次又一次,這種重複(所謂的視覺重複),應該算是一種知覺錯亂,還是幻覺,或兩者皆是?如果一開始真的有東西在那裡,例如一個人,我們傾向於稱之為錯覺或幻象,如果是完全無中生有,就說是幻覺。但是,我有很多病人幻覺、幻象以及複雜的錯覺全都經歷了,三者之間的界線有時候很難劃得清楚。
※
雖然幻覺現象可能和人類的腦袋一樣古老,但是我們對幻覺的了解卻是在最近幾十年才大大增強的。2尤其是因為我們現在擁有的科技能夠進行腦部造影,監測正在經歷幻覺者的腦部,觀察其電流和代謝活動,讓我們增加了許多這方面的新知。這類科技加上植入式電極研究(植入需要動手術的難治型癲癇病人腦部),讓我們能釐清各種幻覺是由腦部哪些部分負責的。譬如說,右下顳葉皮質裡有一個區域和臉部認知有關,如果出現異常活動,可能會令人產生臉部幻覺。而腦部另一側相對的區域,正常情況下掌管的是閱讀——也就是梭狀回裡的視覺文字處理區;如果這裡受到不正常刺激,可能會產生字母或假字的幻覺。
幻覺屬於「正向的」現象,與意外或疾病造成的負向症狀相反,而傳統的神經科學多半是奠基於負向症狀。幻覺的現象學通常指向腦部結構及其相關機制,因此有潛力提供與腦部功用更直接相關的洞見。
※
幻覺在我們的心靈生活中,總是占有一席重要之地。事實上,我們忍不住會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幻覺經驗,醞釀出我們的藝術、民間傳說乃至宗教。我們在偏頭痛或其他狀態下所看見的幾何圖形,是否預示了原住民藝術的基調?小人國幻覺是否製造出民間傳說中的精靈、小魔鬼、小妖精以及仙子?可怕的噩夢幻覺,像是被邪靈壓身、導致窒息,是否部分造成了我們的惡魔、女巫或邪惡外星人的概念?另外,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種「狂喜的」癲癇發作,對於激發我們產生神聖感,是否也扮演了一部分角色?幻覺的這種無實體性質,是否鼓勵了我們去相信鬼與靈魂?為何目前所知的每一種文化,都會去尋找並發掘迷幻藥物,而且首要的目的都是為了行聖禮?
這並不是新思潮。一八四五年,戴玻以蒙(Alexandre Brierre de Boismont)在第一本系統性探討這個主題的醫學書裡就已論及,那一章的標題是〈與心理學、歷史、道德以及宗教有關的幻覺〉。有些人類學家,包括拉伯理(Weston La Barre)和舒爾茲(Richard Evans Schultes),記錄了幻覺在世界各地不同社會裡的角色。3這些最初看起來只不過是神經怪癖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會讓我們愈來愈深入而廣泛的了解到,幻覺在文化上有多重要。
※
至於範圍廣闊又迷人的夢境(或許也可以稱得上是某種幻覺),這本書不打算多談,只稍微觸及某些幻覺具有的像夢一般的性質,以及在有些癲癇發作時會出現的如夢狀態。有人曾經主張做夢狀態與幻覺是連續性的(尤其是催眠以及半醒狀態的幻覺,特別有可能),但是一般說來,幻覺和做夢還是很不相同的。
幻覺似乎常常具有跟想像、做夢或是幻想一般的創造力,或是像知覺般有鮮活細節與客觀性,但這些都不是幻覺,雖然都可能和幻覺具有某些共通的神經生理機制。在意識與心智生活中,幻覺是個獨一無二的特殊類別。
此外,精神分裂患者所經歷的幻覺,也需要分開來考量、以專書探討,因為那類幻覺無法與病人深深改變了的內心生活和外在環境脫鉤。也因此,本書也較少著墨精神分裂者的幻覺,而會比較聚焦於器質性精神病的幻覺。這是一種暫時性的精神病,有時候與精神錯亂、癲癇、濫用藥物以及某些醫療狀態有關。
※
許多文化對於幻覺的態度,就像對夢境一樣,視為一種特殊的、享有特權的意識狀態——是透過靈修、冥想、藥物或獨處,主動追尋來的。但是在現代西方文化裡,幻覺較常被認為代表瘋狂或腦袋出了大問題——雖然大部分幻覺都沒有這種黑暗的意涵。而且這裡頭還包藏了很大的恥辱成分,使得病人往往不願承認自己有幻覺,深怕朋友甚至醫生會把他們當成瘋子。在這方面,我倒是相當幸運,無論在開業或是與讀者通信時(我把後者當成開業的延伸),都遇到許多願意和我分享親身經驗的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表示說,希望講述自己的故事能幫忙減輕通常環繞在這個主題周圍的殘酷誤解。
於是,我把這本書想成某種幻覺的自然史或是選集,描述當事人的幻覺經驗,以及幻覺造成的衝擊,因為唯有透過第一人稱的敘述,才能讓人領會幻覺的力量。
本書某些篇章是按照醫學分類(像是失明、感覺剝奪、猝睡症等),其他篇章則是按照感官形式(像是幻聽、幻嗅等)。但是,這些分類裡頭有許多是重疊和相關的,而且類似的幻覺也可能出現在許多不同的情境下。因此,我希望本書能成為一個樣本,讓屬於人類基本情境之一的幻覺經驗,展現其寬廣與多變。
【前言】領會幻覺的力量
十六世紀初,第一次有人使用hallucination(幻覺)這個字時,代表的意思只是「神遊的心思」。直到一八三○年代,法國精神病學家艾斯基羅(Jean-Étienne Esquirol)才賦予此字現在的意思——在那之前,hallucination就只被當做是「幻影」。hallucination的精確定義還滿多變的,主要是因為不容易釐清幻覺、錯覺與幻象之間的界線。但是一般說來,hallucination定義為「對於不存在現實世界之事物的知覺」,也就是「看見或聽見不存在的事物」。1
就某個程度而言,知覺是可以分享的,比如你我都同意那兒有棵樹;但...
目錄
前 言 領會幻覺的力量 6
第一章 沉默的大眾:邦納症候群 13
第二章 囚徒的電影院:感覺剝奪 47
第三章 幾毫微克的酒味:幻嗅 59
第四章 幻聽:不等於精神分裂 69
第五章 帕金森氏症幻覺 93
第六章 變異的精神狀態:嗑藥 109
第七章 圖形:眼型偏頭痛 143
第八章 「神聖的」疾病:癲癇 155
第九章 一分為二:半邊幻覺 189
第十章 譫妄:怪異又執迷的幻覺 205
第十一章 在入睡的門檻上:入眠期幻覺 227
第十二章 猝睡症與老鬼婆 249
第十三章 心魔:深沉的創傷 261
第十四章 生魂:幻覺到自己 289
第十五章 幻肢、陰影以及感覺之鬼 309
感 謝 332
前 言 領會幻覺的力量 6
第一章 沉默的大眾:邦納症候群 13
第二章 囚徒的電影院:感覺剝奪 47
第三章 幾毫微克的酒味:幻嗅 59
第四章 幻聽:不等於精神分裂 69
第五章 帕金森氏症幻覺 93
第六章 變異的精神狀態:嗑藥 109
第七章 圖形:眼型偏頭痛 143
第八章 「神聖的」疾病:癲癇 155
第九章 一分為二:半邊幻覺 189
第十章 譫妄:怪異又執迷的幻覺 205
第十一章 在入睡的門檻上:入眠期幻覺 227
第十二章 猝睡症與老鬼婆 249
第十三章 心魔:深沉的創傷 261
第十四章 生魂:幻覺到自己 289
第十五章 幻肢、陰影以及感覺之鬼 309
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