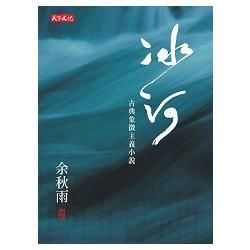只有余秋雨能夠超越余秋雨
華人圈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散文大師,
首部長篇小說
我的創作堅持一種自己確認的美學方式,那就是:
為生命哲學披上通俗情節的外衣;
為顛覆歷史設計貌似歷史的遊戲。
《冰河》的故事好看,情節生動,人物突出,性格鮮明;
但是我要讓所有的讀者明白,
故事只是「此岸」,對面有一個意義的「彼岸」,
那種意義深刻、宏大,直逼世界的悖論、生命的隱祕。
――余秋雨
這條河,餵養河岸多少古樸的人民,
這條河,承載多少書生文人的榮華大夢,
一個古老的愛情故事,
在河面上悄悄發生。
為了尋找二十年前赴京趕考就此音信全無的父親,妙齡女子女扮男裝獨自踏上旅途;孝順的船夫之子為了一圓老父的期待與夢想,決定上京參加科舉;年過六十的老丈,已落榜了十數次,決定再賭最後一次,再參加一回科舉。
三位主角相遇於冰河上的渡船中,冬日寒天,河面上無預警結了冰,整船人的生命陷入危機。這時,其中一人挺身而出,從此改變了彼此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