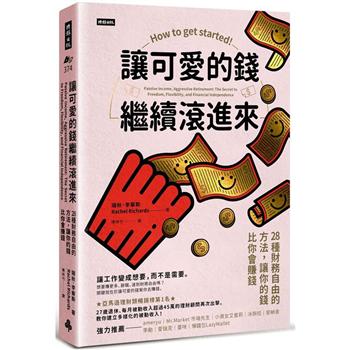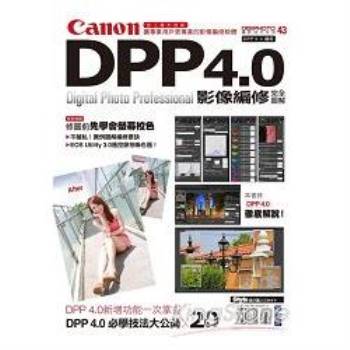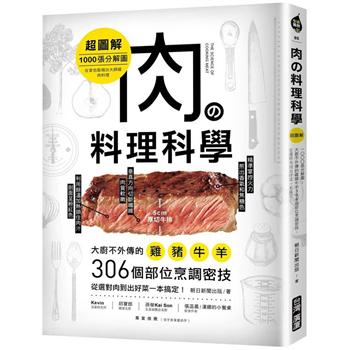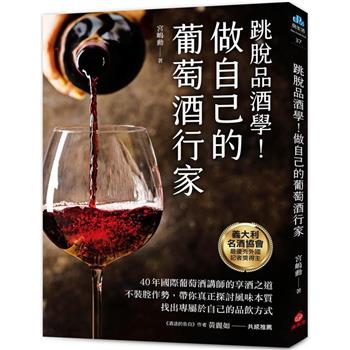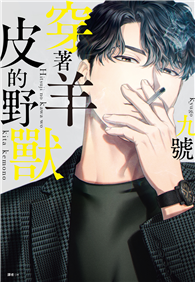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候鳥來的季節──電影小說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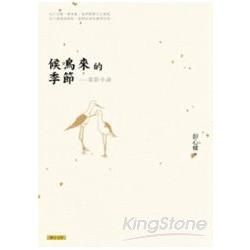 |
候鳥來的季節:電影小說 作者:彭心楺/著、蔡銀娟/原創劇本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9-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8 |
小說 |
$ 198 |
小說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0 |
小說 |
$ 22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飛得再遠,也會回去的地方,叫做家。』為了完整一個家庭,他們即將失去彼此。為了最終的和好,他們必須先練習仇恨。家庭總會傷人,親情卻將撫癒所有傷口。在候鳥來的季節裡,讓我們溫柔又體貼地,把讀這本小說當成藉口,好好哭一次,然後學會愛。你有多想家人,就有多想讀這本小說!候鳥移棲,是場冒險的旅程,沙塵逆襲,海上暴雨,只有通過考驗的候鳥,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愛,也是。兄弟應是天秤平衡的兩端,但當父親講出改變兩人命運的一席話,兩人注定一世尷尬矛盾;對家民、含櫻而言,醫院是羞辱的代名詞,哀忿裂傷,危顫的愛選擇只能出走;她有海慶,他念著幸梅,心有所屬千里跨洋聯姻,愈是傷不起,愈被現實狠狠掠獵。候鳥來的季節,也是這個家庭支離破碎之際,有些,來了又走,更有些,放不下心底的愛,就留了下來,再也不走了。
【作者簡介】
彭心楺
寫劇本,曾獲金鐘獎迷你劇集編劇獎。寫小說,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出過一本書,《嬰兒廢棄物》(寶瓶文化)。是個產量很少,生產力緩慢,卻活得很自在的人。E-mail:pengshinrou@hotmail.com 【劇本原創簡介】
蔡銀娟
臺大社工畢業,曾待過靈骨塔、美術館、製片公司等五花八門的機構,也做過馬戲團專案助理、社工員、中學教師、刊物編輯、配音員等千奇百怪的職務,似乎永遠都在不務正業。舉辦過數次個人畫展及亞太女畫家聯展,著有繪本《我的32個臉孔》、《夏綠蒂的愛情習題》。歷年來得過拍臺北劇本首獎、十大傑出女青年獎、臺北國際書展十大繪本、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臺北美展、打狗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等各種劇本、美術、文學等獎項。《候鳥來的季節》是她的原創劇本,也是她第一次執導電影長片。片中那些畫風奇特的油畫與母女圖,都是她自己的作品。這部電影描繪著家人之間的愛與犧牲,呈現了兄弟間那種說不出口的親情,劇情感人肺腑,不但獲得「優良劇本獎」的肯定,也入圍了「臺北電影節」最佳劇情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