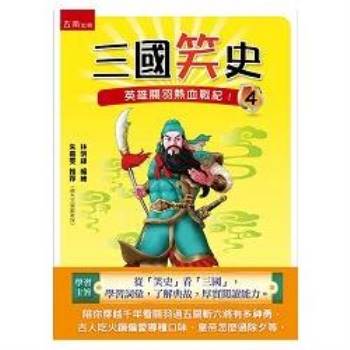浮雲般的青春都會過去,總有點寂寞留下來。
六則小清新的故事,直點人心的真實。
這就是我們缺了一點什麼卻無法拋棄的生活……
擁有的是物質,而不是精神;是時間,而不是歷史。
彈琴唱歌跳舞
她們在游輪上跳舞唱歌彈琴也說愛。那年閒來無事,與人議論叫做香港的城市,結果到了後來,她們自己站在這個城市裡,恍然又站在一片漂浮的陸地上,只是不再談是否快樂。
像長頸鹿一樣跳舞
天才少女小厥永遠在與跟她年齡不相稱的人對峙交戰。可是花了那麼多力氣,卻只是擦肩而過。她用那麼長的時間,不過只跳了一支舞,以為學會了沉默和優雅,但是都是有代價的。
聖吉尼斯.路易斯的中國公主
天堂之國聖吉尼斯.路易斯發放了幾十萬護照,卻只住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嘉嘉公主,她只想知道家鄉的少女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因為傳說那裡一直沉浸在擔心消失的恐懼之中。
龍井問茶之陽春白雪
不管是怎麼樣的感情,只要是真的都是好的,但是那些看得到的圓滿總是需要有人成全,於是有人翩然轉身,有人沉默,有人寂寞。
黃龍吐翠之烽火連綿
歷史裡從來沒有缺乏過烽火連綿,即便戰爭成全了一段感情,也只不過是僥倖。烽煙之下,失去的永遠無法被快樂填平,時間長了也只能淡淡的悵然。
平湖秋月之鏡中花
我那麼清楚地記得那年,那一年我們還都相信童話。曾經興高采烈傳頌的或者鄙視的到頭來不過是大家的想像而已,真實生活裡的不過是些平凡的人生,別的都是鏡中花。
作者簡介
聞人悅閱
紐約 Cooper Union 大學電機工程學士,紐約大學商學院金融碩士。寫作是童年時代的第一個夢想,在理想交互更替的成長歲月中保存了下來。二○○二年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出版有小說集《太平盛世》、《黃小艾》、《掘金紀》,童話《小中尉》,散文集《紐約本色》。
作品入選《21世紀中國最佳短篇小說2000-2011》,長篇小說《掘金紀》獲選2011年《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