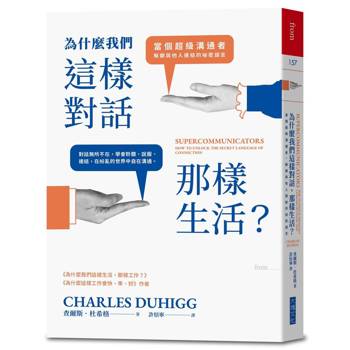在夜裡拎亮一盞燈,拯救那搖搖欲墜的垂危命運。從死亡,從背叛,把不斷沉下去的心靈搶救回來,回到寧靜安穩的文學閱讀。沸騰的審判噪音統治外面那世界時,能夠收留漂流的身軀,唯文學而已。現實是那樣窄仄擁擠,文學是如此開闊豐饒。浮游的命運終於停靠在文學疆界,接受文學力量的淘洗。那是一種淨化的儀式,擦拭傷痕累累的創口,洗滌風塵僕僕的衣袖。坐對情緒退潮的夜窗,一個全新的許諾適時降臨。——陳芳明
歷經半生的漂流苦痛,陳芳明教授透過挑燈夜讀和《新台灣文學史》的撰寫,展開漫長的精神之旅。「輯一」收錄的文字大多是針對新世代作者而寫的序與書評,對高翊峰、黃文鉅等文壇新星的作品給予獨樹一格的定位與闡釋;「輯二」呈現作者的閱讀經驗以及書寫台灣文學史時所構築的多元視野,見證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如何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繁花盛放季節,他在不同作者、文體、形式之間閱讀跋涉,開啟了我們對台灣文學的認識。藉由文學與閱讀,我們看到生命中看不見的世界,我們得以張開眼閱讀整個台灣社會。
作者簡介:
陳芳明
從事歷史研究,並致力於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陳芳明,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他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受委籌備、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以顯其治學和教學上的卓越成就。
陳芳明創作逾三十載,其編著的作品影響深遠,例如主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等;其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見證了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而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在在呈現了高度文學造詣。
在文學創作之餘,陳芳明的詩評集《詩和現實》等二冊,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建立新的研究典範。
二○一一年,陳芳明終於完成歷時十二載的《台灣新文學史》,為全世界的中文讀者打開新的台灣文學閱讀視野。
章節試閱
我們的張愛玲
我的題目是「我們的張愛玲」,剛好能夠和周英雄教授做一個對照;他講的是文本(text),我講的是歷史語境(context),也是歷史脈絡,指出她在台灣文學史過程中的一個定位。
張愛玲在台灣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她從來沒有住過台灣,也未寫過台灣,但是最熱烈擁抱她的竟是台灣。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張愛玲的一生是一座孤島的象徵。在戰爭時期她住在孤島上海,後來她寫《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是在孤島香港完成;再後來她到美國住在曼哈頓,曼哈頓同樣也是一個孤島。但是,張愛玲成名的地方卻又是在孤島台灣。
這樣的一位文學家跟台灣完全沒有關係,但爲什麽竟然被台灣接受?當然這是歷史的一個走向,不是依照她本來的預想。漂泊中的張愛玲從來沒有想到,天地那麼大,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能夠接納她的竟然是小小的台灣。作為一個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我會注意到張愛玲,並不是因為我現在是學者,而是始於一九六○年代還是學生的時期。早在那蒼白的年代,台灣已開始閱讀張愛玲,她已不屬於上海,當然張愛玲更不屬於中國,張愛玲是屬於中國以外的地區。因此請容許我這樣講,她是我們的張愛玲。
沒有台灣,大概就沒有後來文學史上的張愛玲。講這句話,有點傲慢,卻是一個殘酷的歷史事實。當然現在的上海或整個中國,又開始迎接張愛玲;但迎接她、接納她,並不是完整的張愛玲,而是經過篩選、剔除、壓縮的張愛玲。審美原則在中國是減法,在台灣則是加法。張愛玲在台灣受到不斷擴充、不斷填補,所以最完整的張愛玲,竟然是在台灣。
張愛玲能夠到達台灣,大概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九六○年代,這是一個很不愉快的記憶。一九六○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反共社會,當然反對的不只是大陸的共產黨,而是對稍具自由思想、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都是一併反對。可是在這樣天羅地網的檢查制度底下,張愛玲竟然能夠穿越縫隙到達台灣。當時接受她的是右派,也就是國民黨。當初是把《秧歌》和《赤地之戀》當做反共文學接受的。同樣也是由於這兩篇文學到達台灣,才使大家對張愛玲非常好奇。
在這階段,可能跟胡適有關係。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對張愛玲的提拔,開啟文學史上的奇異階段。有人說過,張愛玲對胡適有某種程度的戀父情結。胡適把她介紹到台灣之後,推波助瀾的是一九五八年夏濟安編的《文學雜誌》。他的弟弟夏志清在這本雜誌中介紹了張愛玲的小說。這是我們台灣學界第一次比較完整、比較深入理解張愛玲的文學精神是什麽。當時,我們看的時候其實沒什麼感覺。但是七○年代我投入研究時,再去看夏志清所寫的文章,才知道他所解釋的張愛玲,開啟了以後所有張學的一個入口。
當時夏志清的文章是〈談張愛玲的小說藝術〉,他提到重要的一點,如果人把身份、尊嚴、榮譽等等都拿掉的話,試問人還剩下什麼?張愛玲所寫的小說的人物正是如此不堪,如此難為。藉由這篇文字,他第一次把我們帶進張愛玲的世界。夏志清的功勞,不只是把張愛玲介紹到台灣,把張愛玲的文學提高到魯迅之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得到一種解讀的方式。《文學雜誌》是台灣自由主義的一個大門,它是跟自由創作有非常大的關係,因此接受它,其實就是從自由主義或反共立場接受她。這是最早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七○年之後,台灣因為釣魚島事件整個民族主義開始高漲,這時台灣有左派的民族主義,左派的民族主義是從非常民主的立場來評判張愛玲,當時整個中華民族主義在最高漲的時候,反日的時候,張愛玲就變成了犧牲品與取代品。當時有一個雜誌叫《文季》,編輯包括尉天驄、陳映真,還有從香港去的數學教授唐文標,他們開始大力批判張愛玲。
唐文標寫的第一本書《張愛玲雜碎》,使用的語氣非常貶抑,這本書收集強烈批評張愛玲小說的文字。其中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整個中國抗戰時期,張愛玲並沒有寫出民族苦難,反而在寫女性的幽暗世界。題目是借用張愛玲小說中的一句話:〈一步一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批判張愛玲沒有為中國帶來光明。可是效果適得其反,張愛玲越受批判,她的影響卻更加發揚光大。唐文標接下來又寫了一本書叫《張愛玲卷》,是張愛玲在美國加州大學的一些資料,唐文標把它收集起來在台灣出版。這本書收集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留下的的一些史料,她的一些文學活動。結果這本書在台灣很暢銷,唐文標又編了第三本書《張愛玲資料大全集》,把她的短論、訪談、散文、插畫與封面設計,都收集起來。遠在加州的張愛玲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生氣,她說:本來是自己的東西被別人搶去,人家反而當成他的著作,我還必須忍氣吞聲。所以她發表了一個聲明,對唐文標說,如果出版的話就要提告。當時為他出版的時報公司,聽說張愛玲要警告就很緊張,但所有書都印好了,幾千本,最後不敢發行。時報文化公司把印好的書都送去給唐文標,所以唐文標一夜之間就著作等身了。唐文標批判張愛玲,但我覺得他內心深處其實是喜愛張愛玲。男人的感情是很奇怪,往往以負面態度表達對女人的喜愛。在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張愛玲熱的加速升溫,唐文標的確有其一定的功勞。
唐文標當然是一個左派知識分子,左翼民族主義的狂熱批判反而發揚了張愛玲。可是在同一時期,台灣也出現了真正的張迷,一個是朱西甯,一個是王禎和。朱西甯當時是軍中作家,五○年代流亡到台灣時,在行囊背包裡,就帶了一本張愛玲的《傳奇》。這是一個很強烈的歷史暗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一位年輕軍人遷徙到台灣以後,後來居然變成了一個張愛玲的發揚者。
另外一個是王禎和。張愛玲唯一一次到台灣到訪問時,王禎和被安排去接待。王禎和把她帶到花蓮,事後他不只一次撰文提到張愛玲的花蓮之旅。到目前為止,跟張愛玲有過往來的,或書信往來的,幾乎都慢慢凋零,現在碩果僅存的見過她的人,在台灣還有陳若曦。但這樣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朱西甯與王禎和他也相繼去世,但他們留下的張愛玲記憶,已經生動地留在我們的文學史裡面。朱西甯與王禎和都受到張愛玲影響,兩位小說家既是現代主義者,又是鄉土小說家。前者寫中國鄉土,後者寫台灣鄉土;縱然美學表現不同,但對張的著迷卻同樣深刻。他們在一九六○年代就已經建立文壇地位,從而也相當有利於對張學的推波助瀾。
可是歷史往往不是按照我們主觀的意志在發展,一九七○年以後,台灣在國際地位漸形孤立,中華民族主義在島上也相對高漲起來。同一時期,台灣意識也跟著開始萌芽茁壯。具體而言,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以雙軌形式傳播於作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當時台灣文壇變成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統派與獨派都對現代主義文學進行批判,張愛玲也遭到池水之殃。即使受到強烈的批判,張愛玲在台灣的聲望仍然持續扶搖直上。鄉土文學臻於顛峰之際,張愛玲也不斷擴張她的影響流域。在一九七○年代,香港學者劉紹銘曾經形容台灣文壇是「非張,即鄉土」:說明當時文學版圖,如果不是張愛玲居於領導地位,就是鄉土文學非常風靡。
恰恰就在那段期間,一九七六年張愛玲的前夫胡蘭成來台灣的文化大學任教,竟然也開啟了另外一條有別於張愛玲的路線。朱西甯原是非常崇拜張愛玲,得知胡蘭成來到台灣,便有意去拜訪他。那年,胡蘭成在台灣出版了《山河歲月》,引起很大風波。書中提到抗戰時期,中國老百姓和日本人相處非常和諧,這句話激怒了台灣很多右派知識分子其中。其中以余光中的批判最為激烈,寫了一篇文章〈山河歲月話漁樵〉,批判胡蘭成敵我不分的立場。正是在這期間,朱西甯特意去陽明山去拜訪胡蘭成。他帶著妻子劉慕沙、女兒朱天文與朱天心去見他。歷史往往是在無意中發生,這次見面就要開啟台灣文壇的另一條路線。
當時二十歲的朱天文見到胡蘭成,似乎立刻受到點撥。因為當時胡蘭成送她一本書就是《今生今世》,朱天文拿回去看完後,立即產生「雲垂海立」的衝擊,若用胡蘭成的語言來形容,就是「全身起了大震動」。年紀輕輕的女孩讀了胡蘭成後,居然開始著迷胡蘭成,卻逐漸叛逃張愛玲。可以說,台灣張學慢慢出現了兩個方向:張迷或胡迷。從風格來看,張愛玲具有幽暗蒼涼的特質,胡蘭成則是充滿開朗陽光。年輕一代的朱天文,在父親朱西甯與胡蘭成的領導下,創辦了《三三集刊》,這個文學團體在一九七七年正式成立,培養了許多八○年代成名的作家。從這集團出身的作家,大多帶有胡腔胡調。我們必須承認,一九八○年後台灣重要年輕作家,有不少是從「三三集刊」出來。除了朱天文、朱天心之外,還有蕭麗紅、蔣曉雲、盧非易、丁亞明、鍾曉陽。到了八○年代,這些人不是獲得文學獎,就是在電影或劇作方面發揮他們的才氣。三三集刊,成了發揚胡蘭成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據點。
劉紹銘說「非張,即鄉土」的說法,近乎事實。但我所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稍加修正成為「非張胡,即鄉土」,庶幾近之。這樣說在於指出,七○年代台灣文壇的張迷、胡迷,足以與鄉土文學運動分庭抗禮,因此台灣文學就變得特別複雜了。張胡在台灣的角逐,大概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直到一九九九年,台灣的文建會舉辦一次「台灣經典三十」的活動,就是要選出三十本重要的文學經典,沒有想到張愛玲居然被選在裡面。這引發台灣本土文學陣營的憤怒,他們指控,張愛玲不是台灣作家,張愛玲沒有寫過台灣,爲什麽張愛玲可以進入台灣文學。
張愛玲受到越多反對,她的名字卻越傳播開來。張愛玲對台灣的影響已經形成,王德威教授曾經指出,台灣有所謂的「張腔作家」,指的是一批小說家具有張愛玲腔調。他說的是實情,從六○年代以後,張腔系譜蔚然成形。可是我把台灣大部分散文作品讀過後,不僅小說家有張腔,散文家也大量存在著張腔。影響勢力之大,簡直超乎想像。
最早的張腔散文,出於李藍的手筆,她寫過《中國的日夜》,書的命名絕對是從張愛玲而來。袁瓊瓊與蘇偉貞初期所寫的文字,幾乎可以聞出張愛玲的味道。另外一位散文高手張讓,既寫散文又寫小說,相當出色。張讓說過:讀張愛玲有毒,很難戒掉。這愈加證明她的魅力,像幽靈那樣,不斷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台灣作者身上。這縷幽魂也浮現在施叔青的小說,她的《香港三部曲》第一部《她名叫蝴蝶》,動筆之後,爲了避開張愛玲的影響,曾有一段時間刻意拒讀。可是,《她名叫蝴蝶》出版後我閱讀了,立即給她電話,請她翻開其中一頁,點出張愛玲句式。她自己嚇了一跳,原來那確實是張的語法。在電話裡她說,爲了不受張愛玲的影響,已經五年沒有閱讀張愛玲了。五年沒有讀張愛玲,卻無法抵擋幽靈再度歸來。每位作家都會有影響焦慮,希望能創造一家之言。但是拒絕受到影響,並非是避開閱讀相關作品,就可輕易達成。在施叔青身上,從未查覺張愛玲的影響是多麼深,已經進入血脈裡,以致沒有感覺。
遠在洛杉磯,還有一個散文家戴文采,極為著迷張愛玲。她特地遷居到張愛玲住宅的附近,貼近觀察張愛玲的動靜。張愛玲出門丟垃圾,她竟全部撿回去了,戀物癖戀到這個地步,也只有台灣的張腔作家做得出來。
種種事實顯示,張愛玲無形中在台灣開創出來的格局,無遠弗屆。爲什麽張愛玲可以進入台灣文學史,作為一個文學史家,絕對不可能忽視其中所暗示的搶大意義。所謂台灣文學,並非純粹只由島上作家來擘造。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向四面八方開放。這土地上的作家,長期以來已建立一個活潑的讀書市場,擁有龐大的消化能量。這個讀書市場,使許多作家承繼了批判性接受的本能。既受外來做家的影響,又能擷取智慧創出屬於自己的作品。這種開放式的閱讀傳統,是台灣文學史的重要特質,全然不容忽視。張愛玲是這傳統中的鮮明例證,她接受台灣讀者的大量閱讀與批判,終於形成一種看不見、卻深入骨髓的影響力量。這是台灣獨一無二的文學史現象,而張愛玲正是開啟這種奇怪歷史現象的其中之一。在她之前,還有魯迅的先例。我正在撰寫的《台灣魯迅學》,即將解釋這點。
許多人讀她,所以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她所酷嗜的那種「文字煉金術」,如影隨形跟著許多作家不斷冒出。「文字煉金術」的表演,從剛才周英雄教授所舉的那幾個段落就可發現。她的創作方式往往採取逆勢操作,這種「逆勢操作」的方式,與一般作家相比,總是反其道而行。譬如說,她見到胡蘭成,送他一張自己的相片,在背後題一行字:「看見了你,我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我滿心的歡喜,開出花來。」她不吝把自己矮化,自然就對方就會襯得很高了。張愛玲講的是反語,更加可以彰顯情感的張力。同樣的,我們紀念一位逝者,總會說永遠懷念你,永遠活在我心裡。而張愛玲在紀念她的祖父母時,卻說,:「他們靜靜的躺在我的血液裡,有一天我死時,他們還會再死一次。」這是很厲害的手法,完全擺脫世俗的陳腔濫調。
這就是張愛玲的筆法,不僅如此,還製造了許多術語或關鍵詞。明明是散文集,她偏偏要命名為《流言》,使平面文字產生流動感。比如她也創造「豔異」一詞,請問怎麼解釋?艷,很漂亮;異,不一樣。兩個單字連接起來,驟然生出豐富的歧義性。美得很奇怪,美得很特殊,美得很病態。簡而言之,那是一種絕美。著名散文家周芬伶的第一本作品,就命名為《絕美》,顯然是師承張愛玲。周芬伶後來有一本學術專書,集中研究張愛玲的藝術技巧,書名正是《艷異》。
張愛玲有一本《對照記》,裡面全部是相片。對照,就是容許讀者對著作者的照片嗎?對照,其實還暗示新舊對照,現代與傳統的對照,有一種強烈的時間感。不僅是記憶,也是一種歷史。所以《對照記》已不再只是停留在相片層面,它是一種時間與空間的相互參照與對比。她還有一本讀書筆記《張看》,暗藏太多的微言大義。張看,好像是心不在焉,又好像是不求甚解的閱讀,可又是張在閱讀。即使只書名,張愛玲都注入別出心裁的命名。
她對台灣的影響並不止於小說與散文,在批評實踐上,也同樣開出張學的氣象。今天的台灣文學批評家,不少人都與張愛玲有些淵源。早期研究者始於夏志清,稍後高全之、水晶、劉紹銘,當然也包括唐文標在內。現在會場在座的莊宜文教授,不只研究張愛玲,還把港台兩地有關張愛玲的研究全部收在一起。具體而言,張愛玲研究本身,也變成一種研究。這就是張愛玲所開發出來的不同水域,那種開散葉的局面,分佈越來越廣。
所以我們那個時代,也就是一九七○年代,大概是屬於第二代閱讀者,下一代有楊澤,再下一代有楊照。這種閱讀傳承也應該納入張學系譜。到了二十一世紀則更加豐富,王德威稱張愛玲是「祖師奶奶」,誠然所言不虛。這個祖師奶奶的生命一直是活潑蓬勃,並且她永遠以不同的形式回到我台灣這土地。總也不老,永遠不死。她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回來,以不同的聲音召喚。在座來自上海的陳子善教授,他的《張愛玲未完》給台灣提供很多新史料,最近又由皇冠出版社幫他出版《張愛玲的長短錄》。史料與史料的環環相扣,使張愛玲學的歷史縱深簡直看不見底。
很多新的史料,不能不要求台灣必須使用新的觀點、新的視點去解讀張愛玲。離奇的是,張愛玲的電影也不斷拍攝,台灣最近最知名的有二個,一個就是李安的《色戒》;另一個是「三三集刊」時期的丁亞明,拍了一部電影叫《她從海上來》。這部影集本來是以張愛玲為主軸,可是拍攝到最後,重心卻都放在胡蘭成。沒有張愛玲的幽靈,胡蘭成就沒有機會再次回到台灣。
我在寫《台灣新文學史》,並不迴避張愛玲。縱然遭到許多本土派的議論,我仍然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在我的文學史,有關張愛玲的段落非常長,主要在於指出,張愛玲的文學傳播,不只是帶來現代主義技巧,也帶來文字煉金術。她的小說,表現了時空交錯與幽暗人性。那種內心世界的挖掘,影響我們這一世代,也影響下一代人。
張愛玲很厲害的地方,便是既高雅又通俗。學院裡可能專注在她的藝術暗示,但一般社會大眾,卻沉迷在她通俗的愛情故事。記得有一次我回台中靜宜大學,在沙鹿小鎮下車。門口的收票員是一位女性,收票時認出我,她說:「你不是陳芳明嗎?」問她怎麼會認出我,她說:「你昨天去參加張愛玲學術討論會,我就在現場」。一個鄉下車站的收票員,因爲喜歡張愛玲,特地跑到台北去參加學術討論會。因此張愛玲對台灣的影響不只有學院,即使在鄉下,只要對文學有興趣,都會閱讀張愛玲。這讓我感覺非常震撼。所以她的幽靈不只存在於學院,也存在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心裡。她是幽靈,更是異形。因此,寫台灣文學史的人,能叛逃張愛玲嗎?對這樣一個龐大的身影,在歷史上創造那麼大的一個衝擊力,我們僅有的選擇,就是不要抗拒,馴服地接受她。
我們的張愛玲
我的題目是「我們的張愛玲」,剛好能夠和周英雄教授做一個對照;他講的是文本(text),我講的是歷史語境(context),也是歷史脈絡,指出她在台灣文學史過程中的一個定位。
張愛玲在台灣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她從來沒有住過台灣,也未寫過台灣,但是最熱烈擁抱她的竟是台灣。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張愛玲的一生是一座孤島的象徵。在戰爭時期她住在孤島上海,後來她寫《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是在孤島香港完成;再後來她到美國住在曼哈頓,曼哈頓同樣也是一個孤島。但是,張愛玲成名的地方卻又是在孤島台灣。
這樣的一位文...
作者序
餘生與未了——《星遲夜讀》序 陳芳明
《台灣新文學史》付梓出版後,閱讀的工作又重新展開。望向文壇,舉目盡是陌生的面孔。時代已經進入換季的時刻,世代也漸漸到了接班的階段。跨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文壇出現的作者,幾乎都是少壯行列。見證六、七年級的新星,次第浮現出來,內心自有難以言喻的喜悅。文學史的書寫,是一種向後看的篩選工作。現階段的文學閱讀,則是一種向前看的審美實踐。從一九八○年代至九○年代的作家,基本上已經完成台灣現代主義的接收工作。緊接著下一世代,又嘗試實驗全新的技藝。這種變化,似乎與戒嚴文化的終結有著相應的關係。
解嚴以後的台灣文學,出現前所未有的活潑狀態。其中最顯著的跡象,莫過於文字鍛鑄的鬆綁。現代主義運動的先驅者,曾經開發過大量的精煉語言。他們非常專注於濃縮的文字表現,企圖在最簡短的句式裡,發揮最大的想像。新世代作者則反其道而行,他們盡量揮霍文字,為的是描寫極為細微的事件。從駱以軍以降,許多年輕作家敢於耽溺在鬆散語言的運用,即使是最俚俗、最民間的說話方式,都容許放進詩或散文書寫,更別說小說故事的經營。
一個新的表演時代已然到來,只因為不再擔心政治權力的干涉,或介意傳統觀念的干擾。當台灣社會逐漸捲入全球化的浪潮,年輕作家也慢慢擺脫過去的思維上的束縛。受到翻譯文學的衝擊,從昆德拉、村上春樹到馬奎茲、卡爾維諾的美學洗禮,台灣少壯作家遣詞用字的技巧顯得更恣意而放膽。他們的藝術手法是思想解放後的美學,完全洗去過去壓抑年代的掙扎痕跡。面對正在崛起的作家行列,深深覺得台灣文學史的生命後勁十足。感受到文學力量的躍動,怒濤般擊打在心坎上,驅使我必須持續閱讀,注視他們將如何造成新的景觀。
至少收在這本書裡的文字,大多是針對新世代作者而寫。或者更確切而言,未來我所讀的文學書籍,大部分必然都是出於比我年輕的手。當我的前輩與朋輩逐漸減產或停筆之際,勢必要把眼光投向年少的後輩。文學生態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完成世代交替。與我二十年前出版的《危樓夜讀》相互參照,作者的年齡層次與審美原則,確實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感到慶幸的是,由於毫不懈怠的閱讀,終於還是能夠追上文學進步的節奏,並且也鮮明察覺新舊世代的差異。日月升降或潮汐漲退的自然規律,也相當生動地對應於近二十年的文壇風景。
這三年來,與年輕作家的互動日漸頻繁,尤以小說作者居多。他們在顧盼之間,儼然有一種自信。對於時代與家國,似乎不再抱持緊張情緒。當整個社會朝向開放方向篤定發展時,本土或非本土的意識型態,再也不是檢驗美學的標準。他們可能各自有其政黨取向,卻並不滲透於文字之間。所有的議題都是他們的關懷,從性別取向到公共事務,從私密幻想到家族細故,從歷史事件到個人記憶,無不可以進入詩、散文、小說。無論是時間跨度,或是空間廣度,遠遠超過上世紀的作者。年輕寫手所反映的想像,正好迎接解嚴以後的解構傾向。所謂解構,無非是偏離既存的主流價值,也偏離從前那種歧視、偏見、排斥、壓抑的中心位置。上世紀五、六○年代的黨國思想與七、八○年代的民族主義,都在進入九○年代後逐漸退潮。
關在研究室夜讀年輕作家的新語法、新句型時,當可發現新世代的作者並未與前行代發生斷裂。他們的審美態度也許有所差異,但確實是在前人的實驗與實踐的基礎上,持續開展大開大闔的格局。如果新世代可以定義為後現代,精神上其實是與稍早的現代主義運動接軌。沒有現代主義,就沒有後現代主義。兩個世代的不同美學,無疑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如果是在現實基礎上形塑虛構的想像;則後現代主義的變革,則是在虛構中延伸另一虛構。如果沒有先驅者的勇於虛構,大概就沒有後來者的嘗試。
正如我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序論所說,政治史在乎的是成敗興亡,文學史則強調繼承存續;前者計較權力輸贏,後者關心文化累積。在文學世界,完全不存在誰淘汰誰的問題。所有的美學實踐,都可成為每位創作者得借鑑,也可導出更精彩的藝術表現。因此,縱然已經完成一冊文學史,閱讀的工作仍無可懈怠。只有通過更豐富的涉獵,才能理解為什麼台灣文學的生命力是如此強悍。現在所做的閱讀,乃是有所為而為,主要是為了繼續增補未了的文學史工作。這可能是我餘生無可推卸的任務。
文學史撰寫之難,只有真正涉入之後,才能體會其中滋味。既然以意志與勇氣接下這份挑戰,便注定要承擔全部責任。如果發現缺憾、遺漏、錯誤、短少,都無須逃避過錯。寫史,從來都不是一蹴可及。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須時時自我要求,不斷回到這項書寫工程。正是在這要求下,每天還是耽溺於夜讀。全集式的閱讀,是過去十餘年養成的脾性,至今已經內化成為血脈的一部分。深夜裡月移星換的速度,我仍然可以感受。依舊守住深山裡的樓頭,星有多遲,閱讀就有多長。
——二○一三年二月十六日於加州聖荷西
餘生與未了——《星遲夜讀》序 陳芳明
《台灣新文學史》付梓出版後,閱讀的工作又重新展開。望向文壇,舉目盡是陌生的面孔。時代已經進入換季的時刻,世代也漸漸到了接班的階段。跨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文壇出現的作者,幾乎都是少壯行列。見證六、七年級的新星,次第浮現出來,內心自有難以言喻的喜悅。文學史的書寫,是一種向後看的篩選工作。現階段的文學閱讀,則是一種向前看的審美實踐。從一九八○年代至九○年代的作家,基本上已經完成台灣現代主義的接收工作。緊接著下一世代,又嘗試實驗全新的技藝。這種變化,似乎與...
目錄
餘生與未了——《星遲夜讀》序
輯一
暗夜裡的鄉土──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序
俯視黑暗的井底──重讀林佛兒《北回歸線》
後鄉土的考掘學
攜夢繼續航行──序林文義《邊境之書》
文學史的重訪與重塑
Love Is Four-Letter Word──《嬰兒宇宙》推薦序
文學史的逐夢與築夢
傲慢的食夢獸序陳永興《無悔之旅》
文舞雙全的林懷民讀《高處眼亮》
在關閉的地方重新開啟──序汪其楣《歸零與無限》
雪落韓半島──《無窮花開》序
盆地的巨河──序莊華堂《水鄉》
寂寞的時光與靈光
花謝落土又再回──《謝雪紅評傳》再版序
水淹鹿耳門
艾雯和戰後台灣散文長流──《艾雯全集》序
孤兒精神與林惺嶽美學
記憶是一面鏡象──讀郭松棻的遺稿〈驚婚〉
從孤島到孤島
毛澤東的牙齒
啟開黑暗的閘門
模糊世代的魔幻詩學──讀高翊峰的《烏鴉燒》
懺情與懺覺──閱讀黃文鉅《感情用事》書序
東亞現代與台灣書畫
坂本龍馬的造型與變形
權力與暴力──讀林宜澐《海嘯》
輯二
我的散文經驗
我們的張愛玲:她在台灣的不死與未了
台灣文學的現代與後現代
閱讀越美麗
台灣知識分子的宿命與宿願
瞭望百年來台灣的文學與藝術
我是如何到達台灣女性主義
十年之約
新台灣.新文學.新歷史
無止無息的造山運動──《台灣新文學史》餘話
散文可以虛構嗎?
餘生與未了——《星遲夜讀》序
輯一
暗夜裡的鄉土──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序
俯視黑暗的井底──重讀林佛兒《北回歸線》
後鄉土的考掘學
攜夢繼續航行──序林文義《邊境之書》
文學史的重訪與重塑
Love Is Four-Letter Word──《嬰兒宇宙》推薦序
文學史的逐夢與築夢
傲慢的食夢獸序陳永興《無悔之旅》
文舞雙全的林懷民讀《高處眼亮》
在關閉的地方重新開啟──序汪其楣《歸零與無限》
雪落韓半島──《無窮花開》序
盆地的巨河──序莊華堂《水鄉》
寂寞的時光與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