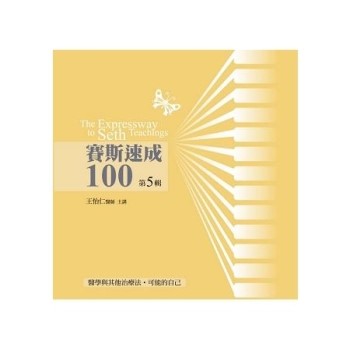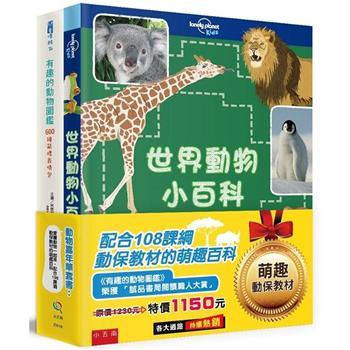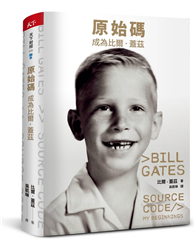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拜訪糖果阿姨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拜訪糖果阿姨 作者:伊格言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4-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9 |
小說 |
$ 221 |
小說 |
$ 246 |
小說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而大學第二年的國慶日,便是他第一次邀女孩來他的頂樓住處看煙火的時候了。
那也是他們的初夜。無數寂靜的花火在小窗外綻放閃燃。每次回想,他總覺得那年的記憶彷彿都沾染了那黑暗中嫣紅豔白的花色。年輕的星夜在他們頭頂旋轉燃燒;細語、呢喃與汗水微雨般落在水泥地上。
而那記憶中的光亮,竟像是要將他們的裸身全都曬傷了一般。
繼格局恢宏的宇宙滅絕史詩《噬夢人》,以及滿溢青春愛戀氣味的詩集《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之後,伊格言再變戲法,全新推出溫柔悲憫之作──小說集《拜訪糖果阿姨》。
八篇流暢易讀的小說,八個光澤璀璨的故事,《拜訪糖果阿姨》寫盡了生命中種種令人懷想、迷惘、無比眷戀的各式溫柔情感──比如模擬切.格瓦拉二十一世紀若仍在世的溫暖驚奇故事〈革命前夕〉,老阿嬤回憶日治時代青澀初戀時光的〈思慕微微〉,揉雜失散父女、舊愛重逢之忐忑心情的〈那看海的日子〉,以及浪漫、感傷,如青春般短暫絢麗的〈花火〉等等。讀著讀著,像是打翻了回憶的糖果罐,彷彿做了一場又一場深沉的夢……角色們那些酸甜不定的人生,彷彿都曾暫住在你心中最柔軟私密的角落;彷彿,那一切種種,你也都曾親身經歷過。
作者簡介
伊格言(Egoyan Zheng)
1977年生。台大心理系、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肄業,淡江中文碩士。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等,並入選《台灣成長小說選》、《三城記:台北卷》、《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等選集。
2003年出版首本小說《甕中人》,已成新世代經典,並獲德國萊比錫書展、法蘭克福書展選書。
2007年獲英仕曼文學獎(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入圍;並獲選台灣十大潛力人物。2008年獲歐康納國際小說獎(Frank O’Connor 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 Award)入圍。
2010年出版長篇後人類小說《噬夢人》,為該年度華文純文學小說賣座冠軍,入圍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並獲2010年聯合文學雜誌年度之書。2010、2011連續兩年攻佔博客來網路書店華文創作百大排行榜。
2011年出版詩集《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
曾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作家、國立成功大學駐校藝術家、元智大學駐校作家等。
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臉書:www.facebook.com/EgoyanZhe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