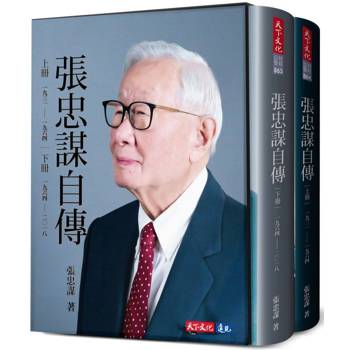別怕12年國教,害孩子讀不上好學校。
本書幫你和孩子勇敢邁向頂尖高中生涯!
有一點小孩,又有一點大人,這就是高中生!
光會念書還不夠,懂得為自己決定人生,才是最強的高中生!
這本書涵蓋了宗教、愛情、文學、政治、金錢、人格、大學選擇、交友、創造力、領袖觀、國際觀……等20項,是男女高中生最想知道的世界,也是家長、老師、輔導人員及一般社會大眾會有興趣的論述。夏烈以親切的文字娓娓道來,像是在和你面對面對話。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本和高中生對話的書。學生家長及老師更要讀此書,以了解及輔導你的孩子及學生。
夏烈是工程博士,又是外國文學及電影課程的教授,這本書卻是以社會及生活為主的基本書籍。他一針見血的論述令你在最短時間內看到極多極多的人生及生命。這本書將伴隨著你成長!
作者簡介:
夏烈(夏祖焯)
夏祖焯教授筆名夏烈,台北建中及台南成功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工程博士。曾在美任職橋梁工程師、大地工程專案經理多年。現任教於台南成功大學及新竹清華大學,教授近代歐美文學及日本文學,文學與電影等課程,為我國唯一工程博士出任文學教授之職。夏教授亦為建中文教基金會董事及建中校友會常務理事,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其長篇小說〈夏獵〉(九歌)榮獲民國八十三年「國家文藝獎」,2006年獲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科技與人文獎」。另外著有散文集《流光逝川》(爾雅),大學教科書《近代外國文學思潮》(聯合文學),中短篇小說及散文合集《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又名《白門再見》,九歌),以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城南少年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北中南各大學與高中校長、學生、校友聯合推薦
本校夏教授的這些議論文有相當大的啟發性,不但適合高中生,也適合大學生,甚至家長、老師閱讀。——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
夏教授經歷了理工領域的琢磨,並承襲了雙親的文風。本著作融合人文、科技與人生經驗,給現代徬徨的青年及家長們進一步思索的方向。——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
夏祖焯教授是一位兼具科技專業與人文素養的傑出學者,夏教授在本校期間,每學期課程皆為同學熱門首選,他的文章不同於一般老生常談,其思維觀點細膩,更有許多宏觀建言,對高中生、大學生、家長甚至於老師,皆有相當大的啟發,連我亦覺得獲益良多。——成功大學校長∕黃煌煇
跳脫外在環境的制約,勇於自我探索。把握自我實踐的機會,做最好的自己。這才是人生最高的價值。——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
夏祖焯先生出版了《建中生這樣想——給高中生的二十堂人生要課》一書,引領青年學子進行一場場思辨之旅,助其建立立身處世不可缺少的重要價值觀。從國際觀、宗教觀、金錢觀、愛情婚姻觀的辨析,到菁英教育、品格教育的省思,延伸至文學價值與生命意義的深究,在人格形成期的風雨雲霧中,對於這些人生課題有所定向,必是豐厚羽翼的重要滋養,相信這本書將能幫助每個徘徊於成長十字路口的孩子,翱翔向寬廣高遠的天空。——建國中學校長∕陳偉泓
夏教授一針見血、簡短有力的文章,令讀者很快吸收到許多知識及分析,啟發他們的思考。——北一女校長∕張碧娟
夏祖焯教授對任何事物總有精闢、獨到的見解,每每讀畢他的文章,都會啟發我更深入的思考。這本也不例外,其內容鏗鏘有力、助益良多,實為一本佳作!——建國中學學生∕廖軒晟
受感性支配太久,想給理性一點空間嗎?覺得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徬徨失措,就缺少一個適合自己的出路嗎?看完這本書,便知道下一步怎麼走!——蘭陽女中學生∕蔡佳柔
夏教授的創作文學總是有明晰的現實背景。這本書的循循善誘也是以理性知性為主,感性為輔。在流行「跟著感覺走」的今天,年輕人必能得益。——北一女校友、大專聯考狀元∕郭譽佩
建國中學對我來說是久遠的回憶了,但最讓我終身受用的是當時好幾場由學校特別邀請的演講。在那個年代,談思想的演講只開放給十幾個特別選出來的學生。夏教授這本書,遠超過當時我青澀年華所吸收的或現在市面比較膚淺的書籍,我相信會成為許多年輕人「想法」的啟蒙,值得終生咀嚼受用!——台大電機及建中校友、大專聯考狀元、有史以來聯考最高分紀錄保持者∕白培霖
以理性與幽默引導感性的能量,陪伴年輕的靈魂走過阡陌紛呈的歲月。——台中商專校友∕林和君
十八歲前我應該完成的事——閱讀本書,夏教授將以最貼近高中生的口吻,帶領你建立一個「認識自己」的多元化生活。——台南女中校友∕林亮宜
迷茫與無措,是高中以上、大學未滿最常遇到的問題。多樣的選擇是幸福也是負擔……也許文章不能給你明確快速通往成功人生的答案,卻能拓展你思考的方向,為你的未來提供值得參考的依據。——台南女中校友∕朱奕霖
讀一篇夏祖焯教授的文章,令人妙趣橫生。其深入淺出、風趣亦不失嚴謹的文筆,更可謂文情並茂、字字珠璣。每篇文章,都像是在和教授對話,在一段又一段的字裡行間中,潛藏著無限的智慧與省思。——安康高中校友∕賴英錡
坊間有很多寫給年輕人探究社會、思考人生的書,但夏教授的論點新穎且文字淺白生動,閱讀完書中的二十個主題,即猶如與夏教授面對面學習。——高雄新莊高中校友∕澎瑋琳
夏老師本書的分類觀點甚是有趣,有別於教科書的知識,貼近我們生活的常識更應了解,本書是值得買來細細品味的。——高雄楠梓高中校友∕蔡志賢
夏教授要教給讀者思考,從高中到大學,就是出了社會的人也很受用的。不管是在哪個年紀的人,都值得從書架上拿起書,花時間用心品嘗。——新竹女中校友∕邱睦容
名人推薦:北中南各大學與高中校長、學生、校友聯合推薦
本校夏教授的這些議論文有相當大的啟發性,不但適合高中生,也適合大學生,甚至家長、老師閱讀。——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
夏教授經歷了理工領域的琢磨,並承襲了雙親的文風。本著作融合人文、科技與人生經驗,給現代徬徨的青年及家長們進一步思索的方向。——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
夏祖焯教授是一位兼具科技專業與人文素養的傑出學者,夏教授在本校期間,每學期課程皆為同學熱門首選,他的文章不同於一般老生常談,其思維觀點細膩,更有許多宏觀建言,對高中生、大學...
作者序
豹 The Leopard
一隻年輕的金黃色豹子在荒原上奔跑、捕獵,身軀矯捷,耀眼陽光曬在牠滑亮帶黑斑的短毛上,閃閃發光。豹子跑累了、渴了,屈在一方小水潭前急促大聲喝水。水波平靜後,豹子赫然看見水中蒼老多毛的面頰,牠歪頭唔了一聲:
「啊,我怎麼會變老成這個樣子!」
有個聲音由遙遠的空中傳來:「你繼續跑,不停的奔跑,就會跑回年輕,像浮士德一樣……」
於是金豹轉身躍入空中,繼續奔跑,整片無際草原是牠寬闊的舞台世界。
這本書原是近年來寫給建中學生的專刊彙集。「聯合文學」與我商討,決定略為修改成寫給一般高中學生的書,寫給男生,也寫給女生,不再是建中。但後半部收錄了一些我曾發表過,與建中及隔壁國語實小有關的文章,以紀念那個一去不返的青少年歲月──我竟在台北南海路植物園對面這兩個學校度過了十二年時光,是整個的成長歷史。因為原來寫給建中,加上我的個性,再加上在美多年,受到美國主流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直截了當性格的影響,筆調免不了男性化。
任職美國工程界多年,我也曾是台灣高速公路局的工程顧問,最近十數年在台灣教授近代歐美文學及日本文學,文學與電影等課程,由工程轉為人文。但是個人最大的興趣不在理工,也不在人文,而是社會學科,這本書中的文章由而產生。文章寫給高中生,用詞用語盡量淺易,並且不在文中引用社會科學的學術文字或專有名詞。
小學及國中時寫「我的志願」,幾次都寫長大要作政治家,以後未能如願。
文章是個人主觀的看法,在建中出專刊時,每篇之後都有十篇左右的迴響文字,由馬英九總統到高中生都有。這些迴響作者不乏大牌人物(我在大學時外號就是「夏大牌」)、政治明星(甚至有的已被定刑關在獄中)、企業大亨、學界泰斗,或知名作家,因為篇幅不能全部收錄。實際上,有些高中生寫的迴響更有內容,更有見地。由這些迴響文字,我看到男生與女生的不同,年輕高中生與成年人的差異。很明顯,女生比男生要溫和及有人情味許多;成年人比年輕學子要理智、現實、以及「狠心」。年輕學生理想主義色彩重──走入社會,他們就知道不是這麼回事了;走上戰場,他們會看到人間痛苦、醜惡、敗德、凶殘的一面,那不是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中剛由高中畢業,相互提攜、生死與共的年輕兵士,而是海明威筆下「失落的一代」。書中某些文章,我寫出了真相,會令一些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學生失望及不悅,但是他們或她們將要面對,遲早的事。
我的母親林海音是出生在日本的台灣人,一半閩南,一半客家,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十年(民國四十二至五十二年)。我的父親夏承楹筆名何凡,是《聯合報》專欄「玻璃墊上」作者,也曾任《國語日報》社長及發行人近二十年(民國六十一年至八十年),他是京滬一帶的江蘇人。我出生在北京,長在台北,大學念台南成功大學,又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念碩士、密西根州念博士及美國各地工作數十年,家庭及學校背景算是比較多元。這些複雜的背景開展眼界,啟發思維,增長分析能力,所以書中一再鼓勵學生要多元化、多地域化、多接觸面、多好奇心。這四多不見得造益每個人,但絕對適用於大多數人。我們今日的學生逐漸在缺乏這四多,與家長不鼓勵有關。
前年我被母校成大延攬擔任教職,五年五百億「菁英條款」下被聘用,這條款極明顯是偏重理工醫。出面邀請的是當時的教務長湯銘哲醫生及校長賴明昭醫生。這兩位都是台南一中畢業入醫科,在美國再讀一博士學位後在醫學院任教,再轉任行政工作。我進入成大後發現湯銘哲教授偏向理想主義,人文氣息濃厚,重視他人的感覺。而我是工程出身,比較實際、客觀、重效率、簡單,不太考慮人的感覺,但是比他重物質。然而,我年輕時曾是強烈的理想主義及自由主義者,現在改變了,原因多重,不足一一道來。由此,我會想到,他為什麼延攬一個與他不同的人?交往兩年,從未問過他。以他的條件及資歷,應會被聘為一個醫科大學的校長(編按,湯銘哲明年將出任東海大學校長),他教育學生的方式可能與我大相逕異,哪種教育方式是對的?而台灣的教育應重理性,還是感性?高中與大學是否不同?與他交往聊天,深刻的是他曾說過:「……反正南部人就是逆來順受的。」我說:「我認為台灣人也都是逆來順受的。」然而,為什麼台灣人逆來順受?為什麼南部人更逆來順受?是否高中階段南北就有不同?高鐵一個多小時就由北到南,為何有此差異?
我教外國文學及電影方面的課程,朋友還是以工程界為多,其次是醫界。這和過去的學校及工作環境有關,也是家庭因素使然,因內人也是石化工程,女兒是免疫醫學,兒子是藝術家。實際上我的性格及為人較符合工程師「負責任,解決問題」的兩大特質。與人聊天,卻發現最喜歡與中文系出身的男士交談。在拙著《流光逝川》(爾雅出版)一書中有一篇學生對我的訪問稿,我也表達再考一次大學,會選擇中國文學系。因為出路(純物質)、虛榮、及六年建中的傳統,我選擇了工學院,如果當年不顧這些,或有高人指點而選擇了中文系,今日是否更快樂,更有成就,更超過我曾獲得的「國家文藝獎」及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的「科技與人文獎」的榮譽。如是,那又是什麼?
先慈出生日本大阪,第一語言是日語,後來才學習台語及國語。先外祖母住在家中時,與友人談話常是台語夾雜日本話。因此,我對日本的文化及習性逐漸了解,也常以此比對中國的文化習俗,這相當於民族性的比對。近百年我們曾兩度被日本嚴重侵略傷害,但又普遍欽羨日本在經濟、科技及人文方面的成就,因而形成國人仇日、媚日、抗日及哈日的複雜矛盾心態。我在文中則是強調「學習日本」的重要性。許多事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比較的,如此才能對鏡,才能客觀。實際上,我們也要學習韓國了。日韓的高中學生和我們有何不同,心態上是否有相當差異?這些高中生二十五年後成為社會中堅,領導他們的國家走進何處,又將走向何方?而中國大陸在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更是驚人。我的學生中有大陸及韓國來的交換生及外籍生,我看到他們的敬業及出眾。
日本曾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故而極為重視小學教育,因為小學生最容易被洗腦,此時要灌輸他們忠君愛國,為國犧牲性命及世界最優秀民族的優越感。到了國中孩子逐漸有判斷力,同時開始生理上的發育。高中階段則明辨是非的能力顯著增加,同學之間的談話開始有不少理性、分析歸納、及知識的共享,國中時期的叛逆色彩大幅淡化。本書中這些文章就是走這個方向,一共有二十篇,涵蓋面廣,帶給高中生對生命及生活的思考,也希望閱讀此書的家長及老師們與高中生作同樣的思考及討論。現在職場上需要的不僅是「I」型的專業人才,而是「T」型的對於其他領域都有相當知識的人,也就是「通才」,還有雙專業能力的「π」型人才。如此看來,中學時期就要開始培養課本外的知識。這本書寫給高中生,也寫給家長及老師,甚至大學生。
講到日本,成大現任校長黃煌煇博士曾問我為什麼不寫一篇有關武士道的文章給學生。黃校長初給我的印象是有些草莽豪氣,但他的工程論文曾六次獲獎,可能是獲學術獎最多的大學校長。武士道文化實際上源自中國文化,在日本本地化後又滲入神道及佛教的思想,統治日本長達近七百年的歷史。黃校長認為武士道並非只是打打殺殺,它的精神實質影響了近代日本優越的文官制度及民間企業文化,促進日本成為一個富強及高效率的國家。我同意黃煌煇的看法,也深深感覺應寫一篇重忠誠、名譽、禮儀、尚武、樸實及廉潔的武士道介紹。然而「聯合文學」初版付梓已箭在弦上,不得不放棄收錄。由於本書銷路不錯,再版時便加入此武士道之文。
我們學習日本容易,學習歐美只能學到表面,不可能徹底,還是洋體漢魂,因為西方重視個人及人道,東方強調群體而非個人,太不同了。日本自明治維新即強力學習西方,也還是名副其實的「和魂洋體」。由於浴血抗戰,中國大陸極度仇日,當然這也包含今日與強國日本在經濟及科技武器上作競爭,別苗頭。我數年前應北京大學之邀,作一場有關日本文學與電影文化的演講,數百人的小禮堂座無虛席,全場鴉雀無聲,講完如雷掌聲。中文系博士生林崢女同學彙集所有同學聽後感想文字給我,全是正面評價。可見全國第一的北京大學學生認清日本的重要,不是盲目反日。而日本的社會有開放性及收容性,不但不以接受外來文化為恥,反而對優良外來文化的吸收有感恩之心──我們是不是也應如此?
我在大學教書,又是建中的董事及校友會常務理事,所以更有資格,更有義務,更有興趣為高中生寫這本書。寫議論文章一針見血才會引起讀者興趣,躲躲藏藏、不痛不癢、四平八穩的文章讀來乏味、無趣。我年紀大了,衝勁減低,如果這些文字逐漸失去吸引力,希望後繼有人,為高中生寫出更有可讀性的文章。文章在精,不在多。寫多了,落得個文人名,出點小風頭,非我所願──我喜歡大的。
建中給了我六年教育,又邀我寫專刊有年,感激。(書後半段四篇原刊登於爾雅出版夏烈(我的筆名)所著《流光逝川》,九歌的《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城南少年游》三書,特此致謝)。此書半年初版是給高中生的十七堂課,再版我與企劃編輯張晶惠及叢書主編羅珊珊商議,再加三篇為二十堂課。如果銷售很好,還可再加重要的課。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女士與內人龔明祺在北一女同班,張女士念台大時我只見過她一面,還是晚上一個舞會,燈光昏暗,但聽說有許多台大同學讚美她,追求她,如今她竟為我出版兩本書(另一本是聯合文學的《近代外國文學思潮》),世事難料,這就是人生。
我為人理性,這篇開場白卻寫得感性,那可曾是年輕的我!
我們的高中生如何?我們國家的前途在哪裡?我們與大陸的關係又將如何發展?窗外時風時雨,時晴時晦,我的車在陽光與陰雨中穿梭。
豹 The Leopard
一隻年輕的金黃色豹子在荒原上奔跑、捕獵,身軀矯捷,耀眼陽光曬在牠滑亮帶黑斑的短毛上,閃閃發光。豹子跑累了、渴了,屈在一方小水潭前急促大聲喝水。水波平靜後,豹子赫然看見水中蒼老多毛的面頰,牠歪頭唔了一聲:
「啊,我怎麼會變老成這個樣子!」
有個聲音由遙遠的空中傳來:「你繼續跑,不停的奔跑,就會跑回年輕,像浮士德一樣……」
於是金豹轉身躍入空中,繼續奔跑,整片無際草原是牠寬闊的舞台世界。
這本書原是近年來寫給建中學生的專刊彙集。「聯合文學」與我商討,決定略為修改成...
目錄
自序:豹 Leopard
輯一:給高中生的二十堂人生要課
你告訴我高中生該去談戀愛嗎?
頂尖高中生要懂文學
你告訴我生命的真相是什麼?
你要不要從政?作政治家還是作政客
沒創造力爬得更快?
我們的民族性可愛嗎?
我們要如何培養國際觀——大陸與台灣
看重自己才是高人格
你要念理工醫還是人文社會科?
你可以是不信教的孤鷹
節儉未必是美德,先花了再說
你要走上勝利之路
作一流學生,也作一流領袖
你要又會讀書又會玩
選系不選校,離家念大學最好
記得,菁英不一定是功課好
向社會大學高材生多多學習
你是快樂還是不快樂的高中生?
你該去美國留學嗎?
武士道花落知多少
輯二:我的課餘好時光
我的高中生活
城南少年遊
白門再見
昨日
自序:豹 Leopard
輯一:給高中生的二十堂人生要課
你告訴我高中生該去談戀愛嗎?
頂尖高中生要懂文學
你告訴我生命的真相是什麼?
你要不要從政?作政治家還是作政客
沒創造力爬得更快?
我們的民族性可愛嗎?
我們要如何培養國際觀——大陸與台灣
看重自己才是高人格
你要念理工醫還是人文社會科?
你可以是不信教的孤鷹
節儉未必是美德,先花了再說
你要走上勝利之路
作一流學生,也作一流領袖
你要又會讀書又會玩
選系不選校,離家念大學最好
記得,菁英不一定是功課好
向社會大學高材生多多學習
你是快樂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