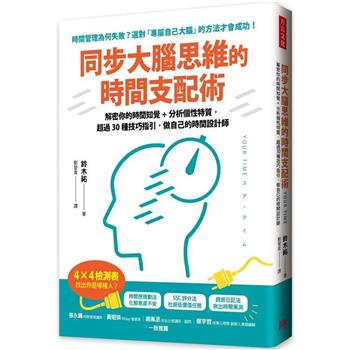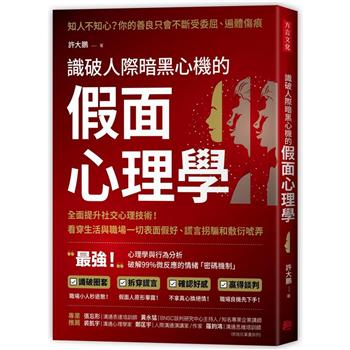微光亮起,每盞燈下每個人影都展演著自己的生活。第一盞是艾美麗,總在鐘響過後望見陽臺母親的背影回首卻變成好友母親的臉;第二盞田教授,面對自己的心理問題,先用醫學理論精準關照,以為自療;第三盞王惠婷,被裁員的出版社員工,家庭成員有各自的困境;第四盞詹醫師,年輕有過理想,之後卻被自己全盤推翻;第五盞幸子,當賣笑賣身繁華已過,她只想擁有自己的孩子……這些燈盞盞亮起,就像夜裡的星星,彼此各異卻又可連成一氣,他們家庭崩裂,生活丕變,有現實的問題,也有心理的障礙,而這些皆是城市生活裡的眾生相。
在城市裡,人人是在孤島中工作和生活,人人也彼此是孤島。許多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人聽聞和應對,連基本語言的能力都可能喪失,有精神官能症現象的人可能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這當是因為現今社會,特別是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以及和變化多端的人交往容易緊張,而也有因為堅持特別美學或思想和現在社會功利價值觀格格不入而患病。《城市微光》致力描寫台灣代表性住商城市的生活實境,包括中產階級和社會大眾的生態和感受,規模和深度以及一次描寫數十人的樣本是過去「台灣城市文學」前所少見的,也因此大部分的讀者都可能在這部小說中看到自己的影像。
作者簡介:
東年
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研究,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小說獎,曾任聯經出版公司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歷史月刊》總編輯、歷史智庫出版公司社長、桃園縣忠烈祠文館執行長;現任聯合文學社務顧問、台灣歷史文化生活影像再造協會理事長、新北市大河文化協會理事長。著有長篇小說《愛的饗宴》、《我是這麼說的—希達多的本事及原始教義》、《地藏菩薩本願寺》、《模範市民》、《再會福爾摩莎》、《初旅》(英文版Setting Out在美國印行)、《去年冬天》(改編同名電影)、《失蹤的太平洋三號》、《愚人國》、《城市微光》;小說集《大火》、《落雨的小鎮》、《東年作品集》(台灣作家全集系列)、散文集《給福爾摩莎寫信》、研究《桃園開拓軼史》、《桃園縣忠烈祠本事》、《道法自然》、《花神與花祭》、《神社的建築與思想》。
章節試閱
艾美麗站在二十一層高樓,從落地窗外望;藍天晴朗襯亮一朵朵積雲的邊絮。有些積雲結得密實,飄得很低,她想像自己是腳踏雲朵在深海幽靜裡漂浮。
「真是秋高氣爽。」遲疑幾次,她想:「去看新衣當是會比較開心。」
出門之前她給詹美鳳打電話取消門診。
早上十點環河東路上班潮已經消退許久,遠處轉角綠燈亮起才會跑出幾輛汽車和機車。
這裡正在拓寬道路,有些路段舊河堤已經拆除露出後面新造的防洪牆。她邊走邊瀏覽殘餘舊河堤上的爬藤,它們細緻攀爬灰暗長牆,而結有淺綠小球狀果實的薜荔在堤頂探出綠蔭;路旁大葉欖仁一株株筆直高出堤頂,橫張幾層枝葉上下搖晃更顯東南風氣息,她也能夠從裙裾上感受風的流動。
「真是秋天了。」她低聲自語。
離家走一小段路她看到路旁有成群幼童圍觀兩輛紅漆鮮亮的消防車,盛裝的消防隊員正在為他們指點消防車結構講解裝備。孩子們大都睜大眼睛聽得津津有味,總是會不專心的幾個孩子看到她走近,大聲喊:「艾老師好!」其他孩子跟著呼和。
突然聽到孩子們這樣接連放聲大喊她嚇了一跳,趕忙回應:「小朋友好。」這樣,她也想起自己在教室忍受孩童經常突發噪音可能會病情加劇,就又猶豫這幾天是否再和園長請辭。
她一邊回應孩童的招呼一邊向帶班教師點頭致意,說:「這就是戶外教學呵。」
「妳今天不是休假了?」潘雅慧說。
「我路過。」她說:「我要去蕭心怡那裡看衣服。」
「我很久沒去她那裡了,她生意有沒有好一點。」
「我也很久沒去。」
「下星期一妳可不可以再載我去買一些東西?」
這星期一他們一起去過中山路B&Q那棟大樓地下層的家樂福賣場,潘雅慧曾經猶豫是否要去二樓HOLA買枕頭和床單;她猜想潘雅慧是要買這些東西,就說:「沒問題,決定了呵。」
「昨天晚上決定了。」潘雅慧靦腆一笑,說:「先同居可以省一個人的房租,而且每天晚上可以那樣呵。」
艾美麗沒有男女互相滿足的經驗,但明白自己經常的慾望;她微笑起來表示贊同但是臉耳羞紅起來,就和潘雅慧告別而拐進一條長巷。
這裡除了一家陽春麵店和鄰長家戶戶門窗緊鎖,只在幾處門口有花壇植栽、懸吊盆栽、微風中圍牆鐵欄間探出的花枝招展,顯得生氣。麵攤熱鍋冒著煙霧老闆娘在後面將小菜分盤,從大片玻璃門望進鄰長家可以看到東南亞年輕女傭和輪椅上的婦人對坐發呆。巷子裡這些花木、蔬果飽受陽光雨潤每片葉子都綠意盎然,開出的花果也顯得飽滿和喜氣。幾個月前她因為幾次養不好室內植物,開始留意室外植物的可愛;她常駐足欣賞路過的花木,特別還去書店買了一套植物圖鑑仔細認識它們。她也觀賞一個人家圍牆探出的各色九重葛和粉紫色孤挺花,另一個人家門口長出野薑花和西印度群島櫻桃;這人家還用保麗龍箱種幾種蔬菜。有個人家在牆外沿路邊整齊擺了一盆盆花木,其中開出兩朵嫣紅的沙漠玫瑰;還有一個人家在遮雨棚簷下懸吊紅、橙、黃、紫、白五種百日草花。
巷子轉折處有雜貨店,早報陳列在門口鐵架上看起來只賣出幾份,燈光黯淡中老闆半躺在櫃台後的椅上觀看高懸在天花板下的電視。
這條曲折的巷子後段開有社區小廟、洗衣店和三明治早餐店,近巷口有音樂教室和美語教室。
斑馬線上的綠燈只為行人亮十六秒鐘,她匆匆橫過竹林路轉進中興街。
服飾店裡蕭心怡正就辦公桌吃便當;「妳吃過了嗎。」她說。
「還沒。」艾美麗不喜歡那種擠滿飯菜的便當盒,但是看到蒸餃不自覺嚥了口水。
「還剩三個,先給妳吃。」蕭心怡說;「我來打電話要他們再送二十個來。」
「我不餓。」她說:「我看了衣服還要去別的地方。」
昨天中午到現在她只喝過一杯咖啡,蕭心怡給她倒茶她就連喝兩杯。
「這普洱茶我老公前天從西雙板納帶回來。」蕭心怡說:「很好喝,我等等給妳包一點回去。」
「我可以買一點喝喝看。」
「那就先買半斤好了,我照成本給妳,覺得好喝再說,有些人不喜歡普洱茶說有臭腐味,其實它可以減肥、防止動脈硬化、降低血壓、抗衰老、抗癌還有很多好處,不過喝普洱茶要小心,潮濕或放太久就可能有黃鞠毒素,我老公帶回來的這普洱茶很新鮮很甘醇我一喝就上癮,現在大陸有很多黑心食品我還忍不住問他這普洱茶有沒有下毒,呵呵,最近新聞我有看到老鼠炸成乳鴿賣,要腿有腿要翅膀有翅膀,還有尾椎──屁股上那一點突起呵,竟然是用老鼠肚子有乳頭的部位做成,手工實在高明,啊,說到哪裡去了──衣服呵,我這次在大阪看到幾款不錯的,其實妳可以試試看,穿不同的衣服可能改變心情──不管怎樣我還是幫妳帶回一件毛衣,總之啊妳就是愛古典愛端莊不想和一般人從俗也不想和時髦流行,其實啊妳身材好穿怎樣穿什麼都好看。」蕭心怡說:「妳對男人沒興趣,這有點麻煩,我們女人就像花開花落,妳好像也不緊張呵。」
艾美麗每次來看衣服總會被蕭心怡這樣嘀咕;其實她有時候也會想試不習慣的形色,一猶豫就會放棄。她也不習慣在自家外任何地方脫衣服;她們身高體態相近,每次她拿蕭心怡推薦的衣服對鏡比照就決定取捨。這次她也只看一眼就接受一件無領套頭毛衣;這是帶有絨毛的粗線編織,胸前寬條相間織出淺灰和深灰藍色波紋,領下則編成一片片花瓣其間串有墨色繩索可以調整領口鬆緊並在胸前打蝴蝶結。她也從蕭心怡推薦的衣服中,留下一件混染各種明度和色調的紅色斑塊洋裝。
「終於可以接受彩色呵。」蕭心怡說:「這件我是看了自己喜歡,沒想到妳也愛。」
「這樣呵。」艾美麗說:「那妳要不要自己留下來?」
「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店裡,穿漂亮給誰看呵。」蕭心怡說。
「我剛遇到潘雅慧,她問妳生意有沒有好一點──她應該很快就會結婚了。」
「那好,我來注意一下有什麼適合她的衣服──我會給她打電話。」蕭心怡說:「我的生意喔,我先生去大陸和韓國找便宜的,我到日本找好的──大概還能維持啦,唉,我們小小一個永和市服裝店幾十家上百家。」
艾美麗再次上街,到處可見從辦公室或屋子鑽出來午餐的人群;她在狹窄的騎樓裡幾次遇到家庭主婦大包小包提著魚肉蔬果,一時興起就在幾步路後走進整條巷子的傳統市場;從巷底的永和路出去,她也可以繞路回家。這個市場由店攤夾道組成,蜿延三百多公尺;她許久沒來這市場,這次看了覺得魚、肉都比超市生鮮,熟食、小吃和糕點種類不少看起來也比較新鮮可口。她買了一盒現做的豆皮壽司和一條丹麥來的薄鹽鯖魚,還想買什麼卻想不起來。
回到家,她從冰箱拿出一條小黃瓜切成薄片再用蘋果醋調味;那條薄鹽鯖魚她用一把長刀把魚肉切下一塊,又切成細塊去炒飯。她想再煮一碗味噌湯配食豆皮壽司,才想起忘了買豆腐。
午睡醒來她躺著發呆,想起蕭心怡說她看不上大部分的男人覺得納悶;她從沒和任何人談男人,所以不會有自己看得上看不上男人的問題,如果有問題當是自己從來不知道男人是怎樣的東西也不喜歡男人。腦袋轉過這個念頭她就繼續躺著發呆,直到想要正式試穿新衣才能下床。
毛線絨毛看起來摸起來讓她覺得像是身上長毛,那件毛衣她穿起來不像在服飾店比試時喜愛;那件染有各種紅色斑塊的洋裝好像會讓她蒼白的面容洋溢生氣,她卻更加喜歡。
太陽已經越過高樓在落地窗外投出陰影,遠處散布在台北盆地的樓房叢聚仍然耀眼;新店溪在地面曲折成綠色綵帶非常亮麗。她曾經幾次和朋友說放晴時在高樓俯視蜿延的大河並不像在平地看那樣沉灰或泛黃,是近藍色或綠色;不住高樓的人都不信。有一次朋友和她說從101大樓可以看到海她一聽就相信,並且希望自己住得更高,視線能夠越過堤防、河邊綠地、菜園、大河、橋樑、和散佈各處的城鎮建築、學校、街道、高架公路、湖泊、直到盆地遙遠外緣的山脈和空缺之間,看到太平洋。
「我可以問問警衛或者請他們幫我注意一下如果頂樓有人要賣套房──散步喔,馬蒂。」她說,一邊從電視櫃抽屜拿出狗套繩;一隻白色馬爾吉斯鑽出陽台對她搖頭擺尾。這小狗原是潘雅慧從寵物店買來,幾個月前她去歐洲玩把牠在這裡寄放,說這樣狗可以和艾美麗作伴;有空蹓一下狗艾美麗也能夠多加一點運動。後來潘雅慧專心在男友身上,嫌這狗礙手礙腳就常扔在這裡。艾美麗對這隻狗的去留沒什麼特別想法,但是買了一間小木屋擺在陽台,又找工匠在落地窗紗門下做了小狗可以自己進出的活動門。
到了公園她解開套索任狗亂跑,自己坐在一排榕樹蔭下讀詩集。
她的注意力一會兒就經不起持續推敲模擬兩可的字句,站起來找狗;越過環狀跑道裡面剛經平整的大片草地,她終於看到牠在運動場那頭快步跑回來。她以為牠是遠遠看到她就回頭跑覺得很窩心,隨即看到有一個男人拿著球拍隨後跟來,她就猜想牠一定咬了人家的球或什麼東西。
再一會兒,她看清楚那位先生竟然是她父母的醫生朋友。「對不起喔,詹伯伯。」她說。
「啊,啊,是美麗呵,哇,很高興在這裡看到妳──美鳳說不久前妳有去看她,這樣很好,妳一定要常常去看她。」他說:「呵,我不知道這裡的網球練習場不見了。」
經他這麼說她才發現運動場靠堤防那邊圍了鐵板牆,公園角落那個網球練習場不見了。
醫生夫婦和她父母以前常在那裡一起打牆壁賽球,她自己也曾經幾次在那裡練習擊球;現在那些人只剩下醫生、他女兒和自己;這樣想,她覺得悲哀也就對這個老醫生覺得親切。
她從馬蒂嘴上取下網球,拿起手絹要把它擦乾淨。
「沒關係沒關係,就給牠玩吧,不要把手帕弄髒。」他在椅子旁放下球拍和背袋,拿出一條毛巾擦拭頸項的汗水也把臉色擦得通紅。「妳也愛讀詩呵,像妳母親。」
「我讀詩因為偷懶,字比較少呵,尤其英文詩常常一個字幾種意思也有猜謎的樂趣。」
「這樣喔──文學我一竅不通,英文還可以。」他說:「也許妳可以講一首讓我聽聽看。」
艾美麗從一處摺角打開詩集交給他。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他唸了標題後安靜的把詩看了一遍,說:「好,請說。」
「我就大概說呵──」艾美麗紅起臉說:「三月初春的時候,春光在草地上徘徊,好像在和人對話,也讓人看到草地那一頭遠處斜坡上最遠處的樹──後來──後來──呃,春天不告而別──忽然消失,她走了而我們留下來──」
「It passes and we stay,嗯,這句有意思──讓我覺得生命有點無辜。」他說:「那──那最遠的那棵樹是怎樣,看起來是很孤獨還是很漂亮怎樣的呵。」
「那棵樹──啊,我以前想過幾次,今天──今天這時候我忽然想到,可能像是十字架那樣有神或者神祕的什麼,就是春天來去的地方。」
「這樣喔──哇,能夠這樣想像這樣體會我就不行,我實在太俗氣了呵。」他望著草地遠方靜默了片刻,說:「下次看到美鳳妳可以和她說這首詩──你們家那些書都還在吧?」
「都留著啊,我上次整理只有很多我父親的雜誌堆放久了內頁都黏住,我就全部送給檢廢紙的,裝滿一輛三輪車。」她說。
「呵,那是小發財了。」他說:「妳──妳就大美鳳幾箇月,妳們兩個條件都很好,是不是這樣所以眼光太高,我看我來找兩個學生讓妳們認識認識。」
「呵,不急。」她說:「我覺得一個人生活很輕鬆──」
「一年一年時間過得很快喔──」他說:「還在托兒所教課嗎?」
「只是臨時去幫忙,去教音樂課。」
「我忘了是妳母親的同學還是朋友──那個所長。」
「我母親高中同學。」
「我和她也認識。」他說:「她三個孫子都是我接生的──對了,想說妳在這裡讀詩實在很好,可是下午妳最好不要一個人來公園,現在的社會有點不一樣,早上還好,早上這裡會有好幾個地方有各種健身團體活動,有臨時市場、跳蚤市場也有人在橋下下棋、打羽毛球、乒乓球、跳舞,下午雖然那些下棋的人大多還在,可是我看很多是賭博的,假日我想就沒問題,假日這裡會有很多人──當然我也有可能過慮了,畢竟我們永和是一個水準很高的城市。」
「我是第一次自己來公園讓小狗跑一跑,以後我如果來就上午來好了。」
「或者我們再來以前那樣有時打打網球,我來問問美鳳──」他說:「呵,我沒頭沒腦忙了一輩子,錢是賺很多很多,吃喝很多很多──生活──卻好像沒什麼生活呵──我應該趕快來退休,閒閒沒事或者找幾個人做一點什麼真正有意義和有趣的事。」
*
田教授離開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的時候夜空剛破曉;這時候,從車窗他可以看到陽光照在家門和一些探出圍牆的花木。他趕緊和司機把沒談完的話題結束,才下車立刻懊惱從機場到現在自己應司機談論政治一路喋喋不休,也就希望能夠再解釋自己對公共領域比較苛求以免司機以為他無所不罵是神經病。
他用兩支鑰匙打開門上幾道鎖,第三支鑰匙還沒用門就開了──他想起樓上有個劉小姐受他太太拜託,這陣子會來家裡走動;客廳、廚房和浴室或因此看起來也經特別整理和清潔。
他帶有二十八吋、十九吋旅行箱,大皮箱裝自己衣物和新買書,兩個小皮箱裝加拿大煙燻鮭魚、楓糖漿、楓葉茶、蜂膠、魚油、蘋果酒和各種禮物。從溫哥華飛機飛了近十六小時,但是接近台灣之前的夜裡他睡過一陣子,剛回國他所有的感覺也都清新而亢奮;他立刻換了休閒服,把這些東西逐一放在應在的地方。冰箱看起來也是經過整理和清潔──清空的,只放兩瓶罐裝水、一盒新鮮雞蛋、幾包泡麵、一個白菜,他一看覺得飢渴立刻打開瓦斯爐煮麵。
再沒事了,他一邊喝咖啡一邊推算溫哥華清晨兩點二十分起飛的班機如何在台灣時間早上五點四十分抵達;他知道其間需要加減時差卻總是換算不清楚,就懊惱自己觸及動態事物會顯得笨拙。在他恍惚中門鈴響第二次他才意識到可能是劉小姐來探看急忙去開門,只見門前馬路車陣滾動;他懊惱自己應該先拿起對講機或直接按下院門的遙控開關,卻也懷疑自己聽到門鈴聲只是錯覺。這樣思辨讓他開始焦慮,意識到這樣的焦慮讓他更加焦慮。
當他正在專注自己這樣的意識,又聽到公寓大門那方向有人喊他。
「喔喔,劉小姐。」他對她點頭說:「對不起,我剛剛來不及開門。」
「我想也是,所以又回頭來看。」她說:「教授早餐吃過了嗎?」
「吃了吃了,是妳在冰箱裡放泡麵呵。」
「是啊,田太太email說教授今早會回來,我昨天特地把冰箱洗乾淨地板也都擦洗過。」
「實在感謝──妳太熱心了,妳實在沒必要做那樣勞累的事。」他說:「內人交代三萬塊錢,要謝謝妳這半年幫我們看家照顧花木,啊,沒有妳照顧的話所有的花木一定早就都死光了。」
「那太見外,我和教授太太像姐妹一樣。」她紅起臉說:「也常受你們照顧。」
「還給妳帶了一點加拿大特產,妳要進來坐一下或者我給妳送上樓?」
「太客氣了,留著送親友好了,我正要去趕捷運上班。」她點頭致意就轉身離去。
望著她瘦削的背影,他想起自己從沒記住太太這些友人是什麼背景、身分,但是記得有一些不幸的事似乎和這人家有關;這背影──他同時意識到自己為這印象焦慮,是因為覺得自己現在是同樣孤獨。
孤獨一人在家是他生活中再一次顯著的變動,上次變動是他前年離開學校提早退休;因此,他也想起當時從研究室搬回家的五、六十箱書到現在都還沒整理。他幾乎把這件事忘了,他一直沒整理因為想先淘汰家裡藏書。兩個兒子都離開台灣沒想回來他們的書當然都可以拋棄,那是一些兒童故事、漫畫、平面或立體圖畫書,青少年勵志、科學普通讀物、人文通識、大學系所兩階段各種化學、物理、電子、電腦資訊、石油科技等等理工科教科書、洋文書。妻子有些股票投資技術分析教本,她在年輕時買過許多現在都是高價值的權值股像台積電、台塑集團這類企業股票,現在是相當程度的富婆。他不記得她看過什麼書,她大部分時間在聊電話看電視,要不就是和幾個暱友到處遊玩。她曾經說年老時一定不幫兒子帶孫子,現在畢竟還是被兒子拐去加拿大做祖母;行前還興致勃勃買了幾本養育嬰幼兒的Know How。家裡書他的最多,有幾萬本各種人文、社會科學書。他隨時都會買書,任何新出版只要有一點新見解他就會忍不住掏腰包一袋袋買;儘管好多書,除非需用,都是買時大約翻閱後就沒再看或者只再讀幾頁。現在網路知識傳播如此發達,也是他可以丟掉很多書的理由。
他畢竟捨不得丟掉任何一本他自己或妻兒的書──只要想到選書扔掉他就會焦慮,他曾經幾次從書架搬下書,最後又從地板上撿起來逐一歸放原位;這樣狐疑和猶豫的時候都會讓他焦慮得頭發暈。那些被他選出來認為可以扔掉的書,家裡確實不會有人再讀;這些書被他重新放回書架,因為他認為扔了可惜,也認為它們是這個家的一部份歷史而具有意義。家庭製造的垃圾怎麼會具有意義──日常廚餘和各種廢物就像每天馬桶沖失的東西當然應該拋棄,沒人再會讀的書籍對他來說卻還是有點不同。
習慣這樣鑽牛角尖想身邊任何事物的意義,也是他經常焦慮的原因。他是個廣泛性焦慮病患,正是這樣的病徵他提早退休;他是否確實是個廣泛性焦慮病患也有醫生懷疑。這種病症的定義,比較寬鬆的醫生以至少一個月裡持續發生四種現象中至少三種來認定;這四種症狀是:
煩躁不安、肌肉痠痛這樣的運動性緊張/
冒汗、昏眩、心跳加速這樣的自主性神經系統過度活動/
焦慮、擔憂、害怕這樣的憂慮性期待/
注意力集中困難、易怒這樣的警戒與審視。
但是有相當比例患者是因為憂慮生活瑣事、工作表現或者經濟情況,而不是情緒作用發生焦慮和緊張。所以比較嚴謹的認定──那是他在加拿大就近去舊金山看行醫的同學,她給他看的診斷性標準,用表格說明至少在六個月中大多數日子裡對許多事件或像是在工作、教書中產生:
過度焦慮、憂慮這樣的憂慮性期待/
覺得要控制這樣的憂慮有困難/
焦慮、憂慮、容易疲倦或激動緊張或煩躁不安或注意力集中困難或腦袋常一片空白、易怒、
肌肉緊繃、有安穩睡眠或睡眠之後還是沒精神以及難以入睡這樣的睡眠障礙等,這六個症狀
其中三個或更多有關聯/
焦慮、憂慮或生理症狀引起痛苦、傷害社會或職業以及其他重要領域的功能/
障礙不是藥物直接造成生理效應或醫療情境,也不包括在情感性疾患、精神病性疾患或普遍
發展性疾患發生的期間/
焦慮和憂慮的臨床關注焦點不含人格疾患和智能不足的憂鬱、焦慮、雙極性疾病或躁鬱症、
過動症、與精神分裂等第一軸臨床疾患例如恐慌、社交恐懼、強迫性、離家背井或親人的分
離焦慮疾患、擔心變胖而厭食、身體性多種生理不適,或是有嚴重疾病以及不在發生創傷後
壓力疾患的期間內。
他能夠把這些原則和項目背起來,因為每當他感到焦慮就會對照表格做自我內省和檢查。他那次其實算不上就醫,只是那位同學基於友誼的諮商教導,要他學會對自己的焦慮意識──當它發生時對它加以管理。她深識他的知識背景和深度思惟的習慣,所以最後還和他說了像是禪語,說:「不必為這些焦慮或自他管理的成敗焦慮,因為最後能有死亡這樣完全有效的工具。」;她這樣說的時候臉上浮起微笑,他知道那一方面是安慰,一方面是警惕。
劉小姐打電話來邀請他去晚餐時他正睡得酣熟,電話響了好久他才想起自己已經回到台北而且睡了整個下午。
她推辭不成,接受了加拿大特產這樣的禮物,錢是一定不肯收。她給他的晚餐用一個白色長方形磁盤裝厚片烤牛小排、咖哩蝦仁豆腐和炒高麗菜。
「我只是煮飯時想到教授可能一時沒東西吃,多煮了,請不要客氣。」她說:「我自己都是這樣吃,這樣可以少洗餐具。」
他知道住樓上的人會有比較開闊的景觀可看,沒想到他們這棟公寓高樓層的人會有這樣好視景。餐桌──這小面積的仿明式長方木桌原來也許不是用餐的,緊貼著改裝過的大片窗沿,視覺越過馬路、防洪牆、大片河岸可以看到新店溪在月光下緩緩流動。
「這時候加拿大那裡是白天晚上?」
「卡爾加里啊──那裡這時天還亮,大約八點多才會天黑。」他想像家人這時候也許圍著大兒子家門前擺在草地和楓樹下的餐桌,也正在晚餐。「那地方在阿爾比省南部洛磯山脈山腳下,以前是牧場區後來發現石油、天然氣變成新興工業城,很多石油公司在那裡設有辦公室、總部,所以工程師很多,是加拿大工程師最多的地方──卡爾加里印地安語是清澈流動的水,現在也還好幾次被評為世界上最乾淨的城市,我大兒子喜愛那裡四季分明,特別是夏天短,他喜愛運動,他在台灣夏天常會發汗斑這類皮膚過敏的發癢。」
她送上水果和咖啡的時候,正好看到他把盤中殘餘飯粒集中用食指掃進湯匙一口吃了。他用餐巾紙擦了擦嘴唇再把食指擦乾淨,一邊說:「太好吃了,掃得一乾二淨。」
用筷子和湯匙收拾盤中殘餘飯粒需費多次工夫,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開始會無意中用食指配合湯匙做這件事。年輕時他晚上常在街上和文學院幾位教授聊天,那時他們熱衷譯介各種思潮。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位外文系教授用三根指頭把盤中殘餘弄成一撮抓起來就口;看到他注意自己這個動作那位教授表示洗乾淨的手指比筷子衛生,又說這是哲學系印度藉客座教授的看法。那位教授究竟沒解釋為什麼那樣做──是因為好玩或是喜歡看餐後的盤子乾淨。好久以後,那時候他已經懷疑自己可能患了焦慮;有一次,當他意識到──當他同時有知覺的看到自己也那樣用手指去整理食物,他是想而且想儘快把盤子弄乾淨。
調羹發出響聲,他看到劉小姐低頭在攪拌咖啡想起她剛才好像有問他要不要加糖,就假裝是在猶豫而說:「我就這麼喝好了。」除了低頭喝咖啡或著偏頭去看窗外風景她沒再說話,沉默中他覺得尷尬而有點坐立不安;假設自己兩三口把咖啡喝了,站起來道謝,並表示有點事要去處理,這樣告別會很自然。但是,在這樣沉默的寂寞中她側臉的影像非常吸引他;那是從淺鞍型肩膀委婉轉進頸項越過耳朵一邊折上側臉一邊直上整齊梳理出來髮根緣線所描繪的,當男人面對面緊抱女人讓她消魂失神她轉側顏面而顯現的,正是這片表情豐富的曲折。他問她這個晚上先生是不是在外面應酬,她淡淡的說她先生在大陸做生意不太回來;這讓他想起有一次太太幾位友人來家聊天,傳說有誰的先生在上海金屋藏嬌還生了一對子女。
「他想離婚──我沒表示意見,也許我是要這樣懸著來懲罰他。」
「喔。」他說:「那妳工作還愉快吧?」
「還可以。」她說:「我在監獄擔任諮商心理師,為受刑人做行為矯治和預防再犯。」
猶豫了一下,他說:「也許妳正好有治療焦慮症的經驗?」
「憂鬱、焦慮患者心理壓力的處理、精神病患的行為問題是醫院諮商心理師的專長,我唸研究所的時候在醫院實習過也考有證照,不過我後來沒在這領域發展。」她說。
教授這個話題畢竟讓她很感興趣,整個晚上她就侃侃談了焦慮和憂鬱的臨床心理以及許多罪犯和精神病患的心理。很久以前他就有創作者、精神病患、罪犯是同源的知識,經她相當專業的解析他在恍惚間忽然脫口說:「我自己這幾年好像常受焦慮折磨,但是也有醫生表示這需要進一步觀察,我的麻煩是──啊,就像我曾經和幾位從政同學去一家財團的招待所玩,那個晚上有個命理大師幫大家算命也表演催眠術,我是唯一沒被催眠入睡的──有些醫師為我的症狀感到困惑,他們認為按我自己的描述和他們的分析,我右側腦室、左顳葉、右被殼、海馬迴、杏仁核等等的大腦掃描應該會體積增大,這些醫師多是我的校友或是他們的朋友,都對我很感興趣常找我去參加飯局,有幾個還打算拿我做研究,呵,我倒是從他們那裡認識了許多精神醫學,他們之中只有極少數能夠有時認得我所談的心理經驗和知識,儘管如此,我再多談他們就會覺得困惑,最後他們都放棄了只建議我吃藥,我從來不吃藥因為我知道他們不會和病患明說吃藥可能鈍化大腦功能。」
他這麼一口氣的快速自白,讓她聽得目瞪口呆;這口唇微開的表情也讓他有點心神盪漾。緩了一口氣,他終於忍不住說:「我可以抽一根菸嗎?」
她點了頭,去拿來一個煙灰缸、一包ESSE薄菏涼菸;這一下子,他已經點過自己的長壽菸抽了兩三口。
「教授剛說的,我聽起來很有趣。」她說:「也許──如果教授願意我也想試一試,我不是說醫療那樣嚴謹,我沒那樣本事,我只是想那樣的模式和過程可以深度聊天,也可能會有效果呵。」
他跟著呵呵一笑,表示可以考慮;事實上他很高興她這樣想。每次有醫生或者學者和他談廣泛焦慮症──無論是經驗或知識都會讓他對自己有新的或更深刻認識。
他和她交換名片,請她先用電子信件大約說明要怎麼聊就和她道別了。
*
電腦螢幕右下角的電子鐘已近七點半,王惠婷想起盛夏此刻天色才會完全暗下;那一陣子她男友常愛把車開到郊山、湖畔、河邊等夜幕完全落下。「高樓會擋住夕陽,城裡就暗得早些。」她一邊喃喃自語,一邊將下班後新寫的企劃案在桌面儲存。關機前她打開信箱,沒看到什麼信件需要立即回覆,覺得有些失落和寂寞。以往下班前她愛抬頭去看不遠處掛在牆上的圓面鐘;現在因為不景氣公司嚴格執行節能,時鐘陷在黑暗中只能看到一點糢糊輪廓。
當她熄了自己的桌燈,辦公室的角落還有一盏桌燈亮著;最近美術編輯楊福奎常加班到半夜,這時他在辦公室外的梯口窗旁抽菸。
「要走了?」他說。
她和他微笑點頭。
她在電梯門口呆站片刻才發覺電梯在上面樓層停滯不動,說:「像是又有公司要搬走──你明天還是會來加班呵。」
「妳要來嗎?」
「要看醒來的時間和心情──」遲疑片刻她說:「我來好了。」
他沒再應聲,當電梯門打開她想和他說再見他已經離開了。
她走約十來分鐘去搭捷運,這時候捷運不像五點半前後第一波下班潮擁擠。
她家離捷運也是大約十分鐘步程,夏日走路會流汗雨天衣鞋同樣會打濕,所以捷運通車幾年她仍然愛騎機車上下班,直到機車幾次故障她不想再修理。她不愛捷運就像不愛公車,都是不想和人擠在一起,但是擠了一陣子捷運她認為搭車時間不長不短,很適合自己一筆筆加強日文能力。
每天睡前她在Youtube選聽日語歌謠,順手把讀者評論下載,經常她也會去NHK選看歷史文化節目,印下一些能夠增進自己詞彙和文法的短評;無論在捷運月台、車廂站著、坐著她就打開ipad讀這些評論、短文。她很高興網路也發展出如此便利的知識性的資訊傳播,雖然這也正是加速滅絕傳統出版業的一種主要因素。剛進出版公司工作她以日文背景擔任文學類編輯,後來因為公司幾次裁員特別是裁掉資深、高薪人員她很快就升任主編,工作內容先後擴及通俗文學兼及文史。這樣發展和她原來的志趣很接近,也讓她相當有成就感。
在台北車站轉車,她才踏出車廂就看到國中同學林錦郁走在前面。
前幾天她也曾經在永和頂溪站門口,偶遇林錦郁剛從中興街郵局前買了擺攤小販一袋檸檬;按林錦郁建議,她們就近在一家超商喝咖啡。坐在落地玻璃牆邊就狹宰的長條木桌喝咖啡,她覺得實在沒什麼生活情調;每次路過超商她看有人在裡面看報紙還能接受,若是喝咖啡、用餐、吃便當甚至於對著小鏡子化妝嘴臉、塗抹指甲則會覺得不可思議。
她在匆匆行進的人群中緊跟林錦郁步伐,終於在捷運離開月台前趕上同一節車廂。「妳今天這麼晚下班?」她說。
「哇哩王惠婷──又碰到了,我不是晚下班我是去榮總看人家生病,我一位同事實在倒楣還沒怎麼用就患子宮癌,哎哎哎,妳看我瘋瘋癲癲正經話說不好,明明是關心焦急卻說得像搞笑,今天是小週末噎,現在才下班也沒男人給妳約會給妳想怎樣啊?妳長得比我好看三倍以上噎。」
面前坐著的乘客有人似乎已經豎起耳朵,王惠婷覺得不自在,就錯開話題說:「捷運真的很方便,從台北車站到永和只三站。」
「只三站還是只經過三站,這我都沒注意,反正都是很快呵──我們等等要不要再去超商喝一下咖啡,我們乾脆在那裡吃便當好了。」林錦郁說:「我剛在醫院看人家吃便當覺得很好吃。」
「呵。」她說,一邊從口袋掏出ipad瀏覽上面的日文資料。
在超商吃便當王惠婷無論如何無法感覺自在,勉強點了一份關東煮。
「啊,這關東煮看起來也很好吃,等一下便當吃完我也──呵,我這樣愛吃很快就會變成豬頭。」林錦郁說:「妳相信嗎──我有沒有和妳說我養了一頭豬?」
「有啊,上次在這裡喝咖啡妳談到你家屋頂上的菜園,還有一隻迷你豬叫阿珠。」
「呵呵,阿珠真的很可愛──那天我們來我房間煮一鍋關東煮開同學會,在屋頂上烤肉唱KARAOK也很好玩。」林錦郁說:「對啊,你們家也常烤肉唱KARAOK一定知道啦。」
王惠婷因為身旁一位老先生在翻看女性服裝雜誌覺得侷促,再過去有學生一邊吃泡麵一邊翻看書架上取下的言情小說則讓她厭惡。「我實在不懂妳怎麼愛在這種地方吃東西喝咖啡。」她說。
「好玩啊便宜啊歇歇腳休息一下嘛,吃完喝完拍拍屁股走人很合乎現在的社會步調啊,呵呵,亂沒情調是真的。」林錦郁說:「「我剛很想在台北車站買鐵路便當,那種便當真的很好吃。」
「要是一塊排骨、一個滷蛋、一塊豆乾、有一片黃色蘿蔔乾那種便當才是正宗鐵路便當。」她說:「世事變化無常,只有那種鐵路便當是少數始終不變的,因為這樣才覺得好吃。」
「是喔,這世界上還有始終沒變的東西喔──」林錦郁繼續講些什麼,她則仔細瀏覽起街上的車輛和行人;再次這樣貼近觀看街景,那些襯著夜色在城市光影中流動的行人讓她有些異樣感受。她忽然想起學生時代林錦郁就是這樣愛鬧,是同學間的開心果。「妳實在也是一種鐵路便當那樣的東西。」她看著林錦郁津津有味咬一塊滷肉片,說:「善良的無知可以算是一種美德,擁有這種美德的人一定很幸福,呵,是不是這樣?」
「哇哩善良無知──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而我變成鐵路便當──呵呵,開同學會那天早上我一定會要我那個外勞開車先去買鐵路便當。」
「什麼外勞?」
「我男朋友啊,他啊我說東就東說西就西,像外勞那樣好用。」林錦郁說:「他很能搞──呵,一下子東一下子西也可以上上下下這樣亂搞,幾下子我就被他搞昏了。」
「喔,什麼時候發請帖?」
「我媽拿他八字去合好像不太合,我──暫時就這樣吧。」林錦郁說:「下次找一個比較不準的來合好了,或者合到了再帶我媽去合一次──」
在回家的路上她想起從前能和林錦郁這樣的同學揪城一團,一定是自己也擁有這樣開朗性格;現在,這種特質完全消失了。「簡直是混沌開竅的故事。」她自言自語說:「混沌開竅一定會是我這樣下場嗎?那故事實在只是一種後設的寓言吧?」林錦郁談起男友讓她羨慕也讓她想起還在加班的同事,就又自言自語說:「我對楊福奎──我想,他才來公司不久之後對我也是有點──當然是啦──無論如何,我們常一起加班也常一起在電腦螢幕前交換意見,我們比別的同事多有默契和共患難的感情。」
*
再十來分鐘市公所清潔車就會經過大馬路,阿敏婆已經騎三輪車回家;之前幾路小型清潔車進入附近幾個巷弄之前,那些路線她也都領先去過。三輪車的車台上有欄杆固定幾個塑膠箱雜亂堆了大包小包、廢紙、空瓶;她很高興今天有人家清出一個電磁爐、十幾個紅葡萄酒瓶和兩箱不知道什麼東西;她還沒翻看紙箱,因為那是她在路旁離開車子去巷弄裡探看時有人堆上去的。
她把三輪車騎進自家邊增建的邊間,從牆角的小冰箱取出一瓶白開水,坐在板凳休息;那支檢來的玻璃瓶有很長的瓶頸原來是伏特加酒瓶,那個人家拋棄的小冰箱他長女婿來換掉門上的橡皮條就不會漏氣。有些被拋棄的電器其實都只壞在一兩個不值錢的小零件──前年有個人家丟給她一組二十年前的SONY音響,她女婿只是把裡面一條脫落的排線接好,她就用來聽佛經、台灣歌謠CD、廣播,用到現在。
有這樣專才的女婿,每次檢到電器用品她都很興奮。
她正詫異是誰打開客廳的燈和電視或是自己出門時忘了關,聽到長孫女阿真隔著門喊:「阿嬤轉來咯?汝緊來喔我有買汝上愛呷的餅──鳳梨、綠豆沙、滷肉、紅豆兒四種喔。」
阿真在嘉義讀研究所很少回家,阿敏婆很高興自己最疼愛的這個孫女回來了,把瓶子放在地上就趕去客廳。
「我可幾分鐘兒即看了。」阿真正在看電視劇,說:「阿嬤汝手面洗洗我隨會去切餅奉汝呷。」
「沒打緊沒打緊,汝看汝的電視我身軀洗了即給妳切水果。」她說:「我上愛汝轉來呵。」
她洗完澡回到客廳,阿真已經把四張大圓餅切成小片整齊擺在兩個玻璃盒,另也切了木瓜、香蕉和甜柿。
她打開電視把遙控器遞給阿真,說「汝不愛可在看電視嘛?汝看啊我陪汝看啊。」
「我不是在看電視,我是在做研究。」阿真關了電視說:「我會記得阿嬤汝永過莫是定定在看八點的電視劇呵?汝感覺按怎呵?」
「電視劇喔──呵呵,彼電視劇攏真趣味也真實在。」她笑皺整張臉皮說:「好人壞人善良罪惡好命歹命有孝沒孝人在做天在看人生愛撲拼等等,這款的故事和道理攏真好,而若是用國語講即是──打發時間呵。」
阿真被阿嬤台語腔國語笑彎了腰,一會兒,又說:「而汝這麼有可在看八點的電視劇沒?」
「甚少啦。」她晃了一下頭說:「我七、八點攏要在外口沒閒,而我這麼目珠也加足花噎。」
阿真看看桌面,說:「汝一定是沒在戴我上遍帶汝去配的目鏡。」
「足不會慣習呢,戴得怪怪。」她說:「既然汝問我是在做研究,我給汝講我實在的感覺──電視在做彼好人啦孝子啦有情有義的人啦,在這麼的社會實在是愈來愈少,所以看起來也不使講是實在的,而這麼社會男女也沒電視故事彼純情彼老實──令老爸老母辛辛苦苦給汝飼屆這若兒粹款受屆這若兒高的教育,可艱苦幾年兒汝即會當去教冊還是呷頭路,以後清清白白嫁人,不好去奉壞人騙去呵。」
「呵呵,我即沒彼若兒戆呵──啊,阿嬤我備去看冊囉,我明兒日再可來合汝開講。」阿真說:「唉,汝若不在做回收我即會當請汝去呷牛排,汝足久沒呷牛排呵。」
「是啊,時間攏不即好。」她說:「而我這麼也不使呷牛排,我合人在學唸經,按那喔我後擺若死,佛祖才會率我去阿彌陀世界。」
「唉,阿嬤汝實在沒必要可在沒閒彼垃圾回收,我上遍合汝去銀行存款,看汝簿兒頂寫貳百九十外萬,這麼一定又可較贅囉──」
「沒啦,令老爸買新車──而令二叔也借去二十萬──」
「唉,阿嬤汝個己的錢要顧較著些,免管阮爸阮阿叔,伊們攏個己會賺錢囉。」阿真說:「阿嬤晚安。」
「晚安晚安。」說著,她在阿真口袋裡塞了五千元;阿真推辭不過就說:「謝謝阿嬤。」
她看孫女從梯間上樓,就收拾好茶几上的糕餅、水果。
她連打幾次呵欠,但是沒想睡;這是好久來第一次在家裡有人和她說這樣多話讓她很興奮。
在外面回收資源多少會有人招呼她,遇到以前鄰居他們也會閒聊幾句、相互噓寒;以前鄰居住在地面路過人家就看得到,現在大家讓地改建公寓大樓夾雜在大量外來人裡散居在空中各處,偶而才能在菜市場或路上碰見。所以,只要有人和她多談幾句她就會很興奮。
她曾經兩年因為肝病沒出外工作,肝病治好閒在家裡不久卻常失眠也覺得人生乏味;阿真的父親開計程車,有一天空車路過家門想去洗手正好看到她昏倒在地。醫生給她轉診而精神科醫師把她這些症狀加上倦怠看成憂鬱症,她明白自己經常很鬱卒但要接受自己罹患什麼憂鬱──她聽醫生告訴阿真的父親,家人應該怎樣支持憂鬱病人的感情,就知道這對她不會有用,而精神科看出來的病對她來說就是神經病──她非常害怕自己變成那樣被人家指點的痟人。後來她在自家旁邊的畸零三角地、路邊用保力龍箱種了幾種蔬果,覺得很有成就而恢復生活和工作活力。她常去市場檢菜葉和果皮回來發酵成有機肥料,又重回資源回收工作而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上個月長子換新車向她借五十萬,想到他是阿真父親而且還有兩個孩子在讀書家計很緊,她僅片刻遲疑就答應了。當是看了眼紅,二兒子不久之後也來說他家最近收支有一點打不平要借二十萬;她知道不借他連媳婦也會來鬧到她發瘋還擺不平。
除了阿真她和其他孫輩沒什麼交往,他們也大都忘了自己幼童時父母上班後阿嬤是怎樣照顧他們;不過,她知道他們和她疏遠主要還是國語說的代溝。她和兩個媳婦現在連點頭之交都算不上,想到媳婦她就恨自己兒子;他們不只會當著媳婦、孫輩面前否定她的看法,私下也會毫不留情面批評她。不過她多少還是相信長子是孝順的;她重複聽過幾次大約明白他壓抑她的意見,因為認為她性格剛烈在家人的關係或對她自己都是有害無益的。
今晚阿真問八點檔電視劇她隨意談自己感想,現在想起自己在家裡的遭遇不知不覺氣憤起來。這個家的由來是她讓出房地讓建商蓋公寓大樓,而建商除了幫她的老平房改建三層公寓又貼三十萬讓她能像樣養育四個兒女。最讓她感到不平的是每當她賭氣提起這樣的功績,兒子和媳婦就會頂嘴說她被建商騙了──正好證明她頭腦不清楚,要不然他們就會像很多賣地人家每天閒著只顧吃喝玩樂;只有一次,阿真當大家面前為她抱不平,說當年這裡還沒有大馬路房地當然不能比現在的價值。她不相信自己被騙了,那時候孩子小無法提供任何參考,她問過附近幾個鄰居還有一個在商場打滾的親戚,她們都說那樣商洽不算離譜;這親戚並且說明她必須考慮先生死後的家計和兒女的教育。無論如何,她能感覺累積多年現在自己身上有點閒錢,而比較任何她做過的工作這資源回收她覺得最有樂趣。
輾轉難眠她起來上洗手間,要去工作室把今天的收獲分類才想起有兩個紙箱不知是什麼內容;她一打開上面的紙箱就看到一台像是音響的東西。
晚上十點半她女婿還沒睡覺,聽說像是有很多玻璃管的音響上就表示可以馬上來看。
他從新店開車來大約需要二十分鐘,她就從冰箱拿出糕餅用塑膠袋裝了又到菜園採了高麗菜和苦瓜。
她長女婿一看那個用真空管組裝的音響趕忙插上電源,讚說:「這看起來真老古,實在是有名的德國貨,這款好物這麼沒了,若是整理會好我看值在兩萬。」
「若是這好,汝即卡緊搬去。」她笑縐了臉說:「今兒日還取得一台電磁爐。」
「汝真久沒去阮厝踢踏囉。」他搬起音響說。
「我攏沒閒在取好物呵。」她提著電池爐、高麗菜、苦瓜和糕餅跟著出門,說:「啊阮孫去台積電做工程師錢賺足蕞呵。」
「啊,彼款高科技工程師實在是賺艱苦錢,沒暝沒日。」
「少年郎有錢賺就好啦,工作若安定趕緊娶娶呵──」她說:「按若我捏瞇兒即做太祖嬤囉。」
艾美麗站在二十一層高樓,從落地窗外望;藍天晴朗襯亮一朵朵積雲的邊絮。有些積雲結得密實,飄得很低,她想像自己是腳踏雲朵在深海幽靜裡漂浮。
「真是秋高氣爽。」遲疑幾次,她想:「去看新衣當是會比較開心。」
出門之前她給詹美鳳打電話取消門診。
早上十點環河東路上班潮已經消退許久,遠處轉角綠燈亮起才會跑出幾輛汽車和機車。
這裡正在拓寬道路,有些路段舊河堤已經拆除露出後面新造的防洪牆。她邊走邊瀏覽殘餘舊河堤上的爬藤,它們細緻攀爬灰暗長牆,而結有淺綠小球狀果實的薜荔在堤頂探出綠蔭;路旁大葉欖仁一株株筆直高出堤...
作者序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自序
艾蜜莉(Emily Dickinson) 有關春天的詩寫有A Light exists in Spring,我這書初稿在前年冬末完成,那時候沒想到會把這首詩名作為這書自序的標題。艾蜜莉這首詩我最近幾年,常在農曆年前重讀一次,都能有新的感觸。前年冬天我無意中再讀一次竟然對詩中草地那一頭遠處斜坡上最遠處的樹( It shows the furthest tree upon the furthest slope )有更深感受,以為可以藉這種春天的亮光想像城市微光。
關於城市,在台灣我們至少可以想像每兩個人有一個人是在住商、住工的小城市或社區中生活,事實上可能更多到每三人有兩人的程度。在城市裡,人人是在孤島中工作和生活,人人也彼此是孤島。人流落在孤島上就會像狄福(Daniel Defoe) 《魯賓遜漂流記》筆下的魯賓遜,也必須為生命存活非常努力,雖然他沒有買房子和上班的問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人聽聞和應對連基本語言的能力都可能喪失;狄福寫的這個故事,出自一艘捕鯨船的蘇格蘭船員Alexander Selkirk被船長拋棄在南美洲太平洋荒島Más a Tierra四年的真實事,這個船員獲救時幾乎不會說話了。如果魯賓遜繼續留在島上就會還原成自然的動物而可能和以經驗獲得的人性衝突,最終也可能發生精神官能疾病。台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慢性精神病患,與前十年比較增逾一倍且有逐年增加趨勢。事實上,台灣有精神官能症現象的人可能高達百分之二十五;二千多萬人口中約有五百萬人曾受此困擾且明顯有逐漸增加趨勢。這當是因為現今社會,特別是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以及和變化多端的人交往容易緊張,而也有因為堅持特別美學或思想和現在社會功利價值觀格格不入而患病。
海明威《戰地鐘聲》原書名For Whom The Bell Tolls (鐘聲為誰作響),摘自約翰‧登恩No man is an island這首詩的結尾:也因此你不必打聽鐘聲為誰作響,它為你悲鳴(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這首詩說:沒有人能自行完全孤立成為一個島,因為每個人都融活在整體人類之中,任何人的死都是任何人的損失和減少。海明威因為動蕩時代、戰亂感受生命的脆弱、孤寂、徬徨、虛無和恐怖,而這個島和這樣的鐘聲是約翰‧登恩,身為詩人、教士,在一次病危康復後的冥想;在他《祈禱文集》(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沉思第十七:沒有人是一個島,他說:全部的人類是一部作品,一個人死了這書不會撕去一部分而是落實到更好的言語表現,每一個章節都是這樣,因此佈道鐘聲響的時候不只是要請來傳教師,也召喚大家集會…沒有人是個島…任何人的死讓我變小…不必打聽這鐘聲為誰作響,它為你悲鳴。這個概念,發展出他後來的詩以及佈道證詞,傳頌三、四百年。我以為在城市裡人人是孤島,這樣的概念,很有意義,所以藉以寫序。
前年冬天完成的這本小說,今年才出版,因為今年是我寫作四十年。我曾經想在這特別的一年,出版三本新寫小說,以彌平自己因為工作忙碌多年的荒廢,也作為自己寫作階段的一個里程。但是,我隨後只另寫了《愚人國》;無論如何,我很高興自己的再出發──這有點像在冬末風雨的城市微光中,看到春天亮麗的亮光在草地上徘徊,越過遠處的斜坡,回到極遠處的那棵樹。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自序
艾蜜莉(Emily Dickinson) 有關春天的詩寫有A Light exists in Spring,我這書初稿在前年冬末完成,那時候沒想到會把這首詩名作為這書自序的標題。艾蜜莉這首詩我最近幾年,常在農曆年前重讀一次,都能有新的感觸。前年冬天我無意中再讀一次竟然對詩中草地那一頭遠處斜坡上最遠處的樹( It shows the furthest tree upon the furthest slope )有更深感受,以為可以藉這種春天的亮光想像城市微光。
關於城市,在台灣我們至少可以想像每兩個人有一個人是在住商、住工的小城市或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