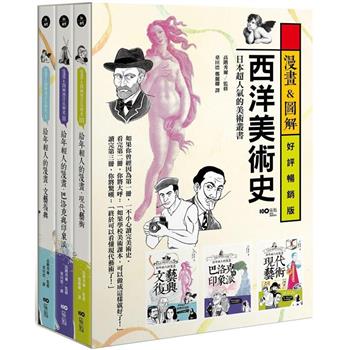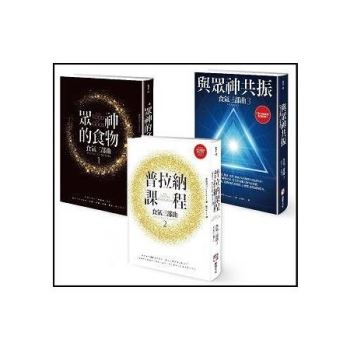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孤獨隱含一種巨大的力量,我無不探索文字更大的無限可能,所謂:人格即風格。
我手寫我心。文學本如是。
厭惡世俗,這是我的,傲慢以及堅執。」
在《歲時紀》,
春夏秋冬,象徵生生不息的循環。
林文義的創作也進入一個循環,來到「寫作起點」的初衷。
他寫散文、寫小說、寫詩,宛如四季邅遞,變幻深刻多彩的文字。
然而林文義永不重覆自己,
當《遺事八帖》拔高他散文的新境界,
他卻以極驚險之反差,回到這本《歲時紀》,
他透過手記體回到純淨的初衷。
對他而言「沒有理想國度,不會有烏托邦,
只有在文學書寫過程中,始能編織一方淨土。」
在《歲時紀》,
讀到他書房禁地之小物和意象。
讀到他反骨的品質。
讀到他行走在豁達與憂鬱間的思路。
讀到他活得像一行信手拈來的詩句。
這是《歲時紀》,
這是最純淨的文體,
這是未曾發現的林文義,
這是一本不小心被出版的私手記。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歲時紀的圖書 |
 |
歲時紀 作者:林文義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文學小說 |
電子書 |
$ 196 |
文學小說 |
$ 221 |
文學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現代散文 |
$ 24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文義
1953年生於台灣台北市。少時追隨小說、漫畫名家李費蒙(牛哥)先生習繪,早年曾出版漫畫集6冊,後專注於文學。曾任《自立副刊》主編、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時政評論員,現專事寫作。著有散文集:《歡愛》、《迷走尋路》、《邊境之書》等37冊。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革命家的夜間生活》、《妳的威尼斯》3冊。長篇小說集:《北風之南》、《藍眼睛》、《流旅》3冊。詩集:《旅人與戀人》、《顏色的抵抗》2冊。主編:《九十六年散文選》等書。2011年6月出版大散文《遺事八帖》,榮獲2012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
序
序
散文家的生命絮/續語 郭強生
該如何閱讀在實驗了以「大散文」述志立言的《遺事八帖》後,林文義最新的這本看似相對袖珍溫婉的《歲時紀》?
答案是,不要被這樣隨筆式的看似和藹可親騙去了。
有幸先睹為快,但掩卷時的我心情可一點也不輕鬆。雖題名《歲時紀》,以春夏秋冬分卷,但四季的輪迴牽動的依然是作家的長懷千歲之憂。在一句不經意的「生命過往,悔憾曾經」後,憶舊可能就驚動了天地之心,成為了「如果人云亦云,那麼你著力一生的文學有何意義?」這樣的自問。「點亮一桌燭光,就有美夢」的詩情,不時就有歷史的夢魘來侵踏,不得不「冷冷一笑。就是如此荒謬之世。誰是惡鬼?誰是霸王?」
心情的起伏跌宕,殘念的起落糾纏,因為不能割捨而最終成了如今的文字樣貌。
我會說,札記隨筆式的《歲時紀》儼然就像一部史詩電影完成後,又出現的一部幕後拍攝過程的紀錄片。詩人/散文家的生命絮/續語,如同自我的側拍,一格格盡是流離的剪影。
印象中文義過去的散文形式工整,文辭富麗多典,如攀峰,過了一山還有一山,峻險但又盪氣迴腸。此回,他相較之下揮灑得更寫意;呼風喚雨,用更直接的速寫,沒有構圖底稿,也不假召喚繆思女神的儀式,落筆成章。但生活情趣終究不是他的書寫重點,品茗訪友,鶼鰈情深,只是偶爾喘口氣的逗點。作者雖在《遺事八帖》後又完成了詩集《顏色的抵抗》,但太多的人情弔詭與悖理依然如幽靈,得著機會就滲透進文學家的所思所想。
也難怪。張瑞芬教授在評《遺事八帖》時就提到:「學院裡感受的是學院的腐敗,文壇裡自然可嗅出文壇的銅鏽,但林文義不只在文壇打滾四十年,又和政治沾上一點邊,知道的事也太多了一點,多到犯愁的地步了。」這本《歲時紀》沒有文壇或政壇的解密,但卻是作者在「打滾四十年」後的沉澱之書,告別那些禍毒亂象,並鄭重宣告文學創作才是後半生的重心。但我不免想起了他另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書名,《革命家的夜間生活》;文學究竟能不能成為革命家未竟之夢的另一種出口呢?曾於政界與媒體界顯過身手,再回歸文學後,又豈會對「文學」沒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閱讀何以?我在反思,關於人與人之間的詭異多端,心與心的冷和熱。」
「孤獨隱含一種巨大的力量,我無不探索文字更大的無限可能,所謂:人格即風格。
我手寫我心。文學本如是。
厭惡世俗,這是我的,傲慢以及堅執。」
「情欲,如是美麗,如此哀傷。
文學,如是隱約,如此雄壯。」
「活著,為了知心之人以及,僅存的文學。」
「在早無政治制約、自由民主的台灣,持續半生的文學書寫以及信念,依然是個『永遠的反對者』。
流亡。我在愛與恨交織的島鄉活著,我的心自問:流亡多久了?」
………
對於作家心中不時翻湧的無奈與喟嘆,作家之妻謂:「憂鬱,是因為完美主義。」但我要對文義說:「文學,是因為人世的不完美。」也許文學永遠無法提供最後的答案,但書寫卻給了我們一個可以將現實變形,讓眾生發聲的特權。
我特別注意到書中有一則談到「真日記」與「偽日記」的問題,而文義也立刻自覺地寫下:此時我所撰寫的《歲時紀》,是真是假?讀到這段時,我心裡立刻閃出了對話方塊:是真是假,交給後世來決定吧!散文家念茲在茲的忠於自我與流亡,難忘還是相忘,何妨換一種心境,管那個獄中總統是不是要出書,做為台灣作家幸或不幸,誰曰秋天不可以有春鬧,冬來嚐夏釀豈不是更有滋味?
歲末,偶有寒流與霪雨,但萬物生命蓄勢待發。初升級當了祖父的作家,一定更能感受到這種生生不息的驚喜,無怪乎全書以「最後祈盼,不分季節」二句為結語,是否也意謂著,心頭遺憾終於可以還諸天地?
精彩的文章不必然要長篇大論,這本《歲時紀》讓我更認識了這位作家勇於自我探索的勇氣與率真。全書在一種信手拈來的風流與感性中,流蕩著屬於他的獨特風格。雖是短歌之行,仍難掩文人天生的那股豪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