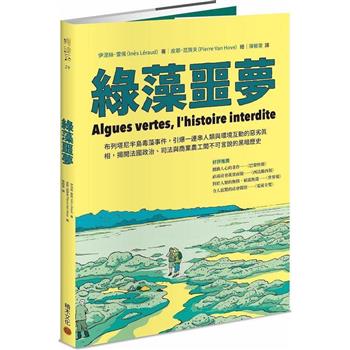半碗蜜
有一個小劇種,在村裡稱「二夾弦」,講訴世間哀愁。道具由一把胡琴來奏。那胡琴有四根弦,因每兩根弦夾一根馬尾拉奏,故叫二夾弦。風中顫音。
在村裡,它還有個更妙的稱呼,叫「半碗蜜」。
為啥叫半碗蜜不叫「半碗米」、「半碗水」、「半碗糊塗」?我曾專心探討過,是說二夾弦音調甜美,委婉動聽,聽一段心裡如同喝了半碗蜜一般。「糊塗」則是玉米粥,質稠,黏嘴。蜜的聲音是甜的。
鐵匠孫炳臣有一句口頭禪,「二夾弦一哼哼,不穿棉衣能過冬。」
他媳婦就會嘲笑他:「不穿衣服,照樣凍得你個屌朝下。」
他還有一句話,「不吃不穿不過年,也要聽聽二夾弦。」
他媳婦接著又嘲笑他:「好,那我今晚就不給你插糊塗了,你去吃哼哼吧。」
孫炳臣的後一句沒有上一句直接到位,唧唧復唧唧,就有較勁的意痕。
二夾弦分河東調和河西調。黃河東流去,在我們這裡拐了一個彎,掉頭北下,闖入渤海。以黃河為界,河東調是山東菏澤那邊演唱的,北中原的二夾弦屬於河西調。每年黃河發水,河東曹縣、東明過來的要飯藝人都唱河東調二夾弦。我們這岸的肯定也過去光臨,去傳播河西調。
河西調唱得最好的是道口鎮的一位藝名叫「大蒲扇」的,因演唱時習慣放把蒲扇,他以唱《王婆罵雞》出名,吐詞爽快流暢,一口氣可唱二百多句,還博得一個「翁倒山」的美名。
孫炳臣後來因為犯了那件政事,死了。我在一篇叫《鏊》的文章裡戰戰兢兢捎帶過。
他死了三十多年之後,他兒子掙了大錢,恍然想起他爹喜歡二夾弦,請了滑縣豫劇團退休演員,雖說這些藝術家們一一嘴裡跑風。在村裡唱了三天二夾弦,讓他爹喝了「半碗蜜」。
戲劇場景是他爹當年在監獄裡痛定思痛時沒有想到的。
2013.04.25
湊合畫
畫畫我多是閒湊合。如何湊合?說來你聽這些雕蟲之技。
一,先說紙張。
我信奉古人「敬惜紙張」語。我除了喜歡上好的舊宣紙,還喜歡賣紙的老闆娘,更喜歡一刀宣紙外面唯一那張包裝紙,粗糙簡單,這張紙落筆會有出奇之趣。我讓紙店老闆不棄,專門給我留著。老闆有心計,我都買過他數百刀宣紙,這對他是舉手之勞。且還落他半張紙情。
我喜歡在舊紙上染色。我在一張宣紙上面攤上一層熟透的桑葚,幾天後,葚的紫色會滲透紙上,花青?三青?酞青藍?那色是國畫顏色調不出來的味道。
我還擅長收留商品包裝紙,我在服裝店一張光滑的皮而卡丹廣告單上抄過蘇軾《寒食帖》。這是他人沒有的。時光恍惚。
二,顏料。
當年河南省銀行往鄭州新區大廈搬家,我為稻梁謀。金庫都拉空了,我撿到一瓶別人不要的山西清徐老陳醋,閒時就慢慢在宣紙上慢慢注醋,造勢。紙上醋是赭色,一副閻錫山的醋面孔,再醋上畫魚,落款《醋熘魚》。
有時覺得賓館裡洗髮液扔掉可惜,就攙合到顏料裡,會有意外效果。只是感情上多不喜歡這些工業用品,本質上我還是喜歡吃醋。吃陳年老醋,吃薛濤、陳圓圓的老醋,尤其鄉村手工醋。
我菠菜汁作草綠,浸泡過石榴皮水刷在紙上。還用芒果皮在紙上擦拭,製造黃,會出現另一種黃。一包感冒沖劑扔掉可惜,也調和到墨裡。宣紙風寒開始咳嗽。
三,器具。
調墨無硯時,環顧四周,我會量才使用,在一方不用的茶葉鐵盒裡。我端執著,寫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手冷哈一口氣。再寫「天生我材必有用」。
有一年自桂林捎來一盒羅漢果,治咽炎,泡完喝淨,不見羅漢了,只剩下一方空蕩蕩塑膠盒子,正好六個窩,就做了調色板,對我來說,調六種顏色足夠掌握。我胸襟小,色再多把玩不好。在我眼裡,世界只有黑、白兩色。水火不容。
最精彩的是我用小荷葉拓畫,用一尾鯉魚裹上宣紙拓畫,裹出來《雙鯉圖》。看得一邊外行人信心大增:操!你們這些鳥畫家竟如此易當,老子也會。
我說,你拓大象吧,最好拓大象雞巴才能超越我。
四,環境。
在北中原,少時家樸,捨不得買顏料。現在,地方小,又無案,故我多畫小品,叫掌上篇。就像我在一柄小勺子聚集風雲。
我沒有畫過大畫的原因:除了胸懷不遼闊之外,主要理由是沒有寬敞條件。我最缺少一方氣吞山河的黃花梨大案,大案上虎皮紋路縱橫,寬可跑馬。有一日能畫丈二匹荷花,在虎紋上,開一宣紙荷花,那是我一生實現不了的一個畫夢。
2011.07.25
二十條鄉村指南(我的不規則的記錄)
一個人必須認識十種以上的本土樹木名字,能分辨出來它們是桑、榆、構、楝、槐、柘。
向一隻匆忙走過討生計的小蟲子表示敬意。向飛翔五米之上的蒲公英表示敬意。
吃過野菜,吃過蟬蟲,吃過柳絮,吃過楊葉,吃過紅螞蚱。
五歲以前知道十種草名。(一年認識兩個並不代表笨。)
在青磚牆上畫過在嗅荷花的老虎。畫過一個憂鬱的少年夢。
很端正地張貼過堂屋的門畫和廚房的灶王爺,關心著鄰家女孩子頭巾上碎花的顏色。
聽到過馬嚼夜草馬嚼銅鈴聲馬嚼月光的聲音。享受一生。
即使沒有看過《詩經》也必須看過《七俠五義》或一卷沒頭沒尾的殘書,多年後才知道它的名字。哦,原來是這名字。
帶領過一條饑餓的草狗走過十里開外的親戚,攆過兔子,無目的的在田野瞎逛蕩轉遊過。
數過屋頂上比衣服白扣子大的那些星星,直到最終和大露珠混淆,直到瞌睡為止,流下口水。
知道哪一條鄉村小路可以通向四十里以外的縣城。和斑鳩一樣有著自己的方向感。有一截小小的耳骨和磁場。
知道鄉村暗喻,隱喻。認識本土標誌。譬如牆頭放一把夜壺的地方就象徵男廁所,而不放夜壺的地方同樣也可以當男廁所。
曾經見過鄉村裡最後一名漏網的地主。感覺他昔日並不金玉滿堂,不錦衣夜行。他是布衣。一片謙卑的瓦。一截咳嗽的門樞。
有過撿拾田野裡陶片的經歷。有一片竟還有手紋。如時間之掌的漩渦。
看到過家園將蕪,它包含有無序、落後、寧靜和貧窮,還有一部分無奈的知足和茫然。
知道院子空空蕩蕩像一張沒有寫字的白紙,在上面寫下過鐘聲,雞鳴,水聲。
知道鄉村常識。知道點燃麥秸烙餅比較均勻,是軟火;木柴是硬火。燒白色的麻桿炸出來的油饃最黃最暄。
每次遠行或歸來,第一個見到的總是站在村口迎著風的姥姥。
三十歲前必須離開那一座鄉村,否則,你可能一輩子就離不開了。
鄉村是減法。城市是加法,或乘法。到現在,都成四則混合運算了。
2010.11.20
履的履(鄉村小鞋史)
這詞彙有點拗口。其實就是「一雙鞋子的身世」。與鞋主人無關。
我二十歲以前穿的鞋都是我姥姥手工做的布鞋。從納鞋底,最後到襯鞋幫,做鞋面。一雙土布鞋上面留滿手溫。搖搖晃晃,土布舟子載著滿滿的風雨。
在古代,因為隱士都穿草鞋,「躡蹻擔簦」之士都是形容隱逸者。《五燈會元》裡,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腳走」。禪宗要求把草鞋子也甩了。腳踏大地。桶透天地闊。
我最喜歡的一句妙語就與鞋子有關,是《易經》裡一句:「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那是一雙素鞋子。
我姥爺對我講三國時,他說,劉玄德就是編草鞋出身。我知道劉備身上沒有禪宗氣,劉備只有一股仕途氣。他想當皇帝,想當總統。他骨子裡與素履無關。他的皇族身分且還可疑。
我姥姥做鞋底需要用許多舊布塊,使用吃剩下的「糊塗」(我們對玉米粥稱呼),把糊塗一層一層刷在布塊上,貼在木板或牆壁,晾曬,這一道工序姥姥叫「抿裱」。三天之後,揭下來。開始找鞋樣,用剪刀鉸成大小相適的鞋底,棉線穿納,成品鞋又叫千層底。
舊鞋子在傳統藥典裡是一味中藥,治霍亂不止,治食肉中毒。李時珍主張把鞋煮湯來喝。有點像「鞋湯」。在北中原現在官方做樣子制定的「四菜一湯」裡沒有這道。傳統的豫菜裡亦沒有這道。
鞋底還有一種不為外人可道的功能。童年時代在鄉村,醫療條件簡陋,村光棍老德有脫肛症,村裡叫「掉疊肚」,中醫胡半仙就讓他用一隻烤熱的舊鞋底托著,說,吸氣,最後托進去。
就是這樣。鞋底最有著大地底氣。
在聽荷草堂書櫃裡,至今我存有姥姥生前未納完的一雙鞋底,三寸金蓮形狀的鞋底。素面。姥姥是小腳。
四十年後,我看到有一個外國學者作消費調查,說,世界上一個女人從十四歲開始買自己第一雙鞋子,平均每年七雙,每雙四點九英鎊,以六十七年時間算,一個女人一生共四百六十九雙鞋子,折合十六萬元人民幣。
我肯定不會計算這個公式。我知道,這只屬於資本主義國度使用的鞋子公式,它在我的北中原社會主義鄉村不適應。故,此題無解。
我的姥姥、母親,她們這些北中原的女人們,她們一生節儉,一雙鞋要穿四、五年。破了縫補,縫補後再穿。最後,剩下一雙瘦瘦的鞋底,還要賣給走鄉串村的貨郎,換成針頭線腦、細碎雜物。
當貨郎鼓點在留香寨村外面消失的時候,一雙鞋的一生才算最後消失。那鞋聲像兩片秋風裡的殘葉,慢慢瘦去。
2010.07.09
手帕在鄉村的壯膽行為
有一年,在黃河風陵渡,迎著溫暖河風的良機,一個女孩子給我買了一塊晉中鄉村土布手帕。木蘭當戶織。我趁機說,這可是當定情物?她說,不!是讓你風中擦鼻涕的。
那塊手帕我保留到現在。
擋不住時光流逝。
在北中原,小時候我姥姥帶我走親戚,鄉村女人都有帶一塊手帕的習慣。土布,白色。村裡標準的手帕都是一尺長,一尺寬,正方形。小斗方模樣。
後來村裡又增添了洋布手帕,上面開著花。繡著格言。
行走,作客,陪客,大家會時不時掏出來手帕。握在手裡,或掖在袖裡。誰家有喜事,吃完喜宴有帶餘下饅頭的風俗,那叫「捎喜饃」。饅頭中間來一刀,夾一片薄肉,纏著一絲紅線。就用一塊手帕包裹,像是把一件喜事又重新裹起來,帶到家裡和那些沒來的人再次分享。這種行為叫「連吃帶袖」。
在鄉村,乾淨的手帕都透出來一股香皂的淡淡味道。年輕人定情,手帕是能把月光和乳名也包起來的。還包起來鄉村誠信。
有了手帕,是一種壯膽定神的行為。讓人不動聲色。
北中原除了女人帶手帕,有時男人也帶,我姥爺就帶手帕,耕地打場,不時擦汗。開始是一塊純淨的土白布,後來成褐色,成土色,最後和大地一個顏色。有一次他的手帕掏丟了,不習慣。幾天後在鄉路上又重新找到。這事讓我姥姥作笑料,結論是:沒有人來拾這塊爛布的。
手帕是舊物道具,持有它是一種簡約、環保的行為,它比當下的抽紙、餐巾紙。名片更內斂,穩定。現在女人不流行帶一張屬於自己的手帕,都帶一個兩個或真或假的坤包在世界遊走。最貴的是愛馬仕,KELLY和BIRKIN。
這是一個無手帕的年代。
手帕離棉布的距離最近。
二〇〇九年度一天,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赫塔‧米勒要登臺演說了,這個矮小的藍眼睛女人上臺,站定,她的題目竟是《你帶手帕了嗎?》。她質問文學。
文章切入點巧。是自己的。除了擦汗,一塊手帕還對抗專制統治。
「好像帶上手絹就等於媽媽也和我在一起。」
這個矮小的來自東歐共產主義國度的藍眼睛女人如是說。
2011.07.19客鄭
豬身上的一條公路
這一篇文章的主題不講豬,是講豬和速度。
留香寨村後一條鄉村公路通向五十里外的滑縣道口鎮,此條鄉村公路是北中原常見的「豆腐渣工程」。築畢典禮之後不到一年,路面就開始毀壞,像一鍋豆腐腦,上面湯湯水水。
這條鄉村公路上,一輛奔跑且超載的大貨車軋死我二大爺家那一隻大白豬。白豬整整養了一年。田野裡,幾個人急忙停下手中農活,圍著肇事司機,要他賠錢。司機是一位滑縣城的青皮後生,耍賴說:
「誰讓你這頭豬往公路上亂跑?公路是你家的豬圈嗎?」
那豬躺在路上,死了,且死得冤。又一鄉村非人類冤案。
我二大爺年輕時見過世面,聽到這語氣倒淡定,他也狡辯說:「你說的也是有道理,雖說公路上沒有豬圈,可你能說俺家的豬身上有公路嗎?」
周圍的人都笑。我操,我二大爺才是語言天才,簡直可以坐禪入定了。那小夥子慧根全失,竟不知如何回答。於是賠款。
要是一百多年前「馬關條約」我二大爺出場就好了。
在一個速度的年代,在速度裡,我二大爺其實說錯了,如今豬身上就是鋪滿了公路,可怕的是,公路已經鋪到人身上。
鄉村公路延伸到了豬身上,又延伸到狗身上,雞身上,兔子身上,羊身上,牛馬身上。無數條鄉村公路在沒有原則地縱橫交錯,一個講究提升速度的年代,速度們不分青紅皂白來臨,快的速度都不是好速度,糟糕的速度注釋著死亡概念。
有人求我書法,我給人寫過錢鏐說過一妙語,「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這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句老話,說古代慢速度,我二大爺家的一匹後現代豬天生不知道錢鏐的速度。錢鏐語言裡也不曾出現一條現代鄉村公路。速度在時光裡都顛倒錯位了。人和豬自己都掌握不住。
2011.05.05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豬身上的一條公路:手卷展的圖書 |
 |
豬身上的一條公路:手卷展 作者:馮傑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3-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52 |
散文 |
電子書 |
$ 252 |
文學小說 |
$ 284 |
文學 |
$ 316 |
中文書 |
$ 317 |
現代散文 |
$ 540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豬身上的一條公路:手卷展
陳芳明專文推薦:
每當俯臨他的散文,彷彿可以窺見一個乾淨而透明的靈魂。簡潔的語法,鄉愁的散發,無垢的美學。
舒國治 瘂弦 宇文正 王盛弘 丁允恭 幽默推薦
這是一本奇書
三兩句即醒腦,轉個彎就撞見幽默。
這是一本奇書,
若以案頭手卷視之,
宜用慢生活來讀,字行間,風吹落花,見心抱素。
但見馮傑以鄉土為榻,荷衣為服,
嘴角掛著最現代的一朵笑。
若以漢簡殘劄視之,亦可,
隨機天成,如紙牌,如撲克,
可自由組合,貌離神合,別有洞天。
這是一本奇書,
他借草、借木、借露水、借咳嗽、借哈欠之後,
遂成字、成句、成文、成一把薄薄的月光意象。
馮傑幽幽嘆道:
「江山依舊在,只是豬顏改」,其意云何?
待他以雞零狗碎,一五一十道來。
作者簡介:
馮傑,真名亦筆名,母親起的。
一直使用,將從有到無。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北中原一個叫孟崗的小鎮。
童年與外祖父母在滑縣小村留香寨度過。
在方圓不足二十平方公里的幾處村鎮輾轉接受教育。
小學、轉學,初中,降級。
職務最高曾任二年級組長,轄管近十人。
高中輟學,考入長垣縣農業銀行。
當信貸員、辦事員,通訊員、文案員、小職員。
在一個斷無詩意的空間獨自造詩造夢近三十年。
四十五歲那年持一蓋滿公章信函到鄭州來當專業作家。
本想養心,實為糊口。
低產作家,著作等腳。
電子郵箱:fengjie1964@163.com
章節試閱
半碗蜜
有一個小劇種,在村裡稱「二夾弦」,講訴世間哀愁。道具由一把胡琴來奏。那胡琴有四根弦,因每兩根弦夾一根馬尾拉奏,故叫二夾弦。風中顫音。
在村裡,它還有個更妙的稱呼,叫「半碗蜜」。
為啥叫半碗蜜不叫「半碗米」、「半碗水」、「半碗糊塗」?我曾專心探討過,是說二夾弦音調甜美,委婉動聽,聽一段心裡如同喝了半碗蜜一般。「糊塗」則是玉米粥,質稠,黏嘴。蜜的聲音是甜的。
鐵匠孫炳臣有一句口頭禪,「二夾弦一哼哼,不穿棉衣能過冬。」
他媳婦就會嘲笑他:「不穿衣服,照樣凍得你個屌朝下。」
他還有一句話,「不吃不穿不...
有一個小劇種,在村裡稱「二夾弦」,講訴世間哀愁。道具由一把胡琴來奏。那胡琴有四根弦,因每兩根弦夾一根馬尾拉奏,故叫二夾弦。風中顫音。
在村裡,它還有個更妙的稱呼,叫「半碗蜜」。
為啥叫半碗蜜不叫「半碗米」、「半碗水」、「半碗糊塗」?我曾專心探討過,是說二夾弦音調甜美,委婉動聽,聽一段心裡如同喝了半碗蜜一般。「糊塗」則是玉米粥,質稠,黏嘴。蜜的聲音是甜的。
鐵匠孫炳臣有一句口頭禪,「二夾弦一哼哼,不穿棉衣能過冬。」
他媳婦就會嘲笑他:「不穿衣服,照樣凍得你個屌朝下。」
他還有一句話,「不吃不穿不...
»看全部
作者序
【序】以緩慢抵抗現代──讀馮傑《豬身上的一條公路:手卷展》 陳芳明
每個人的時間快慢不一,被監禁在囚牢的人,時間相當遲緩;在運動場奔跑的人,時間特別快。由於對時間的感受不同,從而對空間的想像也有所差異。現代生活的節奏特別迅速,所有的事物稍縱即逝,甚至感情與思想也是倏起倏滅。都市的時間,往往只是媒介而已,從來都無法保留下來。尤其在消費社會裡,再也找不到任何鄉愁。新的商品不斷上市,舊的事物不斷丟棄,交替過於激烈,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眷戀。
馮傑的文字,有意使時間都緩慢下來。就像電影運...
»看全部
目錄
【序】 以緩慢抵抗現代──讀馮傑《豬身上的一條公路:手卷展》 /陳芳明
第一集 雞
A
暗夜細聲
B
鞭稍的長度
半碗蜜
C
城市雞鳴
湊合畫
D
地窨之深
多抽出一支筷子的象徵
鑄‧解詞
第二集 零
E
軛
二十條鄉村指南
F
風‧在童年時的解釋
反標
紡車和亂人方寸之弦
G
跟著姥爺去買馬
管管荷花
第三集 狗
H
荷葉的格言
荷花帖
狐狸頭瓜的稱呼
畫龍話龍都不點睛
和蘇東坡鬧
J
節日縫隙裡的兩件碎事
第四集 碎
K
誑花的道理
坷垃影
L
犁鏵的面龐
籠嘴
履的履
裡生外熟
兩匹著名的驢子
第五集 再雞
M
貓行瓦屋
木瓜志
麻經
每個女...
第一集 雞
A
暗夜細聲
B
鞭稍的長度
半碗蜜
C
城市雞鳴
湊合畫
D
地窨之深
多抽出一支筷子的象徵
鑄‧解詞
第二集 零
E
軛
二十條鄉村指南
F
風‧在童年時的解釋
反標
紡車和亂人方寸之弦
G
跟著姥爺去買馬
管管荷花
第三集 狗
H
荷葉的格言
荷花帖
狐狸頭瓜的稱呼
畫龍話龍都不點睛
和蘇東坡鬧
J
節日縫隙裡的兩件碎事
第四集 碎
K
誑花的道理
坷垃影
L
犁鏵的面龐
籠嘴
履的履
裡生外熟
兩匹著名的驢子
第五集 再雞
M
貓行瓦屋
木瓜志
麻經
每個女...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馮傑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3-08 ISBN/ISSN:978986323066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