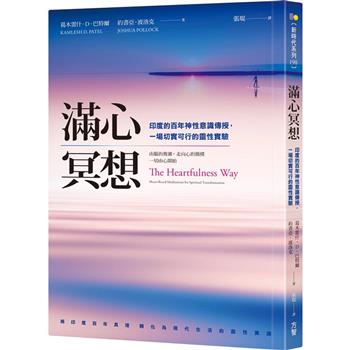一部千錘百鍊之作《髻鬃花》
葉國居創作二十年首度結集
故事好看,字字真情,篇篇都是文學大獎得獎作品。
近年來最經典誠摰的客家風情主題書寫。
結合葉國居書法藝術,併收錄最純最美的客語漢字散文名篇。
忠信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高天極
《大稻埕》導演 葉天倫
金鐘節目主持人 鄭朝方
名作家 吳晟 阿盛 愛亞 廖玉蕙 顏崑陽
聯合推薦(依推薦人姓氏筆畫排列)
髻鬃花,是一朵形象之花,一朵具有普世價值的花朵,開在許多客家人的心裡。
它是祖母頭上的髮髻,青絲到白髮,越老越開花,
那個年代,在勞碌的田莊,髻鬃花流著汗水的芬芳。
《髻鬃花》,透過葉國居特殊心眼,真情的感知,載記客家莊許多大小事。
篇篇都是文學大獎得獎作品,字字都是真情,近年來最經典的客家風情主題書寫。
全書有醇厚客家情調,併收錄〈寫大字〉、〈賣病〉、〈討地〉三篇客語漢字散文,
輔以作者毛筆書寫的詩文創作做為插圖,文學與書法藝術的結合,帶給讀者不同的閱讀經驗。
全文語言清新,敘述節奏靈活而有序,雖做單元切分,卻不至於零散,仍成渾然一體。而全篇意象始終保持在亦實亦虛之間,既寫實又略帶幻奇,表現出生命存在的悲苦與歡樂,莊嚴與荒謬。──顏崑陽評〈相片裡的公雞叫聲〉
〈暗夜挲摩〉是一篇摹寫動人祖孫情文章。作者寫中壯年坎坷勞苦,晚歲為疾病纏繞的祖母的一生。作者對祖母不但有深摯的情感、深入的觀察,且善用靈動的譬喻,將氣氛營造得淒清悲涼。作品由祖母的黑髮起筆,而及於黑夜;由夜色轉入月光;再由月光接寫不小心參雜在晚餐飯碗內祖母的銀白髮絲;緊接再敘攻城掠地、無孔不入的菜蟲;再由菜蟲,躍入如殘風中敗葉的祖母肺葉。將身為農婦竭精殫慮的祖母的一生,由生緩緩趨近老、病、死等意象,寫得淋漓,尤其此中環環相扣的安排令人印象深刻。──廖玉蕙評〈暗夜挲摩〉
作者輕抒淡寫,對父親的深重厚愛安靜地像泥土中萌發的芽,無聲地這裡那裡茁起,「農」這字的深遠意義經過那父親,讓人感動,令人低迴。──愛亞評〈討土〉
寫老農夫面對「現代化」的憤怒、抵抗、迷惘、失落,和田園眷戀的心情,十分細膩。「迷路」,既寫實也寫出真正的心理迷失;文字亦莊亦諧。──阿盛評〈螳螂問道〉
可能因為我是農人出生的,對葉國居的文章感受特別深刻,他透過父親與養鴨、父親與老牛、父親與毛蟹,點出人與土地的深情,若非作者擁有真實的人生閱歷和寫作才華,否則很難寫出這樣直達心田的文章。──吳晟評〈動物的證明〉
作者簡介:
葉國居,1965年生,台中市政府稅務局副局長,曾任新竹縣文化局副局長。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二度獲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散文二獎、台北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教育部文創獎。玉山、花蓮,竹塹、金像獎首獎,金曲獎最佳作詞人及台灣文學獎入圍。書法典藏於國立美術館、國父紀念館、台中市文化局。
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
《髻鬃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bQjzFDHOE
新聞簡介
「跛腳馬」春聯創作者葉國居一夕暴紅
http://www.nexttv.com.tw/news/realtime/hottest/10939272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暗夜挲摩〉入選 九歌年度文選
〈動物的證明〉獲 玉山文學獎正獎
〈客家菜脯的證明〉獲 梁實秋文學獎
〈螳螂問道〉獲 聯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
〈討土〉獲 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二獎
〈芥菜的證明〉獲 台北文學獎
〈鉤〉獲 台北文學獎
〈父親的毛筆與動物之間〉獲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山歌的證明〉獲 花蓮文學獎首獎
〈問路〉悅讀大台中散文
〈相片裡的公雞叫聲〉獲 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二獎
〈手抄一張宣紙〉獲 南投文學獎
〈父親的六食事〉獲 桐花文學獎
〈假面的證明〉獲 夢花文學獎散文獎
〈寫大字〉入圍 2012年台灣文學獎
〈賣病〉獲桐花文學獎
得獎紀錄:〈暗夜挲摩〉入選 九歌年度文選
〈動物的證明〉獲 玉山文學獎正獎
〈客家菜脯的證明〉獲 梁實秋文學獎
〈螳螂問道〉獲 聯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
〈討土〉獲 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二獎
〈芥菜的證明〉獲 台北文學獎
〈鉤〉獲 台北文學獎
〈父親的毛筆與動物之間〉獲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山歌的證明〉獲 花蓮文學獎首獎
〈問路〉悅讀大台中散文
〈相片裡的公雞叫聲〉獲 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二獎
〈手抄一張宣紙〉獲 南投文學獎
〈父親的六食事〉獲 桐花文學獎
〈假面的證明〉獲 夢花文學獎散文獎
〈寫大...
章節試閱
(標)暗夜挲摩
(小標)髻鬃花
對於黑夜的形成,始終有一種模糊的概念在我的心中凝聚:它,與人確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在每一個烈陽如漿的白日裡,祖母在田畝中佝僂耕種。在每一節翻土、播種、除草、施肥的動作間,揮汗如雨。強大的日光,攫取祖母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蘸成墨汁下嚥,經過時間的消化後排泄出來,叫做黑夜。
濃稠的黑夜在暗中默默的成長,流淌於小溪庭院、穀倉柴坊、豬舍雞寮,並不斷的擴張向田畝間的菜圃和水塘。夜色如墨,團團緊緊的包圍村莊,但它卻鎮不住祖母的雙腳,她背負著浩大的夜色,如同白日頂著烈陽,仍不斷的在田畝間穿梭,在豬舍雞寮間忙碌著。
對於我們小孩而言,鄉下的黑夜充滿著神靈鬼魅的氛圍。一入黑夜,便不敢大聲言語,不敢遠離住宅的四周,這是黑夜懾人的力量。但是,你一定很難想像,對於黑夜,我竟然沒有絲毫畏懼的感覺,因為我老早就發現了夜的繽紛和熱鬧,笑臉的月光穿過濃密的樹林,我在其中感覺大樹正在拉拔成長;溪水的唱遊伴著夜蟲唧唧,我在庭前微弱的燈泡下看著飛蛾翩翩起舞。除了這些外,還能騷動寧靜與黑夜的,便是祖母髮間流動的白光和她密集的咳嗽聲了!
就我有記憶之始,祖母的頭髮並非全白,大抵是黑白相摻的,到底是什麼時候,黑色素從她的髮中消耗、蒸散,我便全然不知了。記得我在念小學五年級時,一天,中午從學校回來吃午餐,在竹筷起落之間,發現在碗飯中夾雜著一根長髮,半截如霜、半根如墨,等到下午放學用晚餐時,再發現菜中的髮絲,便已通根如霜。
小時候的我並不懂事,屢屢發現飯菜間的髮絲,不管黑白,我總會先對祖母抱怨一番,卻從不關心黑與白所象徵的意義,我對祖母的白髮沒有任何的戒懼,就如同黑夜在我的心中不設防是一樣的,它不停的占據我和祖母相處的時間,我卻沒有一點警覺。祖母這一輩的客家村婦,習慣將長髮緊束成圓圓的髮髻,像是一朵盛開的花兒,我把它取名為「髻鬃花」。童年時我總是尾隨著這朵花到田園,它流著汗水的花香,隨著祖母年歲的增長,越來越白越像個花兒。越老越開花。
一回,中午用餐時,我發現菜中有幾隻螞蟻,打開湯鍋,竟發現成群的蟻屍,我一下子氣急敗壞的向祖母大聲的說道:「不煮頭髮,換煮螞蟻了?」
「螞蟻不會吃壞人的。」祖母怯怯的趨前安慰著我,也不知要再說些什麼。
「那晚上就煮螞蟻吃好了!」我在盛怒中擱下飯碗,逕自往外頭衝去。
夕陽下山,我才踩著步伐回家,一進家門,發現祖母不在家中炊飯,飢腸轆轆,心中有些著急,卻驚然的發現一輪白霜霜的月,在廚房窗邊晃悠悠的動著。我趨前一看,祖母弓身在窗邊,端著一鍋豬油盆,利用逐漸流失的天光,正在挑撿油盆中的蟻屍,不時的將沾滿油漬的手指伸進嘴裡舔乾,似乎深怕丁點兒的油脂浪費了。眼看天就快黑了,她的動作顯得有些慌忙。我悄悄的走近祖母的背後,發現她的頭就如同望日之月,像是由許多許多花朵簇擁而成的花束,在每一根的髮絲之間,流著暖暖的光汁,彷彿在一個下午之間,祖母的頭髮徹底的變白,究竟整個下午,祖母做些什麼事了?竟然讓烈日如此狠毒的吞盡她髮中的黑色素,我正納悶的想著。
「回來了!」祖母發現我回家了,高興的向我說道:「晚上的飯菜不會有螞蟻了,我在這兒挑了整個下午,一定夠乾淨的。」
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再看到她被憂慮拉扯陷落的雙頰,眼睛已是灰濛濛的一片。
穿過廚房窗邊的那道陽光真的毒辣!
那晚的夜色好濃好濃,將我和祖母密密緊緊的包裹在一起,感覺厚實而溫暖。和祖母躺在同一張床上,徹夜沒有入眠。淚光一直流連在祖母頭上的髻鬃花和蒸散的黑色素之間。
(小標)菜蟲
祖母以種菜為生。二分的田地種了十餘種菜作,當菜作成熟的時候,她會挑去市場賣,或向上莊的阿壽伯換米,向大碑養殖魚蝦的人家換魚換蝦。這些菜作,便成為我們的衣食父母。然而,種菜的辛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辛酸。菜作經不起狂風,也經不起旱澇,除了這些之外,最讓祖母感到傷神的,便是那些日夜顛倒,無法數計的菜蟲。
菜蟲,最喜歡在涼爽的夜裡出來,白天陽光來時,即躲進泥土裡。祖母常在一覺醒來,發現肥美的菜葉被菜蟲食成坑坑洞洞,這些坑洞讓祖母耿耿難安,如同一個國家的版圖,遭逢敵人攻陷、掠地,令人憂心如焚。當生計無法算計時,祖母會做出最頑強的抗拒。
七月之夏,酷熱難眠。夜裡,祖母駭然而起,她把我叫醒,告訴我她夢見成群的菜蟲,在水涘草浦間蠢蠢欲動,正要大舉的進攻菜園。我們迅即著裝,一如遭到敵人的夜襲,我緊緊的尾隨在祖母的後頭,在漆天墨地裡,藉著星光行走於陡峭的田埂上。無聲無息。安靜無語。像是要在利刃出鞘的瞬間,一舉刺向敵人的心臟。
腦滿腸肥的菜蟲,總是在夜半無人時,吃得癡肥臃腫,然後發出腥臊嗆鼻的飽嗝。祖母左手拿著手電筒,右手的姆指如刀,食指似鍘,用力的將隻隻的菜蟲切斷。我蹲在一旁,望著死去菜蟲的身上流出了飽滿的湯汁,鮮明帶翠,彷彿從中可以提煉祖母流下的汗汁、身上的鹽分、皺紋的痕跡,以及逝去的年歲。
我曾多次的想像,自己在大快朵頤葉菜時,如同菜蟲不斷的嚙啃吸吮祖母的汗水和心血。鮮明帶翠的湯汁,同樣的在我的身上盤旋、流淌。一日夜裡,跟著祖母去抓菜蟲,右手一不小心,被田埂上的五節芒割傷了,鮮血汩汩的流出,祖母連忙的在菜園中找尋雷公根的莖葉,在口中嚼碎後,連同溫熱的唾液,敷在傷口。翌日醒來,傷口竟然流出與菜蟲同質的湯汁,令人驚愕莫名。
我一面擦拭著傷口流出的湯汁,側耳聽到死去菜蟲的哭啼,腦中浮現的是祖母身上的血水,不斷嘩嘩啦啦流入我的體內,她顯得逐漸虛脫、憔悴、蒼老。其實我只是一隻受盡祖母寵愛的菜蟲,長年以來,有恆的蠶食著祖母的心血,多年以後,我仍時常為一幕自己率領著成群菜蟲,嘖嘖有聲吸食著祖母心血的夢境而驚醒。
醒來的時候,祖母已經躺在遙遠的山崗。
她死於肺癌。X光片下的二片肺葉,被一種名為「菌」的小蟲食成一個黑黑點點的坑洞,不斷的瀕臨崩塌的邊緣,在螢光幕上,又如同兩片在殘風中的敗葉,隨著祖母急切的喘息不定的搖擺。但對祖母而言,二片完整的肺葉,已經不具任何意義。即使在生前,肺葉的質量依舊沒有辦法和菜葉相抗衡,為的是讓一個疼愛的孫子,三餐得以溫飽。
如今,再也不能品嘗到祖母手植的菜作了,但是祖母在暗中弓身抓蟲的影像,一直都在我的眼眶中定居著,如同雷公根上祖母唾液的溫熱,至今餘溫猶存,在我多年後仍多感的指間。
(小標)祖母的新址
祖母死了!
她的雙頰凹陷,皮膚皺黑,身體比在世的時候,彷彿縮小了許多。像是木乃伊,泛黑、冰冷、乾枯,而且已經逐漸的凝固成型,掀開白幡,我再也忍不住悲痛。
沒有人來報惡耗!在台中念書,宿舍沒有電話,期末考的最後一天,早上陽光烈烈,沒想到考試結束時,便已細雨如織,我坐在試場中,憂心如焚的作答,我可以確信,在同一時間裡,祖母正躺在故鄉那張隨著病情加劇搖晃的床上,急促的呼吸聲,正穿過千片雲層、百條山川,間間疊疊的在我的耳膜中催促而來。坐上火車,心中早已瀰漫不祥的兆頭。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四十分,北上的自強號,我憑窗而坐,駭然的聽見祖母的最後一聲咳,響成天邊的一聲雷。
向來,有許多事,我和祖母是交感互通的。祖母辭世的時間,與我憑著車窗聽到驚雷一聲的時間,事後對照沒有絲毫的差池。任何的感覺、幻覺,在長達多年的相處裡,也經常是相互交應的,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了思想和相思。我在弱冠之年離鄉讀書,早已體會出鄉愁的滋味,在每一個晨昏間,在每一個季節裡,鎮日坐在課堂上讀書,卻發現手上長了厚繭,日日感覺得出肩上的辛酸,其實,那正是一百多里外的祖母,日夜勞動耕耘的辛勞,竟相同的在我身心中滋長。我在台中,最惦念的就是祖母多咳的病,屢屢讓我想到鞭炮,爆裂後肉身即將支解的恐懼。每次我回家時,她總是隱忍在我的面前不咳,或許是相思使然吧!看到她倚門淒遲等待我回家的臉孔,實在不忍揭發她的濃痰隨處可見的事實,心知肚明祖母的病情,只是,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默契,便是相互隱瞞,不讓對方增加負擔。
祖母死了。我坐在她的靈前三個夜晚,用心回憶就我所知道的祖母一生。少年多折,中年勞苦,晚歲病疾纏繞,如同一條崎嶇的山道,從卑處到高嶺,未見平坦。她就像靈前的蠟蠋,肉身在燃燒,滴下的汁液凝固成我,當她的生命走到盡頭,所有的精氣、血水都已完整匯入我的體內。像是一個重新的開始。我在渺渺的白煙裡,感受祖母在我生命中的分量,我宛若是祖母的替身,每每在冥紙的燃燒之間,抬頭望望靈前的相片,總覺得像極了自己。
或許,如今祖母只剩一具勞動過度的皮囊,一具需要長期睡眠、徹底休息的身軀,當三個黑夜過後,祖母將定居在一個依山傍水的新址,所有一切一切辛苦、辛酸的回憶,纏繞的宿疾,將隨著黃土一一掩蓋。我將要在她的塚上植上美麗的花卉和樹苗,讓她有一個安適的家,舒適的過著她的生活。當如炮的咳聲不再,黏膩的濃痰不來,所有的病痛不發,一切的俗世不擾,感覺是那麼寧靜而美好。
我豁然開通了,祖母死了,我心中充滿無限的歡喜。
而我漸漸的相信,死亡只是靈魂的移居,正如同祖母身上的血水、精氣完整的灌注我的體內,只要我在,她終究還是存在的。我有越來越深的感覺,祖母依舊沒有離開老家的四周,因為我在每一個黑暗的角落,肌膚領略得出她的體溫,味蕾嗅得出她身上的味道。在每一個雷聲中,聽到她的咳聲;在每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看到她流著白光的頭髮,看到一朵髻鬃花。站在祖母的神位前,燃一炷清香,低頭跪拜,在我抬頭的瞬間,看到渾濁的煙像一條長長的白蛇,纏繞出一些迷濛的影像:祖母淒遲的臉孔。廚窗邊的月光。坑洞的肺葉。菜蟲。
(標)動物的證明
(小標)聽力障礙的證明
我確信一個人和一種動物朝夕相處,一定會感染與動物相同的氣味和習性,嚴重時還可能會殃及身心。
父親蹲在溪岸旁殺鴨,以他的姿勢看來,他拔毛的手法像是在田中除草,清理內臟如同清理一顆木瓜這麼流利。這年的冬至,父親決定煮一隻薑母鴨為我進補,當他拎著鴨頭走回廚房,恍惚間,我發現這隻鴨像極了父親的膚色,當他的左手按著砧板上赤裸裸的鴨身落落揮刀支解時,我不敢靠旁觀賞,因為我始終有一種幻覺,父親在剁肉的同時,也在砍斬著自己。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父親在我心中的形象,竟然是鴨群中的一隻鴨。起初,我對於自己有這樣的想法覺得十分荒唐。父親養鴨三十多年,從庭院養到河岸,從白鴨養到番鴨,從幾十隻養到幾百隻,父親都是群鴨的統治者,再怎麼說,他都不可能成為被統治的臣民。然而,這種影像,卻像一張張的幻燈片,一再一再的在我心中的暗室中播放。
在這個寂靜的溪岸旁,只要你仔細一聽,便可以聽到群鴨的呷呷喧鬧,對於這種聲音,父親早就習以為常了。當農閒的時候,他鎮日的在鴨群中穿梭,或在岸旁的空地打磨磨,不時的驚動在水中沐浴或在岸旁休息的鴨群,父親很少出聲,因為他知道,鴨子聽不懂他的語言。於是,他經常用手勢來下達餵食的指令,以及讓鴨群辨別天黑時向左向右趕回鴨舍的路途,但是隨著距離的拉長,一旦超過了鴨子的視力範圍時,這樣的手勢便頓失效力,這時,父親便會「齁齁」的出聲,並大幅的擴張他的手勢,鴨子雖然聽到父親的聲音,但卻不知道父親在說些什麼,東張西望的顯露出一副惶惶無措的模樣。
第一次發現父親也有這般模樣,是在車聲隆隆如嘩然山澗的市區中,才一轉眼,父親便消失在百貨公司的大門前,對於一個因樹為屋、隱居鄉野的父親而言,都市,就像一個大湖,而他就像一隻道地的旱鴨,一旦下水便極可能會流連忘返,進而迷失了歸途。我確信父親一定沒有走遠,張大眼睛左右尋視,像是一支銀行的監視器,所幸,在鏡頭下,我發現父親的身影,他站在對街頻頻盼顧。
「爸!我在這裡啦!」我依父親可以聽到的音量喊著。車流很快,父親彷若聽到了,卻不知道聲音的方向,伸長了脖子左顧右盼。
「爸!我在這裡啦!」我再趨前向他叫著,父親確定有人在叫他,但他卻聽不懂我的語言,惶惶然左右搖動著頸項,直到發現我已站在近處向他揮手作勢,父親方才露出了笑容。
父親的姿勢,像極了一隻落單的鴨。
從這年開始,我知道父親患了日漸嚴重的聽障,隨著年齒嚮暮,我們之間所產生的溝通障礙,必須經由近距離的比手畫腳才能移除。
我與父親,父親和鴨子,竟然在傳達間產生了相同的阻礙。好幾次我從鴨群中叫著父親,霎時,鴨舍中重複了許多父親影像,我看到幾乎在同一時間內,與父親動作如出一轍搖著頸項東張西望的——鴨群。我的父親。
究竟,這是什麼力量使然?一直在我的腦中打轉著。
傳說中,帶領反清革命的「鴨母王」朱一貴,年輕時即在羅漢門鴨母寮以養鴨為業。有一天,朱一貴像往常一樣,趕鴨到河邊後,躺在岸旁青青草邊睡著了,醒來時,他蹣跚走到河邊洗臉,甫一低頭,他發現水中自己的身影,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自以為是台灣傳說中喊水也會結凍的真命天子。於是,他對著鴨群發號施令。正步走。前進。游泳。潛水。令人吃驚的是無論他說什麼,鴨子都會按照他所說的語言活動起來,果然,朱一貴後來被眾人簇擁為帥。這證明鴨母王確實深諳鴨子的語言,父親經年與鴨群相處,他不是真命天子,無法像朱一貴這般能號令鴨群,相反的,卻在不知不覺中被鴨群進行大規模的感染。
我豁然明瞭,這樣的現象是出自一種龐大力量的傳染,像是卡通中的泰山,長年居住山林,因而被感染了山中動物的習性,動作酷像山中的猩猩或是獼猴。
載著父親到公所申領殘障手冊的那天,出來時已是正午,比鄰公所旁的一家燒臘店傳來撲鼻香味,父親逕自走入店中坐定,指著玻璃櫃中上架如同上吊的燒鴨說道:
來兩碗燒鴨飯吧!
我搖手向父親示意拒絕。同時,趨前告訴店員:我,不吃鴨,給我來一客燒臘。
(小標)休耕的證明
當清晨的太陽從門外射進來,牛舍裡不像昨夜那樣黑湫湫的,我走過了牛欄,發現老牛已經不在了,心中產生了莫名的落寞,好像是一個經年生活在一起的親人,當他住在遙遠的山崗時,偶然,你走進了他的房間。
老牛跟著父親十多年,頭上兩隻彎彎長長的犄角像番刀,牠的身體非常壯碩,若是跟父親矮小的身材相比,似乎,牠就成為父親最堅實的依靠。的確,當先進的耕作機器陸續推陳出新時,父親依舊守著最初的耕作方法。老牛,竟日的跟著父親黑汁白汗的在田中幹活。
村莊的人都笑著父親跟不上時代,父親總是呶呶唧唧的應答:水牛比較不會變舊啦!漸漸的,老牛成為村莊唯一耕作的牛隻,父親一向不喜歡向人嚼舌嚼黃,卻私下向上畝的阿壽伯表示,只要田還在、力可逮,他便要將老牛留在身旁。
老牛與父親之間,除了共同的工作情感外,老牛也是父親最忠實的夥伴,有了老牛,父親只要擔心風雨,不必擔心繁雜的人情世故,胼手胝足的流下汗珠,不用流露虛偽的言語,好像是一個遠離塵囂的和尚,日夜的敲著木魚交談,心靈得到最舒適的安置。
曾幾何時,父親的夢想卻被逐漸擴張的休耕政策撐破了。一紙休耕的證明拿在手中,父親沉重、無助、迷惘,灑下了鎮公所發放的油麻菜花種子,領了一筆微薄的補償,卻從此買斷了父親的歡笑。當油麻菜花發狂的在田園開放,父親依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牽著老牛在田園吃草,累了就悵然坐在埂上,像是一具自製的稻草人,它不必下田耕作,卻迎接著每一天的日曬雨淋。肩上少了鋤頭,空有田園徒讓長風呼嘯,就如同俠客腰際少了佩劍,空有武功無法施展,因而失去了名分存在的意義。
老牛的祖先,是天帝派遣下凡幫助人們耕種的神獸,牠們代代相傳並遺傳著善於耕作的基因,在牠們靠近頸項的背脊,一旦套上了牛鞅木後,不但可以犁田,而且可以拉車。一連數月,老牛不用耕作,不用拉著堆積如山的甘蔗牛車,牠變得心浮氣躁,屢屢在田中來回的奔跑,或用長角磨撞田埂,如同一隻氣急敗壞的鬥牛,正在場上進行一場激烈的格鬥。
父親與老牛,他們同樣的為了一紙休耕的證明而心神不寧。
我有越來越深的感覺,鋤在肩上、鞅在背上,他們就像泰雅的原住民臉頰,戴著一個V型勝利圖騰,那是男人的英勇,也是女人的美麗,更是責任與榮譽的表徵。父親與老牛,當他們雙雙卸下了這份責任與尊榮,失落自是不言而喻。這樣經過了半年,老牛病倒了,清晨癱在牛欄,一連數日不食不眠,父親憂心如焚,請了獸醫診斷,知其大去之日不遠,決定僱車將其運走,臨走前,父親站在牠的身旁,打著嗝頓說道:
你跟𠊎(我),也有十過年,今日,你愛(要)走,𠊎,係(是)盡毋甘,承蒙你摎𠊎(跟我)做伴恁(這樣)多年,送你走,你,毋好(不要)轉頭,來世,正(才)來,見。
我看到老牛的左眼掉下了一顆晶瑩的淚,像是清晨芋葉上的珠露,像是靜寂夜裡的星光,急促的呼吸聲在回憶犁田時的喘息,身上黑槎槎的長毛,一如用背脊拖運過的枝枝甘蔗,老牛終於閉下了眼睛,感覺每一天默默生成壯大的夜色山林。
老牛走了,父親日日嚬蹙憂傷,我心裡著實有些著急,深怕動物會進一步進行更劇烈的感染。為了讓父親重拾老農的丰采,我極力的鼓舞父親在溪岸旁,種植菜作和甘蔗,父親拗不過我的請求答應了,再荷起鋤頭耕種。他大力的清除岸旁的石頭,像是清除心中久悶的壘塊,不出數月,我在河岸拉拔的甘蔗中,見到了昔日的田園風華。
(小標)公車半價的證明
父親七十歲了,依照規定,搭客運可以享受半價的優待。
他吃力的爬上公車,像極了逆流橫行爬上溪流攔水壩的毛蟹,隨時都會有掉下來的危險。
對於溪流的毛蟹,我是再熟悉不過了。二、三十年前,只要你拿著手電筒,在冬日的溪流走上一回,你會發現成群的蝦兵蟹將在岸邊的水草間唼喋。蟹將貪食,舉凡是飯粒、饅頭屑、或是父親殺鴨後留下的濃黏腸肚,牠都會一一的搬回蟹府享用,人們利用牠貪吃的弱點,紛紛設陷誘捕,包括父親,他砍下身材修長的孟宗竹,去除竹肉,將竹皮編成蟹籠,一如置放在山中誘捕山鼠的鐵斬,讓獵物在不知不覺中投進了他的圈套。
誘之以食。這麼說來,製餌就必須花費上一番工夫了。從霜降到冬至,是捕蟹的最佳時節,每天,父親在天光流失之前,便把中午剩餘的白飯,加上養鴨的飼料揉揉搓搓,像是黏膩可口的米糕,後將其切成塊狀,放進灶內用微火燒烤,又像是現在流行胡椒餅,微黑的火燻色調帶著令人垂涎的香味。父親用紗布將其緊繫後置於籠中,然後將竹籠扛在肩上往溪流的方向前行,籠口逆流置於河上,香味慢慢的在水中蔓延、流淌。我坐在家中便可以感受到,那早就在我耳膜生根的溪流水聲,此時,因為蝦兵蟹將的爭相走告,一時之間歡聲雷動、熱鬧非凡。
就如同播種以後期待發芽的夢想,父親在天亮之前涉水入河,當他拉起水中竹籠,滴滴答答的水聲如同掌聲響起,正當父親眉飛色舞,眼神中流露出獵人的威風時,籠內的毛蟹方才發覺自己離開了家園,驚惶得手足無措。推擠、亂竄、慌張來回的爬行,巴不得能從竹編的細縫中鑽出,如同樹葉打著樹葉發出嗦嗦的聲響,離水之後急切的想回水中的懷抱,口中並吐出堆積如山的白色泡沫,像是渴望入土的穿山甲,一旦被人捉住時,同樣會緊張的吹出一個個白色的氣球。我一直認為父親在魚獵方面,確有叱石成羊、撒豆成兵的功力,向來籠內毛蟹成群。牠們進入湯鍋,用文火煮熟後令人脾胃大開,父親騎著鐵馬將其運到鎮上,市鬻供不應求。
從溪流到鎮上,約莫有四公里的距離,年輕時父親騎著鐵馬走在顛簸的碎石路上,他抓緊了把手用力踩著踏板,腿上帶勁的流著湯汁,目光狠狠的注視著前方,灰色的機械和黝黑的膚色,結合成一隻動能十足的野狼。
父親最看不起貪婪的公車大象,昂貴的票價需要花費一斤的毛蟹,他壓根兒不屑搭上公車,即使當他年紀大了,體力不如從前,以他佝僂的背脊加上後座簍裝的毛蟹,他騎鐵馬時的模樣,是一隻徹底的雙峰駱駝,不過慢歸慢,這時的柏油道路已經顯得平坦許多,為了一斤的毛蟹,他依舊鍾愛那匹鐵馬。
直到父親七十歲的那年,他才從阿壽伯的口中得知,搭乘公車可享用半價的優待。自此,他對大象貪婪的形象終於改觀了,那日,我送他到候車亭坐車,再三的叮嚀他要記住兩件事,一是下車的站牌要記牢,二是乘車安全要注意。我目送父親爬上公車,他已不像從前那樣,在山林種筍來去之間神色自若,如今車門前的三個階梯,在他的眼中拉高成為萬丈峭壁。
他爬上了第一個階梯,旋即以雙手握住車門前的橫桿,低著頭,以側行的姿勢拾級而上。我突然想起,那日逆流橫行爬上溪中攔水壩的那隻螃蟹,隨時都會有掉下來的危險。
社會福利政策製造了一個既香且甜的誘餌,父親和他捕過的毛蟹一樣,被誘進入了一個竹籠,他告訴我那天的客運晃蕩如水,他渴望著儘快赤足重回地面,在一陣暈眩後,口中噦吐出白色的泡沫……
溪流彎彎,在我的眼裡蜿蜒成一條長長的蛇,它吃過了每季臃腫的雨水,多年來身體不斷的肥壯。昨夜一場大雨,今晨起床後,發現濃霧瀰漫,我坐在家中,彷若聽到了溪水捲起了古都都的潑天怒濤,推窗看不見溪水的身影,只發現近處,父親比手畫腳的趕著鴨群,手中抓著一隻上岸避洪的毛蟹,我彷若在同一時間內,又看到了許多的父親。
那老牛呢?我猜想牠一定是在濃霧之中。
(標)暗夜挲摩
(小標)髻鬃花
對於黑夜的形成,始終有一種模糊的概念在我的心中凝聚:它,與人確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在每一個烈陽如漿的白日裡,祖母在田畝中佝僂耕種。在每一節翻土、播種、除草、施肥的動作間,揮汗如雨。強大的日光,攫取祖母髮中的黑色素與汗水蘸成墨汁下嚥,經過時間的消化後排泄出來,叫做黑夜。
濃稠的黑夜在暗中默默的成長,流淌於小溪庭院、穀倉柴坊、豬舍雞寮,並不斷的擴張向田畝間的菜圃和水塘。夜色如墨,團團緊緊的包圍村莊,但它卻鎮不住祖母的雙腳,她背負著浩大的夜色,如同白日頂著烈陽,仍不斷的...
作者序
我白天從事稅務工作,夜晚專心寫字寫作。白天,數字需要理性。夜晚,文字需要感性。在日夜心情交替中,匆匆過了二十年。這本散文集,是我長年以來的夢想。我以毛筆書寫自己的文學創作,作為散文集的插圖,想要用這本散文集,來表達自己,愛上文字勝過於迷戀數字。
從小生活在客家莊,年邁的老父年輕就耳背,他一生在客家莊的所歷所見所聞,都逃不過我特殊的心眼,看似平凡卻極不平凡。我一向認為,散文的真情比真實來得重要,每次得大報文學獎,就有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紛紛打電話到我的服務機關探究,文章是不是真的?真的,假的,我肯定說,我的散文是真情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被自己感動過,四十歲前曾經有一次,在寫作的當下淚濕衣衫。
我喜歡書寫,濡墨臨池。二〇〇三年後,大概近十年的時間,我因工作的關係,頻仍往返桃園、新竹、台中間,家中大小事,概由妻子靜儀悉攬,為了彌補我對小孩的愧疚,只要回家過夜,晨起,我一定會為他們準備早餐。夜歸,孩子入睡;早起,孩子尚未起床。上班前,我習慣以毛筆在宣紙上留話:光和羽,饅頭在電鍋,冰箱有鮮奶,蘋果一人一半,吃完,到校認真讀書。
時間久了,發現這些早餐書寫,料理不同,字跡各異,快慢有別。孩子除了感受父親的存在外,他們還時常從字裡行間,猜出是日的我或焦,或忙,或喜,我開始有了書法線條會說話的想法。自此,我開始以毛筆書寫自己的詩作散文,我深信用毛筆書寫自己的情思,要比抄一段唐詩宋詞來得真摯。至少在看千篇一律的電腦細明體後,目光移到作者親筆書寫的片段中,可以感受不同時空的心情。如同我再次看到早餐書寫,恍然回到我兒我女的童年,我希望光和羽,永遠就這麼大,就那個頑皮的年紀,於是我會一看再看那流逝歲月的清晨書寫。書痕夢清,回到從前。
髻鬃花,是一朵形象之花,一朵具有普世價值的花朵,它是我祖母頭上的髮髻,青絲到白髮,越老越開花,它開在許多中壯年客家人的心裡。那個年代,在勞碌的田莊,髻鬃花流著汗水的芬芳,我以髻鬃花為名創作歌詞,由鄭朝方先生譜曲,並獲得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入圍。由於這本書,載記客家莊許多大小事,遂以髻鬃花做為本書的命名。
此外,本書收錄三篇客語漢字的文章,以母語發音的文學創作,希望能有更多的迴響。驚雪饒古,圍夢真清,夢想終以清晰呈現。感謝黎秀湮老師長年對我客語用詞的指導,她以客語改寫我的散文創作〈討土〉一文,併以收錄在本散文集中。感謝陳文智小姐,為這本散文集精心手繪設計封面,感謝雙親、家人、兄姐一路給我的支持,更要感謝和我曾經一同工作的同仁以及讀我文章的好朋友們。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台中市北區梅川河畔
我白天從事稅務工作,夜晚專心寫字寫作。白天,數字需要理性。夜晚,文字需要感性。在日夜心情交替中,匆匆過了二十年。這本散文集,是我長年以來的夢想。我以毛筆書寫自己的文學創作,作為散文集的插圖,想要用這本散文集,來表達自己,愛上文字勝過於迷戀數字。
從小生活在客家莊,年邁的老父年輕就耳背,他一生在客家莊的所歷所見所聞,都逃不過我特殊的心眼,看似平凡卻極不平凡。我一向認為,散文的真情比真實來得重要,每次得大報文學獎,就有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紛紛打電話到我的服務機關探究,文章是不是真的?真的,假的,我...
目錄
自序
暗夜挲摩
動物的證明
客家菜脯的證明
螳螂問道
雞母蟲醒來的時候
討土
芥菜的證明
鉤
父親的毛筆與動物之間
山歌的證明
問路
禾夕夕
相片裡的公雞叫聲
手抄一張宣紙
父親的六食事
假面的證明
寫大字(客語漢字)
賣病(客語漢字)
討地(客語漢字)
序
自序
暗夜挲摩
動物的證明
客家菜脯的證明
螳螂問道
雞母蟲醒來的時候
討土
芥菜的證明
鉤
父親的毛筆與動物之間
山歌的證明
問路
禾夕夕
相片裡的公雞叫聲
手抄一張宣紙
父親的六食事
假面的證明
寫大字(客語漢字)
賣病(客語漢字)
討地(客語漢字)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