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沒卵頭家》、《俎豆同榮》之後,精神科醫師作家王湘琦費盡精神又一臺灣本土長篇小說
《骨董狂想曲》獨樹一幟的臺灣喜劇風格,莊諧雜陳,魔幻寫實,劇情看似荒誕滑稽,實則赤裸裸地揭露了臺灣的社會風尚、道德面貌、世態人情以及政治狀況,令人拍案叫好!
魔神仔憨神憨神
人牽毋行,鬼牽嗆嗆走
嘖嘖嘎嘎嘖嘖嘎嘎——
這是關於一個古怪的精神病人「孫行家」一生的怪誕經歷。
傳說臺灣深山有「魔神仔」,祂們會幻化成粉紅色的小矮人,有時又像一陣粉紅色的風自由來去,魅惑人。
榮鎮人深信魔神仔就是曾與祖先們相知相惜的貴人,一旦這貴人化身的粉紅色風吹起來,任何美夢都能成真!
孫行家是一名流浪教師,抑鬱不得志,他來到榮鎮芒草河岸,向「魔神仔」許下「甄選上代課教師」的願望後,竟真的接到錄取通知。從此,他與「魔神仔」達成公平交易,只要遭遇不順心的事,便向「魔神仔」祈求。他更夢想著藉由買賣骨董發財致富,甚至能死而復生……。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骨董狂想曲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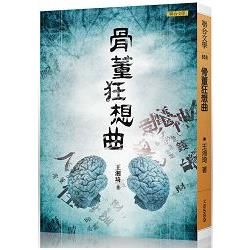 |
骨董狂想曲 作者:王湘琦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5 |
二手中文書 |
$ 276 |
中文書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8 |
小說 |
$ 315 |
小說 |
$ 315 |
現代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骨董狂想曲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湘琦
一九五七年生,台北市立西園國小、萬華國中、建國中學畢業,臺師大生物系、高醫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現為精神科專科醫師,曾任三峽靜養醫院院長,現為王湘琦身心診所院長。
曾以〈沒卵頭家〉獲第一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亦曾受時報文學獎、巫永福文學獎等。著有小說集《沒卵頭家》、長篇臺灣歷史小說《俎豆同榮》、長篇小說《骨董狂想曲》。
王湘琦
一九五七年生,台北市立西園國小、萬華國中、建國中學畢業,臺師大生物系、高醫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現為精神科專科醫師,曾任三峽靜養醫院院長,現為王湘琦身心診所院長。
曾以〈沒卵頭家〉獲第一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亦曾受時報文學獎、巫永福文學獎等。著有小說集《沒卵頭家》、長篇臺灣歷史小說《俎豆同榮》、長篇小說《骨董狂想曲》。
目錄
自序
故事的源頭
第一章、古怪的病人
第二章、放牛班的歡呼
第三章、人性生意
第四章、拒絕服藥的病人
第五章、賭徒之歌
第六章、窟仔底的冒險
第七章、遠離的父親
第八章、世外桃源
第九章、死而復生的秘密
故事的尾聲
故事的源頭
第一章、古怪的病人
第二章、放牛班的歡呼
第三章、人性生意
第四章、拒絕服藥的病人
第五章、賭徒之歌
第六章、窟仔底的冒險
第七章、遠離的父親
第八章、世外桃源
第九章、死而復生的秘密
故事的尾聲
序
自序
對臺灣人而言,所謂的「官方說法」經常就是個笑話!雖然這種令人發噱的感覺,有時和氣得想吐血差不多,但臺灣人就是愛笑!我們的祖先都是勇敢的移民,差別只在於早晚先後罷了!「移民」往往意味著「逃脫」,而「逃脫」自古以來就是臺灣老百姓最大的「夢想」!
「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創作形式,可真、可假,可長、可短,可悲、可樂,就是不可寫成了「官方說法」!這點很難!我太太就常說:「看你寫的小說常令我有點想吐血的感覺!」也罷!也罷!人生苦短,文藝無窮!不寫不行!不寫不行!
「魔幻寫實」、「黑色幽默」的學理,老實講——我不懂!但「平鋪直述」的表達方式有時不但興味缺缺,還常會讓寫作的人意外地被關進牢籠裡去!這冷酷的現實問題,古今中外皆然!於是乎,自古以來,讀書人有歸隱山林的、有裝瘋賣傻的,這其實不失為一種品格高尚的好傳統!《骨董狂想曲》是一部完全虛構的長篇小說,既然全是「無中生有」,又為什麼要掰得這麼長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說——讀書人憋了多長的氣,小說就會有多長!如此看來,像我這種半調子的讀書人,應該頂多只會被判「緩刑」!
其實,將一切抗議的矛頭都對準官府,確實也不盡公道!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有怎樣的人性,就有怎樣的人世!這——始終是令讀書人汗顏的老生常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我完完全全不懂!若問重點到底是在「批判」還是在「現實」?那可能就變成了個永遠無解的問題了!
不認識我的人常會覺得我太嚴肅,認識我的人又會感覺我太無聊,其實,我只是無趣!我覺得——活在當今人世,官員講話無趣,官越大就越無趣!電視節目無趣,收視率越高的就越無趣!朋友聊天無趣,越親近的往往就越無趣!「無趣」簡直就是當今人世最大的「流行」了!怎麼樣才能減少一點「無趣」呢?我覺得或許「文學」能幫上一點忙!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文學一向「收視率」最低!純粹靠文學創作吃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不是肯定會餓死,就是只剩半條命連腳步都踏不穩!這——總算是個還算「有趣」的現象了!哀哉!哀哉!
「象徵主義」是人類文明的一扇窗,透過這扇窗,文學有了自我療癒的特質!創作者大可輕鬆地躺下身來仰望天際,不浪費力氣在大聲疾呼上,或許會讓飢餓的感覺好過一點吧?
對臺灣人而言,所謂的「官方說法」經常就是個笑話!雖然這種令人發噱的感覺,有時和氣得想吐血差不多,但臺灣人就是愛笑!我們的祖先都是勇敢的移民,差別只在於早晚先後罷了!「移民」往往意味著「逃脫」,而「逃脫」自古以來就是臺灣老百姓最大的「夢想」!
「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創作形式,可真、可假,可長、可短,可悲、可樂,就是不可寫成了「官方說法」!這點很難!我太太就常說:「看你寫的小說常令我有點想吐血的感覺!」也罷!也罷!人生苦短,文藝無窮!不寫不行!不寫不行!
「魔幻寫實」、「黑色幽默」的學理,老實講——我不懂!但「平鋪直述」的表達方式有時不但興味缺缺,還常會讓寫作的人意外地被關進牢籠裡去!這冷酷的現實問題,古今中外皆然!於是乎,自古以來,讀書人有歸隱山林的、有裝瘋賣傻的,這其實不失為一種品格高尚的好傳統!《骨董狂想曲》是一部完全虛構的長篇小說,既然全是「無中生有」,又為什麼要掰得這麼長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說——讀書人憋了多長的氣,小說就會有多長!如此看來,像我這種半調子的讀書人,應該頂多只會被判「緩刑」!
其實,將一切抗議的矛頭都對準官府,確實也不盡公道!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有怎樣的人性,就有怎樣的人世!這——始終是令讀書人汗顏的老生常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我完完全全不懂!若問重點到底是在「批判」還是在「現實」?那可能就變成了個永遠無解的問題了!
不認識我的人常會覺得我太嚴肅,認識我的人又會感覺我太無聊,其實,我只是無趣!我覺得——活在當今人世,官員講話無趣,官越大就越無趣!電視節目無趣,收視率越高的就越無趣!朋友聊天無趣,越親近的往往就越無趣!「無趣」簡直就是當今人世最大的「流行」了!怎麼樣才能減少一點「無趣」呢?我覺得或許「文學」能幫上一點忙!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文學一向「收視率」最低!純粹靠文學創作吃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不是肯定會餓死,就是只剩半條命連腳步都踏不穩!這——總算是個還算「有趣」的現象了!哀哉!哀哉!
「象徵主義」是人類文明的一扇窗,透過這扇窗,文學有了自我療癒的特質!創作者大可輕鬆地躺下身來仰望天際,不浪費力氣在大聲疾呼上,或許會讓飢餓的感覺好過一點吧?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