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6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劉墉那些吃苦也像享樂的心靈故事 作者:劉墉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96 |
散文 |
$ 221 |
現代散文 |
$ 221 |
散文 |
$ 221 |
現代散文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名人勵志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
豐沛感情敏感柔軟的少年心事,青春張揚的浪漫情懷,讀他的書如亭亭夏荷,淡淡吐露季節的芬芳。讓人心情跌宕的同時也能會心微笑。
全書共分四輯:〈紅塵〉、〈花魂〉、〈詩心〉、〈童趣〉。從兒時印情到成長生活點滴,回憶少時選擇繪畫之路到擠身暢銷作家,人生恍恍,轉眼成為人父甚至祖父,行文間一貫慧黠逗趣哲思,回盼過往,更多了對生命的豁達及自在。
劉墉每說一個故事,以圖佐文,梭織生命中的點點滴滴,跟著他走訪「紅塵」,沿途經過媽媽的四合院兒、龍山寺、瑠公圳、九份山城……心中一路綻放朵朵「花魂」,隨即跟著進入劉墉畫中的世界,又從畫中逛出來,來到他的童年,跟著他有笑有淚,笑中有真摰的感性,淚中有晶瑩的善美。
作者簡介
劉墉
畫家、作家。在世界各地舉行過三十多次個展,在兩岸出版文學著作、繪畫理論、工具書及畫冊一百餘種,被譯為英、韓、泰、越等各國文字。是一個以自由的心情在生活,認真的態度在學習的人。有一顆很熱的心用來體會,一對很冷的眼用來辨別、一雙很勤的手用來分享、兩條很忙的腿用來超越。
劉墉微博:
騰訊網:t.qq.com/liuy
新浪網:www.weibo.com/u/2203045151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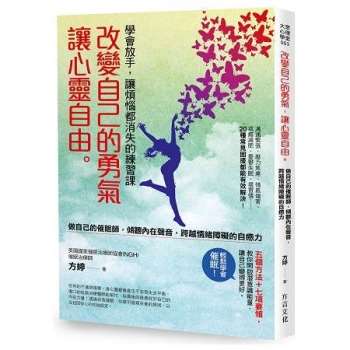










這本書看著看著,跟著劉墉的文字,我彷彿回到了小時候那遙遠又清晰的記憶中。 我哪兒是天才?我只是個愛說故事的藝術頑童。這句話完全道出劉墉的文字與畫。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這本書裡全是劉墉的故事,劉墉的文字是富於情感的,他的文字是有畫面的。他的文字在說故事,他的畫也在說故事,這些故事總是能牽引讀者的情感,讓讀者跟著他的故事一起笑一起哭。 原本聽見紅霞颱風要來的消息,沒想到颱風沒來,反而帶來了台灣最缺的雨水,真是令人高興啊!在這樣忽晴忽雨的天氣裡,拖著重感冒的身體,心卻沈浸在劉墉溫暖的文字裡。看著畫牡丹這篇,感受到父親疼愛兒子的深厚情感,不管孩子畫的如何,在父親眼中總是最美的,最棒的。劉墉父親想和同事炫耀的心情,讓我想到了我的父親,父親總愛提及我小時候的模樣,不管我歌唱的如何,舞跳的如何,都說是棒極了,那樣的心情應該和劉墉父親的心情是一樣的吧。 另一篇惹我跟著揪心的文章是父親的粥,文章提及劉墉小時侯在父親的病床前,吃著父親輕輕吹送入口的粥,而現在自己煮著粥,輕輕吹...一個已花甲的老孩子,居從這碗粥,想到五十七年前抱我的父親,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淌,淌在父親的粥裡...看到這裡,心重重的抽了一下,誰能不被這的情感打動呢? 這本書裡有劉墉的人生哲學與智慧,他的人生並不平順,有苦有甜有笑有淚,但總能看到他的豁達。書本最後有附上這本書的畫作解說,每一幅畫細細看,總能感受到其中的情感。書本裡還有許多感人的篇章無法一一細說,如果喜歡,你也可以翻開書本跟著劉墉的故事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感動。這本書看著看著,跟著劉墉的文字,我彷彿回到了小時候那遙遠又清晰的記憶中。 我哪兒是天才?我只是個愛說故事的藝術頑童。這句話完全道出劉墉的文字與畫。人生是小小又大大的一條河這本書裡全是劉墉的故事,劉墉的文字是富於情感的,他的文字是有畫面的。他的文字在說故事,他的畫也在說故事,這些故事總是能牽引讀者的情感,讓讀者跟著他的故事一起笑一起哭。 原本聽見紅霞颱風要來的消息,沒想到颱風沒來,反而帶來了台灣最缺的雨水,真是令人高興啊!在這樣忽晴忽雨的天氣裡,拖著重感冒的身體,心卻沈浸在劉墉溫暖的文字裡。看著畫牡丹這篇,感受到父親疼愛兒子的深厚情感,不管孩子畫的如何,在父親眼中總是最美的,最棒的。劉墉父親想和同事炫耀的心情,讓我想到了我的父親,父親總愛提及我小時候的模樣,不管我歌唱的如何,舞跳的如何,都說是棒極了,那樣的心情應該和劉墉父親的心情是一樣的吧。 另一篇惹我跟著揪心的文章是父親的粥,文章提及劉墉小時侯在父親的病床前,吃著父親輕輕吹送入口的粥,而現在自己煮著粥,輕輕吹...一個已花甲的老孩子,居從這碗粥,想到五十七年前抱我的父親,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淌,淌在父親的粥裡...看到這裡,心重重的抽了一下,誰能不被這的情感打動呢? 這本書裡有劉墉的人生哲學與智慧,他的人生並不平順,有苦有甜有笑有淚,但總能看到他的豁達。書本最後有附上這本書的畫作解說,每一幅畫細細看,總能感受到其中的情感。書本裡還有許多感人的篇章無法一一細說,如果喜歡,你也可以翻開書本跟著劉墉的故事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