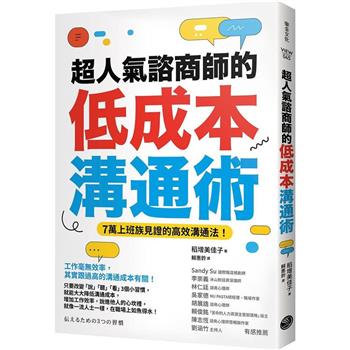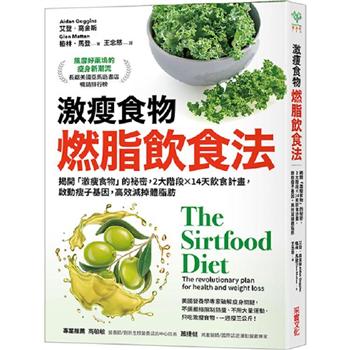三十三宮闕
1
烏雲壓城,寒風中透著血腥的氣息。我透過血汙,俯視著城頭之下零星走過的百姓,他們大多衣衫襤褸,臉上帶著和天氣一樣蕭索的神情。他們中沒有人肯抬一下頭,看一眼我高懸的頭顱。
他們是不在乎的,不在乎我的死。
我是元君曜,大肇的皇帝。我二十二歲那年登基,到現在已經十餘年了。這十餘年裡,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一個好皇帝,至少,我一直在為維護這個國家的南北統一做著努力。直到我的敵人砍下了我的頭顱,我才發現禍事是起於蕭牆之內。
我早已死去,身首異處,卻不知為什麼一直能看到眼前的一切。在北國初冬的寒冷中,我看到比天氣更冷的,是人心。
此地甚好!極目望去,向宮城,可以看到摘星閣那直插雲霄的飛簷,在蒼茫的天際上,投下一道尖銳的剪影。那裡是我的心痛之所在。愛之所忠,唯情而已。
現在,我的頭顱之下,是各種各樣的表情,但沒有哪一種比廣泛的漠視更刺傷的我心。
我至今方懂得悔悟,我走到今天這一步,是自己作的孽。可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看著,連唯一的期望也不能說出口——我希望看到一滴眼淚,一滴為我而流的眼淚。一代帝王的希望,一下子變得如此卑微。
他們原本說要讓我暴屍旬日,今天已經是第十一日了,可他們似乎早把我忘記了。
我想,不會有人來為我收屍,更不會有人為我流淚。
這才是我的悲哀:早已眾叛親離,而我自己還不知道。
這幾天我想了很多,他們在遺忘我,我卻忘不了他們。到了現在,我才真正看明白,這就是被全天下拋棄的痛苦。
我是個昏君,沒有人在乎。因為在所有人眼中,我元君曜也從沒有在乎過他們。我的眼裡只有我的淑妃馮嫣兒,為了她,我對不起天下人。
當然,馮嫣兒是不會為我流哪怕一滴眼淚的。因為,是她親手把一杯鉤吻端到我面前的。
鉤吻是毒酒,喝下去會肚腸盡爛。我只喝了一口,便痛得彎下腰去。
淑妃笑著,她的笑容一如以往的明媚。她說,這酒正適合我。那一刻我的心與肝腸絞在一起。
她知道我已經無力去提起我的劍,所以在我面前不用再裝下去。
「你快點。」她催促我,像是以往和我撒嬌的模樣,「我還急著出宮呢,我爹為我新打造了一張拔步螺鈿床,我得快點去看看。」她看我因疼痛縮成一團,還嫌我死得慢耽擱了她的好事。
而我,曾一直那麼愛她!
她這麼說的時候,她父親的學生,那個她帶進宮來的李逸,當著我的面,把她摟進了懷裡,「好狠!」他說。
淑妃咯咯地笑著,推了他一把。
而李逸的另一隻手上,提著一把打算殺我的刀。他是我新封的禁衛的統領,是淑妃引薦給我的人。
人人都說我元君曜刻薄少恩,他們說的也許是對的。我多疑不信任眾臣百姓,尤其不信任那些新近歸附的南人。可我信任我愛的淑妃,一點也沒有懷疑過她
就算我那統一了天下的父皇,在臨死前一再叮囑我,要對這個剛統一王朝的百姓寬柔並濟,要對南北的眾臣一視同仁。我也是左耳進,右耳出。所以到我死的那一天,連一個為我說話的人也沒有,更不要說為我出力,為我流淚。
我對不起他們。
可我對淑妃,卻是掏心掏肺的好。
淑妃長得漂亮自不必說,我第一眼看到她就喜歡得緊。那時我還只是皇子,為了得到她,我花了許多的心思,打敗了幾個兄弟。得到她,比得到天下還難。
她的美精緻如細瓷,光潔如玉潤。我一直把她小心地捧在手心裡。她的一顰一笑都讓我隨之心顫。我傻傻的愛過她,她的需要,我從來沒有想過違拗。馮嫣兒善舞,我便為她起了摘星閣,她便是想想要天上的星星,我也會想辦法去摘給她。看她如嫡仙般在高閣上舒起廣袖。我神魂顛倒,從沒想過她的笑臉下,正藏著對我食肉寢皮的狠心。
那時的她,時常在我面前撒嬌落淚,每一滴淚珠都好像砸我的心尖上一般。
我是這麼喜歡她!我一當上皇帝,就想把她立為皇后,可大肇的規矩,皇后必先有子這一條卻難住了我。馮嫣兒一直沒有為我生出個一男半女。
就算這樣,馮嫣兒也是我後宮地位最高的女人。有了她一個淑妃,我再也不把妃位封給其他女人,這樣才能讓她在後宮,就和當了皇后一樣。
別人都說君王無情,我卻發了誓要讓她三千寵愛集於一身。我夜夜與她歡好,恨不得與她合為一身,心肝二字來形容她真正是再貼切不過。我與她海誓山盟,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許了她生生世世永不分離,生同床,死同穴,我曾以為她會和我埋在一起。可如今,只有我的人頭掛在這裡。
因為她之故,我提拔重用了她的娘家。她的父親馮驥,先後封為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關內候。總領天下兵馬。她的兩個兄弟也都得了三品以上的高官,她的姐妹全封為夫人,連她家中的子侄弟子,我也全都給予冊封。
我靠著馮家,把那些不聽話的老臣全都收拾了一遍,尤其是那些新歸附的南臣,幾乎被我清洗一空。若不是他們實在根基深厚,大概會被我殺得一個不留。
我不知道,我這樣做的結果是:最後徹底失盡了人心。當馮驥騙我說南人謀反,調動我的兵符時,我還信以為真,被他們蒙在了鼓裡。沒有人告訴我實情,直到洛京周邊各城陷落,叛軍扣城門甚緊,我才從馮嫣兒的的溫柔鄉中張開了眼睛。
當我想調動人馬救駕之時,就算我親軍也推說糧草不濟,無力應戰。我向京中臣僚求告,一家家親自上門借錢。卻一家家的都吃了閉門羹。那時候我才知道我已經早沒君王的威嚴,到了走投無路境地。
想到這些,我想哭,可我這顆孤獨的頭顱已經沒有了眼淚。
我最終沒有去喝馮嫣兒手上剩下的鉤吻,至少,我還有自殺的勇氣。
我抓起了三尺白綾,一步步掙扎著走向御花園的煤山,那裡有一棵古槐斜斜的伸出的枝枒。以前我曾在樹下立過一個秋千架,馮嫣兒清脆的笑聲在樹下蕩漾。
可到了這時候,跟在我身後的只有一個小太監,我記得他名叫如意,是個南人。
他為已經沒了力氣的我在樹枝上掛起了白綾,同時在旁邊的樹上為他自己也掛了一個。我解散自己的頭髮,覆了自己的臉面,我無顏去見我的列祖列宗。
我靠著如意攙扶,把自己掛在了古槐之上,這是我為自己留下的最後一點尊嚴。
如意吊死在另一棵樹上,到了此時只有他一個人陪著我。
我聽到了哭嚎之聲,眼睜睜看到那些沒能逃走的妃嬪和我的兩個女兒被叛軍蹂躪。我一直沒有兒子,只有這兩個小女兒,我看到她們死不瞑目。
李逸跟了過來,命人解下了我的屍體,他們把我抬到了本來該由我來坐的朝堂之上。
我看到馮驥此時占了我的龍椅,大笑著問他的子侄該對我如何處置。
馮嫣兒,我曾經的淑妃,笑著推了李逸一把,李逸怕人與他搶功似的,一個箭步上來,揮刀割下了我的頭顱。
馮驥大笑,連說了三個「好」字,然後叫了一聲「逸兒」,說:「這龍椅終究是你的。」這是怎麼回事?
馮嫣兒嬌怯怯的倚在李逸身邊,眼裡終於有了點驚嚇的表情,可她說的是:終於熬到這一天了。還問她爹,她有什麼封賞?
原來她與我的每一天都是在受著煎熬,而我,一直以為她也愛我。
我早該死了。
我回想起,當初她把李逸引薦給我的情形,不知她何時生的異心,我對她那麼好,這是為什麼?
好在我只剩下了一顆頭顱,再也不會感到心痛。
我的頭顱被他們當成蹴鞠,踢了兩日後,覺得膩了,便被掛上了洛京城頭。城門之內,我頭一次仔細觀察到自己百姓的樣子。他們從我的頭顱之下經過,一個個面有菜色,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每日都有餓殍倒在我的頭顱之下。連吃飽都成了問題,難怪他們漠視了我的死亡。我懷著愧疚,希望他們快點把我忘掉。
這十幾年,我的眼裡心裡只有馮嫣兒一人,與她日日笙歌,夜夜歡好。從來沒有正眼看過我的百姓,也沒有想過他們的生活竟會困頓至此!我都幹了些什麼!
只因一個女人,我愧對我的百姓,愧對這江山天下。我錯了!悔之晚矣,只是,這話我再也沒法說出口來。
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重來,我想我是再也不會愛上任何一個人了。
鉛灰色的天空越來越低沉,北風夾著寒氣呼嘯著掃過城外望不到邊的衰草,十天了。我的頭顱一直高懸於洛京東面的建春門外,讓我看不到河水的浩浩蕩蕩。這是大肇的帝京,坐北朝南,本應該面向天下。
我這個昏君造了什麼孽,讓這塊土地和我的百姓落到了今天的境地。
寒霜在我的臉上凝結,北風如刀一般割著我的肌膚,我想,再也不會有人來理我了。我最後的結局大概也就是被棄屍荒野。不對,我身首異處,只剩下這一顆頭顱,還不夠野狗一頓飽餐。
細小的雪花從天上飄落,北風呼嘯著劃出滿地的蒼涼。繫著我頭顱的枷籠一晃一晃,我這縷死不瞑目的孤魂不知會漂向何方。
這樣也好,我沒有了心,再也不會去愛了。
「諸位軍爺,我給你們帶來了一壇村醪。」一個軟軟的聲音,在我的頭顱下響起。
我向下看了一眼,不由得大吃一驚。
2
在城門下,站了一個小小身影,身上過大的破棉襖,許多地方已經翻出了骯髒的花子。一根草繩馬馬虎虎的攔腰一繫,算是把這不成體統的衣裳穿到了身上。
她此時剛好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我認得她。她頂著難看腫脹的一張黃臉,臉頰上還有一道長長的疤痕。
楚司南!
我當然認得她!在第一次見到她時,就曾被她用這張腫臉所騙,這件事我一直記著,我怎麼可能不認得她呢!更何況,她臉上的疤痕還是我親手留下。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熟人了,此時看到她,我的心抽了一下,沒錯,是我的心,它好像回來了。
守衛的衛兵,一聽到有酒,全都從他們木板的房子裡跳了出來。
「妳是何人?」他們打量眼前這個小小的女人。
她沒有回答,指了指了破棉襖上貼的一塊白布,那上面有一個大大的「義」字。
「妳是義莊來的?」守衛問她。
她點點頭,「來收屍。」順便指了指身後的板車。她拉來了一輛板車,破草蓆下應該是我的屍體。難怪我的心又開始疼了。
我以為我的屍體早就被野狗吃掉了,沒想到居然在她這裡。可是她……
「哦,那我們也可以回去了。」守衛的士兵十分高興,相信了她的話。他們居然沒有人懷疑一下,她那軟軟的南音雅言,怎麼可能是義莊裡的義工。
有人爬上城頭,解下了我的頭顱,丟在她的板車上。「快走吧。」他們都急著鑽回板屋取暖喝酒,沒有人在乎她會把我帶到哪裡。
而我自己也已經不在乎了。只是她……
板車吱吱的響了起來,向著城外的方向。雪下得大了,鋪天蓋地遮去了一切骯髒和醜陋。她頂著風雪,躬起了脊背,艱難的拉著板車。看她的背影,在寬大的破襖下,支支稜稜的突起,這讓我想起她的身體是多麼細瘦。她連聲咳嗽著。每邁出一步,都夾雜著沉重的喘息。
我想起來了,她被我關在冷宮中十餘年,身體越來越壞,近幾年,每年見她,都咳得厲害。只是我從來沒問過她得的是什麼病。只奇怪她病了這麼久,居然沒有死。
我死的那一天,打開了宮門,讓我的嬪妃們都盡可能逃離。當然,我知道,她們中的許多人若是不依附於馮家,其實也無處逃生,走到哪裡都是死路一條。可就在那同時,我也下了死命令,要處死楚司南。我記得,我就在喝下馮嫣兒的毒酒之前,還想過親自殺死這個妖女洩憤。因為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起兵造反的,是那些不肯歸化,死不馴服的南人。
而楚司南,是南楚唯一的公主,楚烈帝的女兒,楚獻帝的侄女。我父皇封她為南鄉公主。
她是我的修容。一個不上不下的封號。
她走的路越來越荒涼,我不知道她拉著我,這是要到哪裡去。雪下得深了,路不好走,她又瘦得可憐,每向前一步,都得奮力掙扎很久。頭一次,我深恨自己竟長得如此高大,讓她為此受累了。
我呆呆的看著她的背影。覺得我好像從來都不認識她。
我是因為娶了她才得到帝位的。
我不知道那是父皇的一個測試。那是一個中秋的家宴,父皇居然請了楚獻帝帶著家人一起參加。當然。那時的楚獻帝已經新封了歸命侯。早已向我大肇投誠。他們一家人在我父皇的威勢下,連頭也不敢抬。
我對楚獻帝一家沒有興趣,我新娶了馮嫣兒,一心只盼著宴會早點結束,好早早和馮嫣兒共赴巫山。
這時,父皇說,他要為楚司南選一個夫婿,而這個夫婿就在我們兄弟之中。
我這才看了一眼楚司南,她那天就是頂著和今天一樣腫脹難看的面皮,睜著一雙好奇的大眼,把我們幾個皇子全都打量了遍。
我本來覺得這不關我的事,可別的兄弟都不作聲,我為了盡早結束這宴會,居然鬼使神差的說,我娶她好了。
我真的娶了南鄉公主,結果父皇將帝位給了我。他說因為我有遠見!統一的王朝需要一個有遠見的帝王。我與二哥拚英勇殺敵的戰功,與九弟比機智聰慧,最後全都比不上娶一個楚司南來得立竿見影。
板車在一處山腳停了下來,這裡荒無人煙,只有山風呼嘯著吹過,捲起了雪花,露出一大片堅硬的凍土。
我看到凍土地上有一個已經挖好的深坑。坑足夠大,應該能夠裝下我這高大的身軀。只是如此堅硬的土地,不知細瘦的她,挖了多久才挖出這樣的規模。
楚司南咳嗽著,喘息了一陣,回過頭來看我了。
她的眼睛還是那麼亮,和她現在的腫臉不相配。這不是她本來的面貌,她本來的面貌是一張娟秀粉白、有些孩子氣的臉。她在嫁給我幾天後,臉上腫脹消去,露出她本來的面目。我才發現,她是故意把自己弄成那醜樣,想躲過我們元家兄弟的覬覦。
我很生氣。
那時我已經聽許多人說南人狡黠奸詐,果然如此。雖然她解釋這是用藥水洗臉的緣故,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可我還是決定再也不要看到她。
當然,那時,我已經有了馮嫣兒,覺得一切很滿足了。
我從來沒有喜歡過她。欺騙,這正好是個藉口,我把她扔到了一邊,先是王府的舊屋,後來是皇宮破敗的冷宮。
為了表面好看,該給她的封號,我一個沒少給她。可她本人,卻一直是我的眼中刺。我只希望,不用我下手,她自己死掉最好。
她向我走了過來。把手攏在口邊哈著氣,因為冷,她鬢邊的髮絲結了霜,連睫毛也變成了白色的蝶翅。
然後,她捧起了我的頭顱。她的手心比我的肌膚要暖和一些。她用修長的手指拂開我散亂的長髮,我這被許多人糟蹋過的頭顱,又已經在城頭凍了十天,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認出我來。
她怔怔的看著我,「你本來那麼驕傲。」她說,長長的呼出一口氣來。
她臉上長長的傷疤抽動起來,好久才平靜了下來。
我的心也抽動了起來,這條疤,是我留給她的。只是因為她不肯向我解釋她那塊玉珮的由來,那塊玉珮,太過神祕,讓我不得不對她生疑。
我這一生,和她沒說過幾句話,從來也沒有好好與她談過心。她對我也一樣。
她用一塊巾帕,沾了些雪來細心的擦洗我的面頰。我看著她,心裡有了一點渴望。
我們幾次不多的相處,全是在衝突中經過。無論她做了什麼,我全認為是她的錯,有時氣急,便管不住自己。
不知她還記不記得我做的那些對不起她的事。
她把我的頭顱與身體對接了起來。然後,她從懷裡掏出了針線。她纖細的手指拈起針來,動作靈巧的飛針走線。我的頸上皮膚感覺到了一陣刺痛。
我都快記不起有多少次想置她於死地,若不是我的父皇生前一再告誡我,這位南鄉公主在南楚的聲望,甚至要超過她的叔父,我肯定早就對她下手了。就算這樣,我還是好幾次傷了她。
我對馮嫣兒可是從來沒動過一指頭。
風聲在我耳邊叫囂,卻蓋不過她溫聲的一句:「有點疼,你忍一忍,很快就好了。」我覺得我的心臟突然被一雙小手緊緊的握住了。
在我的記憶裡,我對她一點也不好,甚至親自動手打過她好幾次。她一定會記得疼。
「我不忍心看你身首異處。」她說,嘴角浮起一抹淡笑,「這樣做,也是因為我還欠著你一個情,謝謝你對我小弟弟的不殺之恩。」
我想了起來,她有一個小弟弟,她父親死時,尚在襁褓之中,由她一人撫養長大。她的叔父登基為帝,又降了大肇,她也就帶著她的弟弟一起來了大肇。她嫁給我時,她的弟弟已經八歲。本來,我想把那孩子和歸命侯的兒子一起,找個事由一併殺掉。但後來心軟,只是將他發配北方苦寒之地了事。這也許算我這一生做得不多的幾件好事之一,沒想到卻在此時得到了回報。
終於,她把我的頭顱和身體縫在了一起。她直起腰來,看著我,淡淡的笑容化成了悲憫。
「你活該!」她說,「我葬了你的骨,還了你的恩,從此我們兩不相欠。你我本無緣,來世你若有福,希望你不要再做皇帝,也希望你我從此陌路,我與你生生世世成永絕,再無相見。」一滴淚落了下來,滴在了我的眼中。
她的身影變得模糊,她的聲音化在了寒冷的風中。我的眼睛疼,一路疼下去,一直到心,我的心抽搐著,痛徹骨髓。我錯了,我知道自己錯了,錯得離譜,錯得不可原諒。
阿南!我突然想起了她的小名,她曾對著牆避,以為我不在的時候,悄聲對自己說話:阿南不害怕,阿南要堅持。
我記得,那是在我用玉鎮紙打破了她的額頭之後。那時的她,沒有哭。
阿南!阿南!阿南!
在這寒冷的冬天,突然有一道陽光直直的打在我的身上,我的身體變得輕盈,溫暖的空氣包圍了我,我僵硬的身體開始一點點的融化,帶來刺痛的感覺。就如同她還在用針戳我。我想我真的要死了,死在一個我從來都沒好好認識的女人身邊。
阿南!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三十三宮闕(上)的圖書 |
 |
三十三宮闕(上) 作者:鄭良霄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三十三宮闕(上)
.晉江原創網破千萬積分,《廚娘王妃升職記》、《風起長安》知名作者
.帝王視角宮鬥重生愛情小說
.收錄特別加筆大結局、出書限定番外篇
她忍辱負重,以公主之尊扮醜嫁給敵朝天子
她不是不會宮鬥,是不屑宮鬥
以為將在冷宮終老,昏君卻驟然轉性
認真的模樣,她還真的有些不習慣……
我是一代昏君,被寵妃和親信聯手狠狠背叛,頭顱被掛上城頭。
風雪之中,敢來送我一程,細心縫合我屍身的人,竟是冷宮的阿南。
昏庸一世,我傷害她、冷落她,多次想置她於死地,最後卻只有她陪在我身邊。
既然因她而重生,我就只對她一個人好。
剷除外戚、疏遠寵妃、裝傻布局等待仇人現身,若棋差一步,便又是粉身碎骨。
這輩子,我心中的皇后非阿南莫屬。
咦,只是這個小阿南,竟敢擺臉色給我看,不但不信任我,還等著看好戲?
作者簡介:
鄭良霄
女,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
生於新疆,祖籍江蘇,現居浙江,一直弄不清自己算是哪裡人。
學的是中文系,工作是工業類,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特長。
年紀老大不小,事業從來沒有,愛情更是從來沒弄懂過。
愛讀書,不求甚解,只留下幾書櫃的書;愛旅行,雁過無痕。連照片都沒留下幾張。
以前寫過些零碎的小文章發表於報刊,仔細想來,不值一提。
到目前為止,所出作品不多,我寫小說只能算是新手上路。謝謝大家支持!
章節試閱
三十三宮闕
1
烏雲壓城,寒風中透著血腥的氣息。我透過血汙,俯視著城頭之下零星走過的百姓,他們大多衣衫襤褸,臉上帶著和天氣一樣蕭索的神情。他們中沒有人肯抬一下頭,看一眼我高懸的頭顱。
他們是不在乎的,不在乎我的死。
我是元君曜,大肇的皇帝。我二十二歲那年登基,到現在已經十餘年了。這十餘年裡,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一個好皇帝,至少,我一直在為維護這個國家的南北統一做著努力。直到我的敵人砍下了我的頭顱,我才發現禍事是起於蕭牆之內。
我早已死去,身首異處,卻不知為什麼一直能看到眼前的一切。在北國初冬的寒冷...
1
烏雲壓城,寒風中透著血腥的氣息。我透過血汙,俯視著城頭之下零星走過的百姓,他們大多衣衫襤褸,臉上帶著和天氣一樣蕭索的神情。他們中沒有人肯抬一下頭,看一眼我高懸的頭顱。
他們是不在乎的,不在乎我的死。
我是元君曜,大肇的皇帝。我二十二歲那年登基,到現在已經十餘年了。這十餘年裡,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一個好皇帝,至少,我一直在為維護這個國家的南北統一做著努力。直到我的敵人砍下了我的頭顱,我才發現禍事是起於蕭牆之內。
我早已死去,身首異處,卻不知為什麼一直能看到眼前的一切。在北國初冬的寒冷...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三十三宮闕
番外、司南
三十三宮闕
番外、司南
商品資料
- 作者: 鄭良霄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10 ISBN/ISSN:978986323116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48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