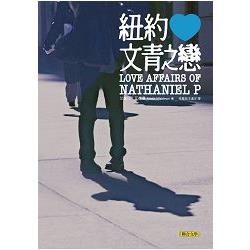圖書名稱:紐約文青之戀The Love Affairs of Nathaniel P.
被喻為當代珍.奧斯汀的艾黛兒.瓦德曼
寫給這都會裡,每一個在愛情中迷惘的男人和受過傷的女人
◆時下兩性關係最佳寫照,紐約藝文媒體圈,人手一本的話題之作
◆美國《紐約時報》編輯選書/《華盛頓郵報》極具影響力之書
紐約新銳作家奈特.派溫,在經過幾年掙扎窮苦日子後,如今擁有知名雜誌社工作,前途一片看好,愛情事業兩得意。遊走在諸多女性友人中──除了當紅商業記者女友的茱麗葉、與美麗的前女友艾莉莎兩人仍然維持好朋友關係,以及朋友圈公認聰明優秀、總是能成為話題中心的漢娜。
艾黛兒.瓦德曼替每個搞不懂男人的人,深入剖析一個帶有缺陷、時而易怒的都會型男:有一定教育水準、心思複雜、有些才華有些自負;受不了膚淺評論,對生活有一定的標準和要求,周遭朋友包括交往對象大都如此。細微處總流露體貼和細心、追求目標卻不時對自身定位迷惘焦慮。這樣的男人對不少女人極具吸引力,卻也因反覆無常的態度,讓她們一再失望。艾黛兒帶領讀者一窺都會男子的內心世界──工作、性與愛以及男女關係。
得獎紀錄
★美國《紐約客》、《經濟學人》、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國家公共廣播新氣象網路電視台《新共和》、《石板》、《國家週刊》、《THE DAILY BEAST》、《衛報》、《柯夢波丹》、《ELLE》、《BOOKFORUM》加拿大《國家郵報》選為2013年度好書
★美國《紐約時報》編輯選書
★美國《華盛頓郵報》評為極具影響力之書
★美國巴諾書店評選新一代潛力作家
★旋即譯成俄文、法文、西文、義文、荷蘭文等多國語言
作者簡介:
艾黛兒.瓦德曼Adelle Waldman
曾任《紐黑文報》(New Haven Register)和《克里夫蘭實話報》(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記者。她的文章作品散見於《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網路雜誌Slate.com,以及《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其他公部門出版品。她和丈夫現居紐約布魯克林區。
本書為她聰慧出眾的首發之作,吸引大家進入時下美國紐約布魯克林藝文小圈圈。但其中的令人著迷之處,來自於男主角奈特那一般男性矛盾卻又自戀的內心真實世界,被評為出版當年,刻畫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說角色。
譯者簡介:
侯嘉鈺
輔仁大學經濟系學士,英國新堡大學筆譯碩士。譯有《禁忌祈禱書》、《偷來的幸福》、《三種力量》、《把人生變動詞》、《居家生活法寶》、《清掃魔》、《消滅所有死亡跡象的神秘藝術》、《明智的冒險吧》等書。譯文指教:jadehou1980@gmail.com
王遠洋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現為獨立譯者,譯有2013女性影展《真實之美:探索愛麗絲沃克》、2014高雄電影節《在土星的光環下:蘇珊桑塔格》等多部紀錄片字幕。吳爾芙有自己的房間;他有信使譯站。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雖然他和艾莉莎已經分手一年多,她位在重劃中布魯克林綠點區(Greenpoint)排屋的頂樓公寓仍舊讓內特感到熟悉,有如自己的公寓那樣。
在她搬進來以前,這間公寓的磚牆塗上了灰泥,且覆有花樣的壁紙,木質厚實且不規則的的地楞橫梁則藏在地毯之下。艾莉莎的房東,小喬(Joe Jr.)曾給內特和艾莉莎看過照片。在經過二十年後,這房子年長的波蘭屋主搬出去和紐澤西(New Jersey)的女兒同住。小喬便拿掉地毯,刮除外牆的灰泥。這間房子是他父親老喬(Joe Sr.)是在一九四○年代左右所買下,從那之後他就搬到佛羅里達定居。一得知他這麼做,老喬說他瘋了,他認為加裝洗碗機或把舊浴缸替換掉才是較妥善的投資方式。「但我告訴他,那對吸引高水準的房客是行不通的。」有天下午,小喬在修補幾塊浴室的磁磚時,這麼對內特和艾莉莎解釋著。「我告訴他,花上大把銀子的那種人對於四爪古典浴缸(clawfoot tub)可是為之瘋狂,我還告訴他那是品味的問題。」小喬把臉轉向他倆,一桶塗料就這麼掛在他肉肉的指頭上。「你們覺得我這樣是對還錯?」他高興的問著,臉上綻放著笑容。內特和艾莉莎手牽著手,不自在的點了點頭,對於被人公開且適當的刻劃成某種傻子,他們不確定怎麼回應比較妥當。
內特協助艾莉莎在兩面無磚牆漆上了米色,與她沙發下深色的磚頭與奶油色的地毯正好形成對比。他們一起在宜家(Ikea)買了餐桌,但餐椅和門邊的長型櫥櫃是他祖父母(或是曾祖父母?)的,她的書櫥則已快達天花板了。
對他來說,如今這間公寓的熟悉感讓他感到有點羞恥。艾莉莎堅持他今晚要來。「若我們真的還是朋友,我為何不能邀你過來跟幾個朋友一起晚餐?」她這麼問過。那他能說甚麼呢?
內特的朋友傑森(Jason)是位雜誌編輯,讓內特又生氣又好笑的是,他一直想跟艾莉莎上床,而他就這麼像天皇老子那樣靠在沙發上,用雙手手掌輕輕抱著後腦勺,雙腳膝蓋張得超開,彷彿正試著把自己給鑽進艾莉莎的家具裡那樣。傑森的身旁坐著奧利特(Aurit),他是內特的另一個好友,最近他剛自歐洲海外研究歸國。奧利特正在跟一個名叫漢娜(Hannah)的女生聊天,漢娜是一名作家,內特常遇到她,除了輪廓看起來特別有稜有角之外,她長得漂亮,身材苗條,就連胸部也是小而美。大家幾乎公認她人好又漂亮,或者說漂亮人又好。坐在雙人沙發上的則是艾莉莎從大學所認識的女子。內特記不得她的名字,而且他們見過太多次面,他連問都不想問了,只知道她是一名律師,而那個下顎後縮,身穿套裝,手臂就垂落在她肩上的人,想必就是她超想委身下嫁的銀行員。
「我們一直在想,你何時要帶我們蒞臨你公司參觀參觀。」傑森這麼說時,內特的雙腳正踏進門。他把側背的郵差包放在地上。「我在路上遇到了麻煩。」
「在G線上嗎?」奧利特帶著同情語氣問道。
接著眾人一陣低聲交談,一致同意G線可是紐約的地鐵中最信不過的。
內特找了唯一的空位坐下,就在艾莉莎的大學同學旁邊。
「很開心見到你,」他盡可能帶著親切的語氣說,「好一陣子沒見了。」
他與她平視著。「之前你還在跟艾莉莎交往。」
內特認為他察覺到了她語氣中的控訴,有如在說「後來你全然踐踏她的自尊而且毀了她的幸福。」
他逼自己保持笑容。「不論如何,真的過了超久的。」
內特向她銀行員的男友自我介紹,試著和那傢伙搭上話。要是他叫得出她的名字,內特至少能夠別那麼焦慮,但這個前公子哥兒卻大多讓她替他回答問題(管理顧問研究員,美國銀行,前美林證券營業員,現面臨轉職壓力)。他傾向的溝通方式似乎是啥都不說,就只固定微笑,而且像個老爸那樣慈愛善意的點點頭。
很快的──雖說好像不夠快──艾莉莎把大夥兒都叫到擺滿碗盤的餐桌。
「全部都看起來好好吃喔。」當大家圍著餐桌、一臉喜悅的朝著彼此和擺設微笑時,某人這麼說。艾莉莎從房間的另一邊回來,拿著一只奶油盤。她把飯廳瞄過最後一遍,皺著眉頭。就在她優雅的坐下且黃色布料的波浪裙襬擺動時,她嘴裡發出了一陣得意的輕嘆。
「大夥兒開動吧,」她說著,自己卻動也不動。「雞肉都要涼啦。」
當他吃著自己的義式紅醬番茄燉雞(chicken cacciator)──一如往常美味──內特仔細看起艾莉莎心型般的臉龐:那雙清澈的雙眼和戲劇般的顴骨,漂亮的弓形唇,還有一大排潔白的牙齒。每次內特看到她,艾莉莎的美貌總有如初見讓他驚艷,彷彿他倆分手的這段期間,她痛苦得肝腸寸斷,進而扭曲了記憶中她實際的樣貌。在他心中,她過去揹負起了不幸之人的角色,而當她把門打開,赫然冒出一副容光煥發、健康逼人的模樣,他不禁吃了一驚。內特曾判斷過,她美貌的力量,乃是來自她能不斷重建的能力。當他覺得自己已解釋過這過往的事實──也就是她是個美女──並把這擱置一旁,她不是別過頭去,就是咬了咬唇,然後像個你搖晃著想重新啟動的兒童玩具,她的美麗變了樣,搭配的服裝也有所不同:如今她微彎的眉毛,光亮的顴骨和害羞微笑的雙唇,都讓她的整體輪廓看起來優雅動人,閃閃發光。
「大美女艾莉莎,」當她在門口擁抱他,她咧嘴一笑,輕描淡寫的略過他遲到一事,內特不假思索這麼說著。
但經過半晌,他也就適應了。漢娜(Hannah)評論起她的公寓,「我討厭這間公寓,」艾莉莎回答,「地方小,格局糟,就連設備也廉價到不行。」然後她笑了笑,好像在說「但還是很感謝你。」
艾莉沙發出的牢騷聲如此熟悉,有如暗示著內特,讓他再次感受起同樣熟悉的內疚、惋惜、害怕與淡淡的煩躁──這些顯示她甚為嬌寵、脾氣不好的特質。她的美麗帶來刺激,有如希臘神話中海之女神卡呂普索(Calypso)所施展的魔法再次誘惑他,引他落入陷阱。
此外,當內特叉起雞肉,他注意到艾莉莎鼻上的毛孔還有額上靠近髮線一點點的粉刺,這些缺陷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在多數女人身上注意到這些似乎顯得吹毛求疵,不像紳士。
但艾莉莎的美麗似乎就是要讓她在某種堪稱奧林匹克水準的百分百美女競賽中,接受人們的品頭論足。這些不完美似乎違反常理,像是她這部分意志或評斷的敗筆。
「你最近忙些甚麼?」她問起他,這時大夥兒盛裝馬鈴薯已經進入第二輪。內特用餐巾輕拍擦了擦嘴巴。「忙一篇論文而已。」
艾莉莎圓溜溜的雙眼和抬起的頭似乎在懇求他說詳細一點。
「是研究一種身為精英的特權,也就是我們把剝削的行為交由外界處理。」他說,瞄了一眼坐在他斜對角的傑森。
這篇論文的概念有點模糊,內特也怕人家聽起來會以為對於較大或嚴肅的主題,他就像在二十幾歲出頭還沒學會野心勃勃的進行寫作那樣,太過天真且不切實際。那是一本特定給寫作已達那種水準的人所投稿的雜誌。但他最近寫起了一本書,也獲得了重大進展。即便還要好幾個月才會出版,這本書已經小有名氣。要是他沒寫這本書,他投稿的進度就會快多了。
「基於道德感,有些事情我們自己臉皮太薄做不來,而讓別人去做。」內特信誓旦旦的說。「良心是最終的奢侈品。」
「你的意思是幾乎整個勞工階層都去從軍這類的嗎?」傑森說,聲音大到其他的對話全部中止。他從厚木板製成的檯子上拿了一片法國麵包。「可以給我奶油嗎?」他問完漢娜,才一臉期待的轉回內特那邊。
傑森抹上油亮的護髮霜才把捲髮壓實。
他擁有邪惡天使的那一面。
「我不是指這個。」內特說,「我是指──」
「內特,我想你說的對極了。」奧利特插話道,有如指揮棒那般揮動著叉子。「我覺得普遍來說,美國人很難體會捍衛所謂的正常生活而牽涉到的醜陋與不幸。」
「當然,那是以色列人的觀點啦──」傑森起了個頭。
「傑森,這麼說很失禮耶,」奧利特說,「這不但太過簡化,還帶有種族歧視。」
「是很失禮沒錯,」內特同意說,「但與其關注日常生活的安全議題,對於我們自我保護,不讓自己感到像是周遭經濟剝削的共犯,也就是取得所有的食物,我還比較來得有興趣。你在那裡逛街所支付的一半金額,也就是正在享受感受血統純正的特權。」 他把酒杯放在桌上,開始用手臂做起姿勢。「不然想想那個房東付錢給他,請他每周把垃圾放在我們大樓前面兩次的墨西哥人好了。我們不會自己剝削他,但就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清楚這傢伙是個甚至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到的非法移民。」
「小喬倒垃圾可是自己來。」艾莉莎說,「但他是真的很小氣。」
「『種族主義者』跟『種族歧視者』有甚麼區別嗎?」艾莉莎的大學朋友問。
「這對幫我們外送比薩跟替我們做三明治的傢伙來說是一樣的。」
內特繼續說,他知道自己正在觸犯晚餐派對禮儀中的潛規則,也就是談話內容應該是表面說說、重點大家開心就好的那種。一個人不該一古腦兒專注在剛剛說了甚麼。但在那個時刻,內特才不在乎呢。「我們不會自己剝削他們,」他說,「不會,我們會雇用某人,一個中間人,通常是一間小公司的老闆來做這種事,所以我們不必感到難過。但我們還是利用了他們的廉價勞工,甚至在我們閒扯美國所標榜的自由主義時──英國的新政策 (New Deal)有多好,每日工作八小時還擬定最低工資──也不例外。理論上,我們唯一會抱怨的就是政府做得還不夠。」
「內特,不好意思,」奧利特舉起了一個空酒瓶,「我們再開一瓶如何?」
「小喬可沒雇個墨西哥人來替他整修,」艾莉莎帶著微醺,以善解人意的嗓音說著,同時走向門邊的櫥櫃。櫥櫃上放著幾個酒瓶,瓶頸還從色彩鮮豔的塑膠袋戳了出來。這些酒當然是其他客人帶來的。內特認出了「葡萄藤」(Tangled Vine)萊姆綠的包裝,那是他家附近唯一的酒行。這似乎讓原本就失敗的他顯得更失敗了。
他原本打算在來的路中帶個一瓶。
艾莉莎選了瓶紅酒,然後回到座位。「有誰來開?」她問完才轉向內特。「內特,不好意思,繼續說吧。」
內特已經忘記剛剛的論點說到哪。
漢娜從艾莉莎的手中接過酒瓶。「你剛剛說大家都透過剝削他人得到好處,但卻假裝自己是清白的,」她幫腔說著,同時艾莉莎遞給了她一只髒兮兮的銅製螺旋開瓶器,那只開瓶器已經老到足以和「前往西部拓荒的路易斯與克拉克」桌上遊戲(Lewis & Clark)媲美了──那無疑也是艾莉莎的「傳家寶」之一。
「我覺得──」漢娜準備開始說。
「對,」內特說。「對。」
霎那間,他又想起剛剛的論點了。「你知道自己是怎麼解讀狄更斯的小說中那些八歲就在工廠工作或者流浪街頭的男孩嗎?然後你很納悶怎麼沒有半個人伸出援手?這麼說吧,大家都一樣。我們只是比較擅長隱瞞這個事實,尤其是向我們自己隱瞞。至少那時的人藉由承認看不起窮人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傑森對銀行員說,「想必你已經注意到了吧,這裡的小內特正為『自由內疚特急症』所苦。」
傑森目前正在進行一篇肥胖傳染病的文章,篇名即將命名為「別讓他們吃蛋糕」(Don’t Let Them Eat Cake)。
在內特未能反應之前,漢娜轉向了他。她正單手抱著那只酒瓶,並用起另一隻手小心翼翼扭動著那只可笑的開罐器。「當人們在逛有機超市『純粹』時,他們自願多付一點,就你的邏輯,他們不就是要試著負起責任嗎?」她問,「他們不就是多付一點,才不致於剝削到廉價勞工?」
「沒錯,」內特讚賞的說道。(似乎真的有人在聽他說甚麼)「但那些標示的價格真的有讓超市股東以外的人受惠嗎?」那些股東所該做的,就是在麥片的盒子放上某張拉子真摯的情侶照,然後我們就會認為那項產品是來自某個自由戀愛工人的天堂。」這麼想對我們自己有利,因為這讓我們買到方便,就像我們買到其他所有東西那樣,」他停頓片刻才做出結論,「基本上這是馬克思的論點,也就是資本主義下剝削所導致的殘酷。」
奧利特皺眉,「內特,這篇論文是要給誰看的?」
「我還不知道,」內特說,「在我擔心起這對拓展我的事業有沒有幫助之前,我想先寫。」
奧利特用那種醫生他研究懷疑是惡性腫瘤的眼神仔細端詳著他。「還有,去逛『應有盡有』的人不就是因為那邊食物比較健康嗎?」
當漢娜拔出軟木,酒瓶冒出酒來嘶嘶作響。
「我覺得你的點子聽起來很有趣。」艾莉莎說。
內特認為,艾莉莎對自己超好,甚至可以說是超乎常態。或許真如她說過的,他倆之間還有可能?
「我也覺得這聽起很有趣。」有對情侶中的男方這麼說,他現在也忘了他叫「凱文」(Kevin)還是「迪文」(Devon),但內特是在酒竄流得更誇張時才注意到他發出聲音、說起話來。「我已經很久沒聽別人說起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還覺得這是好的。」他說,同時艾莉莎再次「醒起」他的酒杯。「從大學之後就沒有過了。」
內特用手肘把自己的酒杯頂到艾莉莎看得見的地方。
當她酙著酒,椅腳磨擦著地板,冰塊撞擊著臼齒,銀器也碰撞著碟子。
內特瞄了一眼艾莉莎書架上的書。她所蒐集的書不失正經又富有品味,女性文學跟女性雜誌她則一直放在臥室裡。
「所以,『種族主義者』跟『種族歧視者』究竟有甚麼區別?」凱文(迪文)的女友最後問道。
「『種族主義者』,」奧利特開始興致勃勃的說,「是指並未那麼厭惡或偏頗一個族群,而是…」
「嘿,猜猜我聽說誰拿到了價值四百美元的預付版稅?」傑森打斷。基於對奧利特的禮貌,沒人回應他的話。
「──個人特質的起始,」奧利特直盯著傑森看,「或是一個人在身為種族成員──」
「是葛莉兒‧可漢(Greer Cohen)。」傑森把剛剛的話題說完。
「所秉持的信念。」奧利特最後這幾個字顯得孤立無援。當她聽到葛莉兒的名字時,他不以為然扮了個鬼臉。甚至今晚突然覺得內特人又好又聰明的漢娜也挑了挑眉。
「這對葛莉兒很好啊。」艾莉莎說,有如電影《超完美嬌妻》取名「史坦佛社區」中某個即使對於沒來的客人也一樣保持有禮的女主人。
「誰是葛莉兒‧可漢?」
「算是個作家吧。」奧利特對凱文(迪文)和他的律師朋
第一章
雖然他和艾莉莎已經分手一年多,她位在重劃中布魯克林綠點區(Greenpoint)排屋的頂樓公寓仍舊讓內特感到熟悉,有如自己的公寓那樣。
在她搬進來以前,這間公寓的磚牆塗上了灰泥,且覆有花樣的壁紙,木質厚實且不規則的的地楞橫梁則藏在地毯之下。艾莉莎的房東,小喬(Joe Jr.)曾給內特和艾莉莎看過照片。在經過二十年後,這房子年長的波蘭屋主搬出去和紐澤西(New Jersey)的女兒同住。小喬便拿掉地毯,刮除外牆的灰泥。這間房子是他父親老喬(Joe Sr.)是在一九四○年代左右所買下,從那之後他就搬到佛羅里達定居。一得知他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