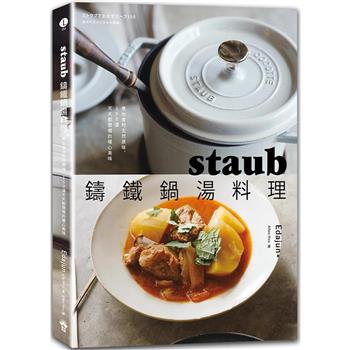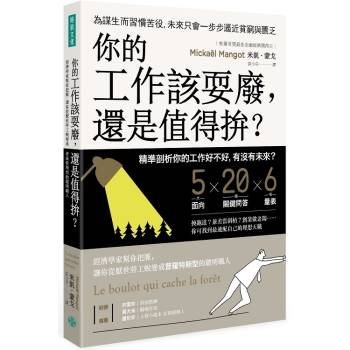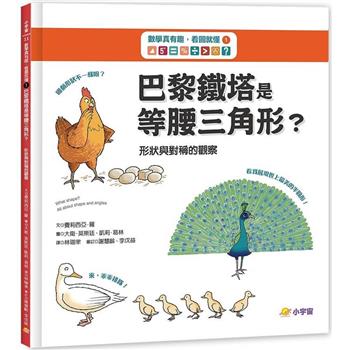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影響《百年孤寂》的時代經典,繁體中文版首譯
★Modern Library二十世紀百大英語小說、時代雜誌最具影響力百大英語小說
《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為美國文學大師威廉.福克納於193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亦屬作家有關美國南方的時代書寫,在其約克納帕塔法系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故事背景設定於三○年代美國南方,仍奉行禁酒令和種族隔離的時代。敘述情節主要分兩主線,一條是關於白人女孩莉娜.葛洛夫,懷著身孕千里迢迢從阿拉巴馬州到約克納帕塔法郡的傑弗森小鎮尋找情人,堅信情人承諾的她,沿途雖有不少善意的幫助,卻遭無情背叛而得面對未來的不知所措。一條是關於喬.聖誕的坎坷境遇:自幼父母雙亡的他,被懷疑有黑人血統而受迫離開自幼棲身的孤兒院,後被農場主收養卻仍遭受迫害,命運多舛。敘述主軸雖按時空順序,但也常夾雜倒敘回憶、內心獨白、多方敘事觀點;大量文學手法的靈活運用,卻充滿新意、富實驗性的作品。
書中描寫不過十天的光景,過往記憶和內心情感穿插其中,人物的性格塑造、處處具隱喻、象徵的段落和對於時情世態的描寫,透過苦痛憂怨的書寫,體現那深埋人類心靈深處、亙古不變的真實情感,也反省了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議題。福克納也藉此書揭示了種族主義偏見對人心的影響和腐蝕已久。時至今日,種族偏見與性別歧視仍潛藏在每個人的內心。當年出版後甫獲《星期六論壇報》、《時代》雜誌、《紐約先驅論壇報》等各媒體和文化評論界等正面好評。除了承襲作者昔作的史觀,卻也展現更寬廣的視界,在種族議題的探討更於當時開創了新的深度。
當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感言致詞時,他曾說:
唯有從人類心靈的掙扎中,才能創作出好作品。因為,只有心靈的掙扎、衝突,才值得作家去寫,才值得作家去憂心、傷神。……作家的責任便藉著提升人類的心靈,藉著提醒人類勇氣、榮譽、希望、尊嚴、同情和憐憫等過往的榮譽……成為幫助人類綿延下去和戰勝一切的支柱和棟樑。
作者簡介: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現代主義文學巨擘、美國南方書寫傳奇,小說家兼詩人和劇作家,為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意識流文學手法的代表作家。出生於美國南方密西西比州的新奧爾巴尼,幼時即隨家人遷至牛津,從小愛好閱讀,卻沒受過太多正規教育。少時曾加入皇家空軍,也曾遊歷歐洲。身處美國南方社會劇烈變革時代的他,透過大量閱讀而接觸當代和歷史上各種文化思潮,自二○年代始,陸續出版其創作。起初迴響不大,直到一九二九年出版了代表作《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聲名大噪。由於其成長背景,許多作品皆圍繞著美國南方,更創造出一座南方州郡——約克納帕塔法(Yoknapatawpha),許多作品的故事情節就發生在此,而筆下人物也常重複出現在不同作品中,這樣的系列創作概念,使得他的作品與美國南方土地緊密結合,透過書寫某個家族的沒落、小鎮的破敗、地方的衰亡,用作品回應其所屬的時代,探討了傳統文化價值面臨社會潮流驟變的過程,資本主義的衝擊、階級、種族、性別到宗教等議題。
福克納的作品文字精粹簡鍊,風格多變,更試圖將小說寫作的可能推展到極限:不按一般前後順序的敘事,常在過去、現在之間跳接,產生另一層時空意義;多重敘事觀點,借用不同角色來敘述故事或者切換第三人稱觀點和內心獨白;意識流的運用也是其作品一大特色,另外,他更有意識地在作品文字段落中植入大量的象徵和隱喻與宗教傳統、神話傳說作連結,使得筆下的現實描寫更豐富,卻也激發多元的聯想,夾帶孤寂、疏離的情調中,仍具樂觀、激昂的情懷。而他描寫美國南方歷史和地誌多部作品中,雖然突顯了現代人的異化和孤獨,卻也懷著寬恕、理解甚至同情的筆調,期盼未來最終能實現真正的世人平等。一九四九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評審評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而有力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譯者簡介:
陳錦慧
加拿大Simon Fraser University教育碩士。曾任平面媒體記者十餘年,現為專職譯者。譯作:《簡愛》、《蘿莉塔》、《在世界的盡頭,我們學跳舞》、《山之魔》、《製造音樂》等二十餘冊。
賜教信箱:c.jinhui@hotmail.com
章節試閱
Ch1 節錄
阿姆史帝跟溫特巴騰蹲在溫特巴騰的畜棚陰涼的牆邊,看見莉娜經過。他們一眼就看出她年紀很輕、懷了身孕,還是個外地人。溫特巴騰說,「天曉得她那肚子是誰搞大的。」
「天曉得她挺著大肚子走多遠了。」阿姆史帝說。
「可能去找哪個住在這條路上的人吧。」溫特巴騰說。
「不太可能。如果是,我不會不知道。也不是住我家那條路的人家。如果是,我也會知道。」
「她知道自己要上哪兒去,」溫特巴騰說。「看她走路的樣子就知道了。」
「她不用再走多久會有人照料了。」阿姆史帝說。那女人已經往前走了,挺著日漸隆起的腰圍和確切無疑的負累緩緩前行。她穿著褪了色的寬鬆藍洋裝,手拿棕櫚扇和小布包。阿姆史帝和溫特巴騰都覺得,她看都沒看他們一眼。「她從遠地來的。」阿姆史帝說,「看她走路的樣子,八成走很久了,而且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她八成來附近探親。」溫特巴騰說。
「是的話我早聽說了。」阿姆史帝說。那女人走過去了,沒有回頭看,消失在馬路盡頭,臃腫、緩慢、審慎、從容、堅靭,就像日影西斜的午後。她也走出他們的閒聊,或許也走出了他們的心思。因為不一會兒阿姆史帝聊起他此行的目的。為了說這番話,他已經來過兩趟,駕著篷車走五哩路,在溫特巴騰穀倉的陰涼牆邊一蹲就是三小時,偶爾吐口痰,全然是那種不疾不徐、拐彎抹角的典型。他來出價,想買溫特巴騰那部待價而沽的耕耘機。最後,他看看太陽,說出了三天前躺在床上時想好的價錢。「傑弗森有一台就是這個價錢。」他說。
「那你最好去買下來,」溫特巴騰說。「很划算。」
「是啊。」說著,阿姆史帝吐了口痰,又看看日頭。「我該回去了。」
他坐上篷車,叫醒騾子,也就是說,他趕起騾子,因為只有黑人才看得出騾子究竟清醒或睡著。溫特巴騰陪他走到圍籬,兩隻手臂擱在欄杆頂端。「沒錯。」他說。「如果是那個價格,我一定會去買。要是你不買,我就要買下來。價格那麼低,我不買就是笨蛋。賣那台耕耘機的人該不會碰巧有一對騾子要賤價拋售賣五塊錢吧?」
「好咧。」說著,阿姆史帝駕車往前走,騾車開始喀噔喀噔地、一哩一哩往前移。他沒回頭看,顯然他也沒看正前方,因為一直到騾車幾乎爬上山頂,他才看見坐在路邊水溝旁那女人。他認出那件藍洋裝的那一瞬間,不太確定那女人究竟有沒有見過他的騾車,也沒人知道他有沒有看她。他們彷彿各自停在原處:騾車在明顯昏昏欲睡的遲緩氛圍與紅土塵埃中吃力地爬向她;騾子沉著的腳步彷彿走在睡夢中,間或穿插挽具的叮噹聲,大野兔般的長耳朵靈巧地擺動。車子停穩後,仍舊看不出騾子是睡是醒。
那頂褪色的藍色寬邊遮陽帽被肥皂和水以外的東西摧殘得更加老舊,帽子底下的她抬頭仰望,沉默又歡喜:青春洋溢、面貌討喜、坦率友善、機靈警覺。她繼續坐在原地。那件同樣褪色的藍色洋裝下的體態看不出曲線,文風不動。扇子和布包擱在大腿上。她沒穿長襪,兩隻光腳丫並攏擱在淺溝裡休息,跟旁邊那雙布滿塵土的厚重男鞋一樣了無生氣。阿姆史帝弓著背坐在靜止的騾車裡,淡藍色的眼眸瞧見那把扇子邊緣整整齊齊滾著跟遮陽帽和洋裝同款的褪色藍布。
「妳還要走多遠?」他問。
「我想趁天沒黑多趕點路。」她一面答,一面站起身,拎起鞋子。她緩慢又慎重地走上馬路,朝騾車走去。阿姆史帝沒下車來扶她,只把兩頭騾子拉穩了,讓她笨重地越過車輪爬上車,再把鞋子擺在座位底下。騾車上路了。「多謝您了。」她說,「走路可真累人哪。」
表面上阿姆史帝自始至終沒拿正眼瞧她,卻已經發現她沒戴婚戒。此時他視線投向別處,騾車又恢復了喀噔喀噔的緩慢步伐。「妳走多遠了?」他問。
她呼出一口氣,不是嘆氣,是平靜地吐氣,彷彿平平靜靜地吃了一驚。「好像已經很長一段路了。我從阿拉巴馬來的。」
「阿拉巴馬?就妳這身子?妳家人呢?」
她也沒看他。「我來這裡跟他會合。也許你認識他,他叫盧卡斯.伯屈。來這裡的路上有人告訴我他在傑弗森,在木材加工廠上班。」
「盧卡斯.伯屈。」阿姆史帝的語氣幾乎跟她一模一樣。他們並肩坐在彈簧斷裂的塌陷座椅上,他看得見她擺在腿上的雙手和遮陽帽底下的側臉,用眼角看得一清二楚。她似乎專注望著騾子靈動雙耳間往前伸展的馬路。「所以妳自己一個人大老遠走到這裡來,就為了找他?」
她半晌才答話,說道,「我碰到很多好心人,大家都很和善。」
「女人也是嗎?」他拿眼角瞄她的側臉,心想,不知道瑪莎會怎麼說。他又想,「我應該知道瑪莎會怎麼說。女人可以做好事,卻未必友善。男人呢,應該會友善。不過,只有行為失檢的女人才可能對另一個需要那份友善的女人非常友善。」他想著:嗯,我的確知道瑪莎會說些什麼。
她上身稍稍前傾,靜靜坐著,側面也一動不動,臉頰也是。「這事可真古怪。」她說。
「妳想不通為什麼大家看見像妳這樣的陌生年輕女孩走在路上,就能猜到她丈夫離開她?」她沒有動。騾車已經發展出一定節奏,車身欠缺潤滑、咿呀亂響的木頭和遲緩的午後、馬路與熱氣融為一體。「妳覺得在這地方可以找到他。」
她一動不動,顯然望著騾子雙耳間的緩慢馬路。她和目的地之間的距離取決於她走過的路程,而她一定能到達目的地。「我能找到他,應該不難。他會在人多的地方,會在歡樂笑鬧的地方,他向來喜歡那種地方。」
阿姆史帝粗魯又唐突地嘟囔一聲,「畜牲,走快點!」他又對自己說了些話,像在自言自語:「她一定找得到。那個傢伙遲早會後悔自己還在阿肯色州的這一邊逗留,甚至德州。」
太陽走到西邊了,離地平線和轉瞬即至的夏夜只剩一小時。小路轉彎離開大馬路,比大馬路更寂靜。「到了。」阿姆史帝說。
女孩馬上行動,她彎腰找到鞋子,顯然不想為了穿鞋子耽擱到騾車。「非常感謝您。」她說,「幫了我很大的忙。」
騾車又停下來了,女孩準備下車。「就算妳趕在太陽山下前走到瓦納的店,離傑弗森也還有十二哩路。」阿姆史帝說。
她一隻手胡亂抓著鞋子、布包和扇子,另一隻手準備下車。「那我最好趕緊上路,」她說。
阿姆史帝沒有伸手碰她。「妳到我家過一夜,」他說。「那裡有女人……有個女人可以……萬一妳……妳跟我回家就是了。明天一早我送妳到瓦納的店,妳可以在那裡搭便車進城。星期六總會有人進城。不差這一晚。如果他當真在傑弗森,明天也還會在。」
她定定坐著,單手拿著隨身物品準備下車,眼睛望著前方,看著馬路拐彎消失的地方,路面有縱橫交錯的暗影。「我應該還有幾天時間。」
「是啊,妳時間還多得很。只是妳現在最好隨時有人陪在身邊,也不能再走路了。妳跟我回家。」他沒等回應,直接趕起騾子。騾車駛進那條陰暗小路。女孩靠向椅背,一隻手仍舊抓著扇子、布包和鞋子。
「我不想麻煩您,」她說。「不想叨擾。」
「沒事,」阿姆史帝說。「跟我回去就是了。」騾子終於自動自發加快腳步。阿姆史帝說,「嗅到玉米了。」心想,「女人就是這樣。她自己搶先做些讓同性姊妹們丟臉的事,然後一個人不知羞恥地到處走,因為她知道人們──那些男人們──都會照顧她。她一點都不在乎別的女人。反正不是女人給她惹出這個她自己根本不在乎的麻煩。是咧,女人只要嫁了人,或沒嫁人就大了肚子,一眨眼工夫她就脫離女人族群,在往後的人生裡想盡辦法擠進男人族群,所以她們跟人學嚼菸、學哈草,還要投票。」
騾車經過屋子、駛向穀倉空地時,他妻子在前門盯著看。他沒望向那邊,他不看也知道她會在那裡,知道她就在那裡。「是啊,」他心想,懷著一股嘲諷的哀怨把騾子趕進敞開的大門。「我完全知道她會說些什麼,我清楚得很。」他勒住騾子。他不用看就知道他妻子現在進了廚房,她不看了,只是等著。他停住騾車,說道,「妳先進屋去。」他自己已經下了車,那女孩正慢慢爬下來,舉手投足之間有一份傾聽內心的慎重。「進去以後如果看見人,那就是瑪莎。我餵完牲口就進去。」她越過穀倉空地走向廚房時,他沒看她。沒這個必要。他亦步亦趨跟著她,也進了廚房,也見著了裡面那個望著廚房門的女人,那女人的眼神跟剛剛在前門凝視騾車時一樣。他想,「我猜得到她會說些什麼。」
他解開騾子的挽具,給牠們水,再拉進畜棚餵了飼秣,又去把草地上的牛隻趕回來,之後才進廚房。她還在那裡,那個扳著一張冷漠、嚴厲、暴躁臉孔的陰鬰女人,那個六年內生了五個孩子,一個個拉拔大的女人。女人正忙著。他沒看她,直接走到水槽旁,從桶裡舀了一盆水,捲起袖子。「她姓伯屈,」他說。「至少她說她要找的那男人姓伯屈。盧卡斯.伯屈,來這裡的路上有人告訴她他人在傑弗森。」他開始盥洗,背對著她。「她說她大老遠從阿拉巴馬來,自己一個人走路來。」
阿姆史帝太太沒有回頭。她在餐桌旁忙著。「她再見到阿拉巴馬之前,會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是一個人。」
「那個叫伯屈的傢伙也一樣。」他在水槽裡用肥皂水盡情洗著,感覺得到她在看他,盯著他後腦勺,盯著他肩膀部位被經年汗漬褪去色澤的藍襯衫。「她說山森雜貨店有人告訴她,說有個叫伯屈或什麼的傢伙在傑弗森的木材加工廠上班。」
「她覺得可以在那裡找到他,而他打點好了房子等著她。」
從她的聲音他聽不出她是不是在看他,他用麵粉袋碎布塊擦抹手臉。「也許找得到。如果那傢伙有心躲她,他遲早會後悔沒等跨過密西西比河再停下來。」現在他知道她在看他,那個陰鬰女人不胖也不瘦,強悍得像男人,能吃苦耐勞,身上那件耐穿的灰色舊衣服又粗又硬,她雙手擱在腰上,臉上的表情活像那些吃了敗仗的將軍。
「你們男人哪。」她說。
「不然要怎麼辦?趕她出去?或讓她睡穀倉?」
「你們男人哪,」她說。「真夠差勁的。」
她們一起走進廚房,阿姆史帝太太走在前面,直接去到爐子邊。莉娜站在進門的地方,她沒戴帽子,頭髮梳理平順,就連那件藍洋裝都顯得精神煥發、恢復了元氣。她站在那裡看著,阿姆史帝太太站在爐子邊把爐頭撞得哐噹響,再用男人般的粗魯蠻力投擲薪柴。「我想幫點忙,」莉娜說。
阿姆史帝太太頭也不回,只粗魯地在爐子上弄出鏗鏘聲。「妳站那兒就好,別到處走動。過些時候妳可能就得躺上好一陣子了。」
「妳讓我做點事我會很感謝。」
「妳留在那裡就行,這些事我一天得做上三回,做了三十個年頭,老早不需要幫手了。」她在爐子邊忙著,沒有回頭看。「阿姆史帝說妳丈夫姓伯屈。」
「是。」女孩回答。現在她很嚴肅,很小聲。她靜靜坐著,雙手一動不動擺在腿上。阿姆史帝太太也沒轉頭看她,她還在爐子邊忙著,爐子需要的關注跟她終於升起火的那股猛烈氣勢似乎不成比例。她專注地顧著爐子,彷彿那是一塊昂貴的錶。
「妳結婚了嗎?」阿姆史帝太太問。
年輕女孩沒有馬上回答。阿姆史帝太太仍舊背對著那女孩,卻沒繼續在爐子上弄出聲響。接著她轉過身,她們四目交會望著彼此,無所遁形:年輕女孩坐在椅子上,頭髮整齊服貼、雙手靜靜貼在大腿上;年長婦人站在爐子邊,身子轉過來,同樣文風不動,花白的頭髮緊緊絞擰在腦袋瓜底下,一張臉彷彿鎸刻在沙岩上。年輕女孩先出聲。
「我沒說實話。我還沒結婚。我叫莉娜.葛洛夫。」
她們互相對望,阿姆史帝太太的語氣不冷不熱,什麼也不是。「所以妳要找到他,趕在孩子出世前嫁給他,是嗎?」
莉娜低下頭,彷彿看著自己大腿上的雙手。她說得很小聲、很堅定、很沉穩。「我不需要盧卡斯的承諾。事情很不湊巧,他不得不離開。他本來打算回去接我的,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們之間不需要山盟海誓,他發現他必須離開的那天晚上,他……」
「哪天晚上?妳告訴他妳懷了孩子那天晚上嗎?」
女孩沉默了半晌。她的臉鎮定得像石頭,卻不堅硬。那份固執帶著點柔軟,一種內心洞徹的非理性與超脫,坦然又平靜。阿姆史帝太太盯著她。莉娜說話時沒看阿姆史帝太太,「在那之前很久他就知道自己可能必須離開那裡,他沒有早點告訴我,是不想我擔心。他剛發現他可能待不下去的時候,就覺得最好還是離開,只要換個不被工頭討厭的地方,他很快就能適應。但他一拖再拖,直到這件事發生,我們就不能再拖下去了。那個工頭欺負盧卡斯,他不喜歡他,因為盧卡斯很年輕,總是精力旺盛。那個工頭想把盧卡斯的工作安排給他自己的表弟。盧卡斯一直不想跟我說這些,怕我擔心。可是發生了這件事,我們不能再等了。是我叫他走的。他說不管工頭怎麼對他,只要我希望他留下,他就會留下。但我要他走,就算是這樣,他還是不想走。但我叫他走。我告訴他,等安頓好要接我過去的時候,派人送個信給我就行。他有心來接我,只是事情不順利。年輕人像那樣自個兒到陌生地方打天下,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安頓下來。他走的時候哪能料得到,哪能知道自己會需要更多時間,尤其是像盧卡斯那樣活力十足的年輕人。他喜歡人群,喜歡打趣,大家也都喜歡他。那時他沒想到他需要更長時間,他那麼年輕,大家都喜歡找他,因為他很會找樂子,很會說笑。他不喜歡拒絕別人,所以常常不知不覺就耽擱了正事。我想讓他好好享受最後一段開心日子,因為婚姻對女人和對年輕男人很不一樣,特別是生龍活虎似的年輕男人。對精力充沛的年輕男人來說,婚姻實在很漫長,妳不這麼覺得嗎?」
阿姆史帝太太沒有答話,只是定定看著坐在椅子上的女孩,看著她柔順的頭髮、靜靜擺在腿上的雙手,和那張沉思中的溫柔臉龐。「說不定他已經派人給我送信,結果給送丟了。從這裡到阿拉巴馬已經是很長一段路,而我還沒到傑弗森呢。我告訴他我不奢望他寫信,因為他不太會寫信。我告訴他,『等你準備好接我過去,派人送個口信就行。我會等你。』他走了以後,剛開始我有點擔心,因為我們還沒正式成親,我哥哥和他那些朋友又不像我那麼了解伯屈。他們怎可能了解他?」她臉上慢慢浮現一抹輕柔又鮮明的驚奇表情,彷彿突然想到了什麼連她自己都沒發現自己不知道的事。「我不能強求他們了解,對吧?他得要先安定下來。他比較辛苦,因為他要跟陌生人周旋。我沒什麼好煩惱的,只要安心等著,讓他一個人去面對那些麻煩和困擾。一段時間以後,我好像只顧著關心肚子裡的孩子,忘了我還沒結婚,也忘了別人的眼光。不過,我跟盧卡斯之間不需要誓約。一定有什麼突發狀況,或者他已經央人送了信,只是弄丟了。所以有一天我決定動身,不再等了。」
「妳出發的時候怎麼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
莉娜望著自己的雙手。那雙手現在動了,著了迷似地理著裙子上的一道褶縫,那不是怯懦或害臊,彷彿只是那隻手沉思時的反射動作。「我到處打聽。盧卡斯是那麼活潑的年輕人,很容易跟人混熟,我知道無論他走到哪裡,人們都會記得他。所以一路問人。大家都很好心。果然,兩天前我打聽到他人在傑弗森,在那家木材加工廠做事。」
阿姆史帝太太盯著那張低垂的臉蛋,雙手叉腰,用冷淡、輕蔑的眼神打量那女孩。「就算他當真在那裡,妳覺得等妳到那裡時他還會在嗎?你覺得等他聽說妳跟他在同一個鎮上,他還會在那裡待到太陽下山嗎?」
莉娜低垂的臉龐很嚴肅、很沉默。她的手停住不動了,靜靜躺在她腿上,像死在那裡似的。她說話聲很輕柔、很平靜、很固執。「我覺得孩子出生時一家人應該聚在一起,特別是頭一胎。我相信上帝會成就這事。」
「我相信祂非得這麼著,」阿姆史帝太太惡聲惡氣地說。阿姆史帝在床上,墊高了頭,視線越過床尾板看著妻子。她還沒更衣,上身彎在梳妝枱的燈光下,粗暴地在抽屜裡東翻西找。她拿出一只鐵盒,用掛在脖子上的鑰匙開了鎖,取出一個布袋,打開來,掏出一隻瓷器小公雞。公雞背後有一道狹長孔洞。她把公雞拿到梳妝枱上方,倒過來猛力搖晃,弄得叮噹響,幾枚錢幣從投幣孔稀稀疏疏地落下。阿姆史帝在床上盯著她瞧。
「這大半夜的,妳拿賣雞蛋的錢做什麼?」他問。
「錢是我的,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她彎身到枱燈下,表情嚴厲、憤怒。「是我辛辛苦苦養大牠們,你沒出過一點力。」
「是咧。」他說,「除了那些負鼠和蛇兒,這個國家沒有哪個人敢跟妳爭那些母雞。也沒人敢跟妳爭那個公雞撲滿。」他補了一句,因為她突然彎下腰,脫下一隻鞋,狠命一擊把瓷撲滿砸個粉碎。阿姆史帝斜躺在床上,看著她從碎瓷片裡挑出剩餘的錢幣,跟其它那些硬幣一起扔進小布袋裡,打了個結,再使勁地打了三、四個結綁牢。
「把這拿給她,」她說。「天一亮你就把騾子套好,送她走。你願意的話,可以一路送她到傑弗森。」
「瓦納雜貨店應該有人可以送她一程。」他說。
Ch1 節錄
阿姆史帝跟溫特巴騰蹲在溫特巴騰的畜棚陰涼的牆邊,看見莉娜經過。他們一眼就看出她年紀很輕、懷了身孕,還是個外地人。溫特巴騰說,「天曉得她那肚子是誰搞大的。」
「天曉得她挺著大肚子走多遠了。」阿姆史帝說。
「可能去找哪個住在這條路上的人吧。」溫特巴騰說。
「不太可能。如果是,我不會不知道。也不是住我家那條路的人家。如果是,我也會知道。」
「她知道自己要上哪兒去,」溫特巴騰說。「看她走路的樣子就知道了。」
「她不用再走多久會有人照料了。」阿姆史帝說。那女人已經往前走了,...


 2016/01/12
201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