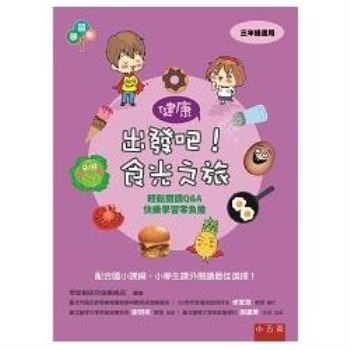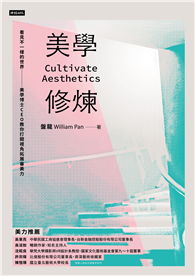此冊新集,延續前書《夜梟》意到筆隨的自然自在;如同前書形式,詩行置於散文中,因此試詩於散文,亦是行筆之間藉以分帙、舒緩,容許作者和讀者得以相互反芻。
書名頁後,引句郭松棻先生逝前剔勵,也是追念年少時未竟的美術眷戀。
從近著《遺事八帖》、《夜梟》及本書《酒的遠方》,文字每學和思想深切、理性與感性交相融匯,正是林文義作品最為圓熟穩健的辨識度;渾然天成練就風格及人格的典範,完美的呈現新文學理念。─陳銘磻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酒的遠方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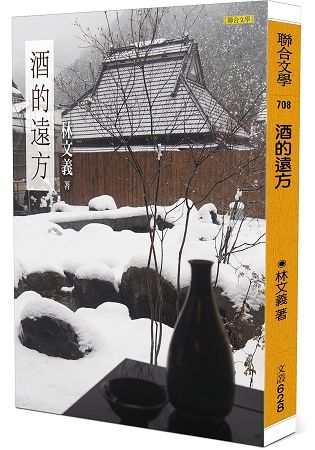 |
酒的遠方 作者:林文義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5-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264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酒的遠方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文義
1953年生於台灣台北市。少時追隨小說、漫畫名家李費蒙(牛哥)先生習繪,早年曾出版漫畫集6冊,後專注於文學。曾任《自立副刊》主編、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時政評論員,現專事寫作。著有散文集:《歡愛》、《迷走尋路》、《邊境之書》等37冊。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革命家的夜間生活》、《妳的威尼斯》3冊。長篇小說集:《北風之南》、《藍眼睛》、《流旅》3冊。詩集:《旅人與戀人》、《顏色的抵抗》2冊。主編:《九十六年散文選》等書。2011年6月出版大散文《遺事八帖》,榮獲2012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
林文義
1953年生於台灣台北市。少時追隨小說、漫畫名家李費蒙(牛哥)先生習繪,早年曾出版漫畫集6冊,後專注於文學。曾任《自立副刊》主編、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時政評論員,現專事寫作。著有散文集:《歡愛》、《迷走尋路》、《邊境之書》等37冊。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革命家的夜間生活》、《妳的威尼斯》3冊。長篇小說集:《北風之南》、《藍眼睛》、《流旅》3冊。詩集:《旅人與戀人》、《顏色的抵抗》2冊。主編:《九十六年散文選》等書。2011年6月出版大散文《遺事八帖》,榮獲2012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
目錄
自序:非典的典型
1希臘
2人間隨意
3那年在基隆港
4酒的遠方
5隱地的鏡子
6飛翔之歌
7我的雪國
8人鬼之舞
9倒影水晶
10蟻丘
11再情書
12繁花聖母
13大寒
14黑歷史
15浮世德定義
16十行詩
17潮聲最初
18華麗廢墟
19夢遊者
20遺信
21夕霧與幽光
22距離十尺
23喧囂的孤寂
24都是美少女
25雙杯合一
26青蛾
27春畫
28邊境隔海
29火燒雲
30永夜的寶石
31普羅米修斯
1希臘
2人間隨意
3那年在基隆港
4酒的遠方
5隱地的鏡子
6飛翔之歌
7我的雪國
8人鬼之舞
9倒影水晶
10蟻丘
11再情書
12繁花聖母
13大寒
14黑歷史
15浮世德定義
16十行詩
17潮聲最初
18華麗廢墟
19夢遊者
20遺信
21夕霧與幽光
22距離十尺
23喧囂的孤寂
24都是美少女
25雙杯合一
26青蛾
27春畫
28邊境隔海
29火燒雲
30永夜的寶石
31普羅米修斯
序
序
非典的典型
我一直欣然地時而翻閱二○一五年初,九歌版自選集《三十年半人馬》,這本從一九八○到二○一○題旨各異的散文書,足以印證三十年夜未眠的寫作者是如何自求精進的時間過程。秉持:書寫文學亦是留下歷史的終極宿願,其實每一帖散文在發表、出版之後,就離開作者了,再重讀、回盼往日的破缺也難以追悔。詩人席慕蓉的油畫封面、亮軒前輩的書序都深切的詮釋我文字的真切意涵,如此護持,何等知心。
記憶延伸到更早之前,忘了是位於台灣大學旁的「胡思」或「永樂座」?就在二手書店的文學座談會後,先遞給我名片的農學院教授,一頭好看的銀髮但比我年輕許多,自稱是「野百合世代」的五年級生,從他的後背包裏取出一冊紫色細薄的書,封面手繪一吶喊衝決著鐵絲網的男子,是我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散文集,春暉版《銀色鐵蒺藜》;書封水墨淋漓如此凜冽,出自繪與文兼美的前輩作家:雷驤。
農學院教授請我題簽,真切的說,這本書帶到美國留學又返回台灣執教;我靜靜看著自己三十年前的舊書,陌生遙遠得彷彿是前生。只有李昂的序文依然親炙而熟識,她形容八十年代的我是「都會的旅人」,就在她將前往艾荷華作家工作坊前夕時為我新書下的美好紀念。序文副標題,這位秀異的小說家寫著──「最好的散文家˙最摯愛的朋友」三十年後再次拜讀昔書序文,「最好」想是她慷慨的溢美與期許,「摯愛」合應就是我們對文學的虔敬。
近時有人問起我半生著力於散文書寫、兼及六冊小說、兩冊詩集和早年漫畫,六十種著作,要全數讀過不免辛苦,盼我自認可留可傳之書是哪些定本?既以散文為主要選項,遂敬謹的提出二○一○年後的近著八冊做為定本印記──
《邊境之書》二○一○聯合文學
《歡愛》二○一○爾雅
《遺事八帖》二○一一聯合文學
《歲時紀》二○一四聯合文學
《三十年半人馬》二○一五九歌
《最美的是霧》二○一五有鹿文化
《夜梟》二○一六聯合文學
《二○一七日記──私語錄》二○一八爾雅
第九本新書,就是此時自序後讀者知友即將逐頁翻閱的《酒的遠方》了。彷彿就是生命流程的時序感思,猶如評論家張瑞芬教授形容我以日記書寫散文的特質;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實浮沉之間,幸好文學救贖我的顛躓和鬱悶。散文是我的鏡子,是人是鬼,陰暗或晴亮,走到今日就像逆水而上的舟子,溯河到盡頭了嗎?不想餘生如何,就放槳任自漂流吧。
回想「摯愛」的文友李昂在三年前秋深的文學獎項致辭時,形容她和我都是「非典型」的極少數作者,那分慨然的不捨我深切感銘於心。另類異端,特立獨行,時而不被所謂的主流價值認同,又有什麼關係,何是創作?風格即人格,堅執自信的我手寫我心,就是典型。
這冊新集,延續前書《夜梟》那意到筆隨的自然自在;曾經說過:散文是我的自由。與之同時每天記載的爾雅版《二○一七日記》猶若和弦,《人鬼之舞》似合似離的巧妙呼應,有時是雙人舞,有時是單人獨步……知交莫逆的諍友:隱地先生和王定國,定能深諳此一情境。
如同前書形式,詩行置於散文中,實是向來愛詩,因此試詩於散文,亦是行筆之間藉以分帙、舒緩,容許作者和讀者得以相互反芻。
意外的逸趣,自繪戲作美人圖刊印書名頁後,引句郭松棻先生逝前剔勵,也是追念年少時未竟的美術眷戀。老友陳銘磻言之此書與前二冊:《遺事八帖》、《夜梟》暗合允為三部曲的圓滿完成,確有此意,果然是靈犀在心。
感謝:筆和紙,修正液,忍受手工寫作的副刊、雜誌編輯諸君。承允收入卷末的「四家之言」,護持、包容的聯合文學出版社。
(二○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臺北大直)
非典的典型
我一直欣然地時而翻閱二○一五年初,九歌版自選集《三十年半人馬》,這本從一九八○到二○一○題旨各異的散文書,足以印證三十年夜未眠的寫作者是如何自求精進的時間過程。秉持:書寫文學亦是留下歷史的終極宿願,其實每一帖散文在發表、出版之後,就離開作者了,再重讀、回盼往日的破缺也難以追悔。詩人席慕蓉的油畫封面、亮軒前輩的書序都深切的詮釋我文字的真切意涵,如此護持,何等知心。
記憶延伸到更早之前,忘了是位於台灣大學旁的「胡思」或「永樂座」?就在二手書店的文學座談會後,先遞給我名片的農學院教授,一頭好看的銀髮但比我年輕許多,自稱是「野百合世代」的五年級生,從他的後背包裏取出一冊紫色細薄的書,封面手繪一吶喊衝決著鐵絲網的男子,是我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散文集,春暉版《銀色鐵蒺藜》;書封水墨淋漓如此凜冽,出自繪與文兼美的前輩作家:雷驤。
農學院教授請我題簽,真切的說,這本書帶到美國留學又返回台灣執教;我靜靜看著自己三十年前的舊書,陌生遙遠得彷彿是前生。只有李昂的序文依然親炙而熟識,她形容八十年代的我是「都會的旅人」,就在她將前往艾荷華作家工作坊前夕時為我新書下的美好紀念。序文副標題,這位秀異的小說家寫著──「最好的散文家˙最摯愛的朋友」三十年後再次拜讀昔書序文,「最好」想是她慷慨的溢美與期許,「摯愛」合應就是我們對文學的虔敬。
近時有人問起我半生著力於散文書寫、兼及六冊小說、兩冊詩集和早年漫畫,六十種著作,要全數讀過不免辛苦,盼我自認可留可傳之書是哪些定本?既以散文為主要選項,遂敬謹的提出二○一○年後的近著八冊做為定本印記──
《邊境之書》二○一○聯合文學
《歡愛》二○一○爾雅
《遺事八帖》二○一一聯合文學
《歲時紀》二○一四聯合文學
《三十年半人馬》二○一五九歌
《最美的是霧》二○一五有鹿文化
《夜梟》二○一六聯合文學
《二○一七日記──私語錄》二○一八爾雅
第九本新書,就是此時自序後讀者知友即將逐頁翻閱的《酒的遠方》了。彷彿就是生命流程的時序感思,猶如評論家張瑞芬教授形容我以日記書寫散文的特質;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實浮沉之間,幸好文學救贖我的顛躓和鬱悶。散文是我的鏡子,是人是鬼,陰暗或晴亮,走到今日就像逆水而上的舟子,溯河到盡頭了嗎?不想餘生如何,就放槳任自漂流吧。
回想「摯愛」的文友李昂在三年前秋深的文學獎項致辭時,形容她和我都是「非典型」的極少數作者,那分慨然的不捨我深切感銘於心。另類異端,特立獨行,時而不被所謂的主流價值認同,又有什麼關係,何是創作?風格即人格,堅執自信的我手寫我心,就是典型。
這冊新集,延續前書《夜梟》那意到筆隨的自然自在;曾經說過:散文是我的自由。與之同時每天記載的爾雅版《二○一七日記》猶若和弦,《人鬼之舞》似合似離的巧妙呼應,有時是雙人舞,有時是單人獨步……知交莫逆的諍友:隱地先生和王定國,定能深諳此一情境。
如同前書形式,詩行置於散文中,實是向來愛詩,因此試詩於散文,亦是行筆之間藉以分帙、舒緩,容許作者和讀者得以相互反芻。
意外的逸趣,自繪戲作美人圖刊印書名頁後,引句郭松棻先生逝前剔勵,也是追念年少時未竟的美術眷戀。老友陳銘磻言之此書與前二冊:《遺事八帖》、《夜梟》暗合允為三部曲的圓滿完成,確有此意,果然是靈犀在心。
感謝:筆和紙,修正液,忍受手工寫作的副刊、雜誌編輯諸君。承允收入卷末的「四家之言」,護持、包容的聯合文學出版社。
(二○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臺北大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