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世紀光陰,以心血灌注散文生命,柔軟實則強韌的筆觸,始終關懷臺灣的核心議題及弱勢族群;時而瞄準中心焦點,也時而抽離又流浪遠方,折衝在理想與幻滅之間,但始終不變的是人道主義的襟懷,每一階段的作品,都是時代見證,皆為臺灣真確的聲音。」──《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
林文義的散文語言獨樹一格。文字的華麗與蕭索、纖柔與剛毅,筆觸的輕盈爽朗與沉鬱蒼茫,語氣的濃稠纏綿與平淡指點,心情的熱切與憂傷,訴求的公共議題與私己情事,諸如此類相異的特色或氣質,在林文義的散文作品裡,經常交相映陳,而貫穿其中的則是林文義自稱的「真情實意」與「浪漫抒情」,並且因而流露出令眾多讀者深為著迷的文體風格。──2014吳三連獎文學獎評定書
林文義的散文語言獨樹一格。文字的華麗與蕭索、纖柔與剛毅,筆觸的輕盈爽朗與沉鬱蒼茫,語氣的濃稠纏綿與平淡指點,心情的熱切與憂傷,訴求的公共議題與私己情事,諸如此類相異的特色或氣質,在林文義的散文作品裡,經常交相映陳,而貫穿其中的則是林文義自稱的「真情實意」與「浪漫抒情」,並且因而流露出令眾多讀者深為著迷的文體風格。──2014吳三連獎文學獎評定書
半世紀以筆就紙,不渝的藏身在墨水中;那是青春習繪未竟反而學文的情境思索。晚秋回眸猶然不忘在此新集中頁留與昔日插畫,前後時距卅四年,巧合相伴卅四帖散文;值此:瘟疫漫延時。──林文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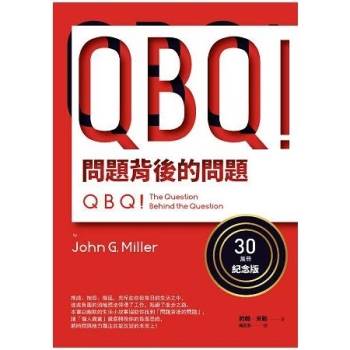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