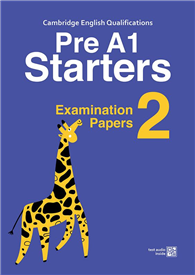只要心中存愛,
生命總有活泉。
記得!川川。
◆白先勇長文推薦:川川就是奚淞自己,這部札記記載奚淞的「精神之旅」,更是他剖心瀝膽的靈魂「懺情錄」。
一本傳愛之書,
記寫人的嚮往與生命思維,
只為傳述一份人生的變化和感動給你。
從朝曦到日暮,由青春到年老,縱然人生情境如萬花筒般紛陳千萬現象,一個「愛」字卻始終傳遞,並且雕造、成就了我們心靈的面貌。
吾人出生於愛;隨順並歸依於愛;歷經種種礙難與困縛,盼望終究能成全於愛。
川川,即或人生有時不免孤獨,我總信賴生命會聯結生命,而人畢竟是要與人相依相存的。
川川,活著真好!
◆
年少時出於內在的不安與脆弱,也對人生充滿質疑與憂悶,作者藉由書寫札記,重重探問生命存在的真義。歷時一年半載,他每月記下思緒的點點滴滴,種種存在的感動和疑惑,傾訴給他心中唯一的對象「川川」—— 一條流動的河川;這流水就彷如內心變動不居的意識流,於焉展開一場文學式的高我對話。
什麼是死、什麼是生?
如何解釋心靈的渴盼、苦惱和無止境的嚮往?
奚淞創作於三十五年前的系列札記,呈顯他對生命存在問題的特殊洞達與感謝心情,逐篇且收錄十八幅宣紙彩繪。以文、以圖,思考人生焦慮與痛苦的來由,湧現微笑希望的活水。
◆
宇宙間至大的神祕,可以歸結為小小的一個字——愛。
隨書附:奚淞「剪紙傳愛」,窗花教作!
窗花貼在玻璃窗上,是一種光的藝術。
「愛」的剪紙其鏤空透光的背景作圓形。圓,古來心靈象徵,又稱之為「曼陀羅」。中間嵌入筆劃飽滿連結的「愛」字。朝輝夕陰變化中,剪紙窗花上愛字或隱或顯,就像一朵盛開、紅豔的大花。它也是人人心中藏有的一朵花。
來,學做剪紙,把愛傳遞出去罷。
作者簡介:
奚淞
畫家、文學家,喜以「手藝人」自居。
一九四六年出生,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後,留學法國巴黎習畫。一九七五年返國,先後擔任《雄獅美術》、《漢聲雜誌》編輯,長期關注國內藝術環境發展,投入文化扎根的工作,曾參與兒童叢書的編寫策劃,並在報刊上發表系列木刻版畫與散文。中年後潛心探究佛學,擅長佛教藝術創作,尤以白描觀音、佛傳油畫著稱。
出版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畫冊等十餘種,包括《封神榜裡的哪吒》、《姆媽,看這片繁花!》、《給川川的札記》、《三十三堂札記》、《光陰十帖——畫說光陰》、《大樹之歌——畫說佛傳》、《微笑無字書》等。近期與白先勇合著《紅樓夢幻》。
作者序
剪紙傳愛——寫給川川
◎奚淞
二○二一年農曆春節裡,我應邀為一群佛堂志工教做剪紙窗花。聯誼同樂性質的活動裡,座中皆是銀髮族。
今年我設計的新年吉祥字既特殊、也平凡,是圖形鏤空背景中,一個紅豔豔的「愛」字。
能舉辦一堂用剪刀做手藝的功課,銀髮志工們都返老還童、很開心。座席間但見他們忙著掏找老花眼鏡、試驗手中剪刀開合。這是民俗學者稱之為「母體藝術」的傳統手藝。從未剪過窗花的人,初啟動時不免覺得手笨眼拙,老學生們紛紛交頭接耳、笑語此起彼落。經過一段試探,他們領略到訣竅,便都靜默、專心剪紙了。此時彷彿春蠶食葉,席間一片微細絞剪、移轉紙片的窸窣聲。紅紙碎片紛墜、飄落,果然一團祥和、溫暖新春氣息蔓延開來……
踱步桌椅間,見他們剪紙都上手了,不管老人們愛不愛聽,我為他們即席朗誦一篇陳年舊文,題目為「人心不安,多因愛字欠缺」。最近我偶然翻讀到這篇文章,作者是民國初年、編印第一部現代佛學辭典的丁福保先生。丁氏文章大意如下:
「處世當以愛字最為有益。心不平安,都是因為愛字欠缺。如見周遭人或事,不覺得可愛而反生厭惡。又猜疑別人不喜歡我,必須防止他來害我;若認為事物皆與我為敵,於是怨風罵雨憑空生起……
「此等人猶如病患,最好能勉強自己學習慈善;試著無論遇到何人何事,都能夠心生善意。此念一發,自然牽引四周和氣回應。即使原來對我有疑忌、甚或想謀害我的人,也會回心轉意。於是社會和諧,人人互愛——
「如此人生俯仰無愧,身心泰然,可得長壽之功。」
誦念丁福保「傳愛」之文,頗似老生常談、無甚稀奇;至少結論是身心泰然、平安長壽,多好。佛堂裡,銀髮耆老們活到這把年紀,得要經過多少世途滄桑。從熟透了的人生經驗中,不讀文章也能明白:沒有愛,不能安心;不安心,還能健康、長壽嗎?俯首手中剪出殷紅飽滿的愛字,就像一朵盛開的花;蘊藏了天地間的奧秘。座席間完成剪「愛」手藝功課的老人,他們拎著窗花左看右看,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靨。
新冠肺炎疫情從去年爆發到全球蔓延,造成人們驚恐、災難和死亡,至今已經進入第二年。台灣因為防疫工作做得好,大夥居然還能正常聚眾活動,已經算是夠幸福的了。
愛在瘟疫蔓延時
春節過去,「剪紙傳愛」卻不受歲時節令影響,我又接到「雄獅星空」文創藝廊邀約,希望我去辦一場剪愛、說愛的活動。這可真是「愛在瘟疫蔓延時」,我笑著想到馬奎斯小說書名。
「雄獅星空」創辦人柏宏與淨馨夫婦是我熟識的晚輩,去年疫情嚴重期間,我們曾經合作,做過一檔很好的展覽。
是在去年四月初,柏宏與淨馨忽然連袂來訪,有要事商談,原來是出於疫情,國際交通與運輸全部中斷。「星空」原已籌劃半年的日本藝展必須取消。在當時一片惶恐風潮中,許多中小商店都準備歇業。柏宏夫婦卻不捨「星空」關門,臨時與我討論,可有別開生面、度過難關的方法?
這是災難挑戰、激發思考的一大關鍵。究竟應當掙扎求存呢、還是歇手不幹?其實,留學日本的柏宏,算是少數生活低調、不嘩眾,喜好村上春樹式「小確幸——微小而確切存在的幸福」理念的新一代人。他所創業的「雄獅星空」也就是那雅淨、散發淡淡咖啡香和書香的藝文空間。平常就如空谷幽蘭、訪客無多,此時又何必考慮歇業?
「好哇,就讓我們一起摸著石頭過河,」我笑說:「好好辦一場對付瘟疫的展覽。」
我說「摸石頭過河」,其實心裡是想到原始佛教、巴利文教典裡,一則佛陀教導弟子如何度越人生急湍暴流的簡短問答:
一日,弟子問佛陀:「世尊,您是如何度過輪迴的暴流的呢?」
「朋友,」佛陀說:「我既不滯留、也不掙扎,就度過了暴流。」
雖然聽到回答,弟子倒更驚奇了,又追問:「但是,世尊啊,您又是如何能夠辦到的呢?」
這時候,佛陀該是要微笑了罷。他不急不徐、條理分明的再答道:「如果當我滯留,朋友,我便沉沒;而如果當我掙扎,則會被急流渦旋捲走;因此,朋友,我就是這般不滯留也不掙扎,因此度過了危險的急湍河流。」
讀到這則南傳佛教《相應部‧第一經》的簡短記錄,兩千五百年後的佛弟子如我,是從現代人流行的心理病「躁症」和「憂鬱症」角度來思考的。面對強大的現實壓力,擔心自己過不了關,佛所謂「掙扎」,猶如陷入身心極度不安定的「躁症」;而所謂「滯留」,就像掉進昏沉、麻木、自我封閉心態的「憂鬱症」。在我心目中,佛陀是名副其實的大醫王,他不急不徐、不慍不火的中道說法,足以治療人心的憂慮和焦躁,進而離苦得樂。這不也正是我們此刻面對疫情可以學習並依持的心法。
於是摸著佛法「正念當下」的靈石,我們為疫情中的展覽定名為「平安‧微笑——來自星空的祝福」。展品包括「心平安」及「身平安」;前者有我創作的《大樹之歌——佛傳故事》木刻版畫系列及《光明靜好》文創燈具,後者有鄭惠中的布衣系列及專為疫情設計的夾層布口罩。如此,身心俱都得到平安祝福,來到「星空」的訪客,能不微笑起來嗎?
回看二○二○年五月到六月間,這檔既無開幕式、也不廣加招徠的「平安‧微笑」展,竟成為口耳相傳,人們在疫情期間享受到的「小確幸」,得到不少知音者好評。
特別當時「星空」在咖啡座臨窗增設一席專為抄心經、描菩薩的「心靈角落」,成為熱門預約好位子,直到今天還有人不斷問起。
遺忘在洞穴裡的夢境
今年裡,「剪紙傳愛」活動接連發生。春三月裡,參與「星空」剪愛活動成員,多半是盛年黑髮、來自社會各行業人士。而後,又有慈濟大愛電視台《青春愛讀書》節目的錄影。由於節目主題在年輕人對文學、手藝和情緒的看法。這下子,邊剪紙、邊探討愛之困擾的族群,就換作從十五到二十歲上下的青少年了;訪談過後,久久不能忘懷少年們閃爍、充滿疑問的清亮眼神。
由退休銀髮族到社會中堅,乃至於尚未脫離父母羽翼的青少年。在接連剪紙活動中,這幅殷紅透亮的「愛」字窗花就像扭轉記憶的時空隧道,令我回頭看歲月中種種礙難和困境對愛的雕鑿。
川川,我著實沒想到,就連你也忽然現身了。
應該不是在作夢罷,川川?我竟看見你在被褥暑逼淺了的新店溪彼岸、芒草叢間的鵝卵石灘上,邊行走、邊笑著向我頻頻揮手,似乎在招呼我脫下一身累贅,趕緊度過河去……
二○二一「剪紙傳愛」的春三月中,最強烈的印象莫過於必須回溯、重新翻開三十五年前《給川川的札記》舊稿了。這就像打開一處被地層變動天然掩蓋的史前文明洞穴,如同德國導演荷索《遺忘夢境之洞穴》(Cave of Forgotten Dreams)紀錄片,影片混合著探險考古家心脈搏動和岩洞滴水聲、在攝影機拍攝移動的光照中,數萬年前人類斑剝的手印和圖畫,在凹凸不平的岩壁上像夢境一般活動起來。導演荷索在此追問:人類心靈最原始、最深奧之處,究竟在夢著些什麼?
事件是這樣的,聯合文學昭翡早就催促我重新出版舊作《給川川的札記》了。這本有插畫的散文集,是從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我在《皇冠雜誌》逐月發表的系列圖畫及散文,集結出版於一九八八年。由於時日久遠,我手邊留下最後一本碩果僅存的珍藏本,也都被友人借走、尚未歸還。為了昭翡約我在四月裡寫成重新出版的書序,我必須翻箱倒櫃,找出歲月沉埋的文圖稿。
當文圖「出土」時,我的心果然如「重尋遺忘夢境」般砰砰跳,也有一份不明所以的近鄉情怯之感。為什麼?
三十五年前黑髮、盛年、從法國巴黎美院習畫歸來後的我,彼時正與「漢聲出版社」夥伴一同做民俗田野調查,同時為提升青少年教育,進行《中國童話》及《小百科》等從民間文學到科普材料收集、編寫工作。可以算得上是身擔重責、相當忙碌的社會中堅。
經濟起飛期,生活在熱鬧台北、經常為上下班交通巔峰時間,受困公車裡動彈不得而苦。表面十分忙碌的我,在內心裡,又像永遠在推敲文句、卻寫不出一行詩的詩人;常覺孤獨,處於情感的白日夢中。這便是行走在凡俗世間、一個夢遊的傻子……
我小心翼翼、解索,啟開密封了三十多年的畫夾子。當時模倣學院裡教授壁畫的技術,以白粉填底、在宣紙上畫成的彩圖,大概是因為未見天日的緣故,居然鮮豔、潤澤如新,就像剛剛才畫好一般。我不由得驚歎,把十八張彩圖依順序,一一展鋪在畫室地板上。
再來,就是那一封牛皮紙袋中的手稿。豈不像私密珍藏的情書?當時用鉛筆工整一個字、一個字寫在稿紙上的散文原稿,十八個月積累成厚厚一大紮,總有數百頁之多罷。不曾有隻字片頁散失,卻都在這三十五年的光陰消磨中變得煙黃,並且如陳年植物葉片標本般易碎了。
有愛,便是活泉
一頁頁翻讀……啊,川川,我看到你了。的確是在當時新店溪畔,夏日可以游泳、撿拾鵝卵石;秋來芒草花盛開成銀白一片,而彼岸的你笑著朝我揮手……
從朝曦到日暮,由青春到年老,縱然人生情境如萬花筒般紛陳千萬現象,一個「愛」字卻始終傳遞、並且雕造、成就了我們心靈的面貌。作為人類一員,無論知與不知、覺或不覺,我們出生於愛;隨順並皈依於愛;經過種種礙難與困縛,盼望終究能成全於愛。
一頁頁翻讀……啊,川川,那始終藏匿在各種情境現象下、並且一再向我們現身的,不就人心中「愛」的真相嗎?
如是「喜夕陽作晨曦,欣暮逝於朝聞」,銀髮的我讀至《給川川的札記》末尾三行字跡:
「只要心中存愛,
生命總有活泉。
記得,川川。」
是為序。
剪紙傳愛——寫給川川
◎奚淞
二○二一年農曆春節裡,我應邀為一群佛堂志工教做剪紙窗花。聯誼同樂性質的活動裡,座中皆是銀髮族。
今年我設計的新年吉祥字既特殊、也平凡,是圖形鏤空背景中,一個紅豔豔的「愛」字。
能舉辦一堂用剪刀做手藝的功課,銀髮志工們都返老還童、很開心。座席間但見他們忙著掏找老花眼鏡、試驗手中剪刀開合。這是民俗學者稱之為「母體藝術」的傳統手藝。從未剪過窗花的人,初啟動時不免覺得手笨眼拙,老學生們紛紛交頭接耳、笑語此起彼落。經過一段試探,他們領略到訣竅,便都靜默、專心剪紙了。此時彷彿...
目錄
【推薦序】奚淞的「情書」,奚淞的「心經」——重讀《給川川的札記》/白先勇
【自序】剪紙傳愛——寫給川川/奚淞
◎五月的札記
給川川。婦人。神蹟。福樓拜爾。入梅。假日黃昏。天人五衰。叢林裡的鼓聲。
◎六月的札記
蒲公英。論美。未來的時代……。心。鈴鐺。水祭。曇花。曇花的邀約。
◎七月的札記
審判。傷心。秋花。顏色。傾向那水。
◎八月的札記
相看。蛻之一。蛻之二。蛻之三。母土與邊疆。
◎九月的札記
重縫一行針線。與星空交會。金言。秋日之心。樹蛙。
◎十月的札記
自我。對話。看海去之一。看海去之二。我將啟程。
◎十一月的札記(上)
開心。書法之美。沙羅雙樹下的佛陀。古董收集家。地光和地音。十一月的雨雲之上。晚晴。
◎十一月的札記(下)
芒草花。渡我過河。傳說。補天。
◎一月的札記
瞬間。永遠。白描觀音。曼陀羅。暖冬與友人。
◎二月的札記
日光和花。世界之晨。神聖的「唵」。火山居民。裸。星光與流螢。給H君。
◎三月的札記
不眠。暖石——遊太魯閣一。山之巔——遊太魯閣二。獵人家族的葬儀——遊太魯閣三。桃花與老榮民——遊太魯閣四。瞬息燭火——遊太魯閣五。
◎四月的札記
童年。花裡逢君。愛麗絲——與T君談天殘局一。藝術?——與T君談天殘局二。藝術之用——與T君談天殘局三。春日‧天涯。
◎五月的札記
外太空訪客。餐廳。記憶中的課堂——紀俞師一。人間重晚晴——紀俞師二。優曇——紀俞師三。
◎六月的札記
觀自在。呼喚。舍利子的答辯。洗浴。日安‧菩薩。
◎七月的札記
風景。公務袋。處境。舞台上的垃圾山。河畔的垃圾山。守靜。
◎八月的札記
青蟲和小樹。花動。無憂。賞荷。石珠和眼淚。
◎九月的札記
焚稿。合十。石與果。苦惱和尚的故事。秋雨。
◎十月的札記
中秋夜的神祕劇。香港之子。在皇后廣場。失落的彌勒。給川川。
【附】「愛」字剪紙教作
【推薦序】奚淞的「情書」,奚淞的「心經」——重讀《給川川的札記》/白先勇
【自序】剪紙傳愛——寫給川川/奚淞
◎五月的札記
給川川。婦人。神蹟。福樓拜爾。入梅。假日黃昏。天人五衰。叢林裡的鼓聲。
◎六月的札記
蒲公英。論美。未來的時代……。心。鈴鐺。水祭。曇花。曇花的邀約。
◎七月的札記
審判。傷心。秋花。顏色。傾向那水。
◎八月的札記
相看。蛻之一。蛻之二。蛻之三。母土與邊疆。
◎九月的札記
重縫一行針線。與星空交會。金言。秋日之心。樹蛙。
◎十月的札記
自我。對話。看海去之一。看海去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