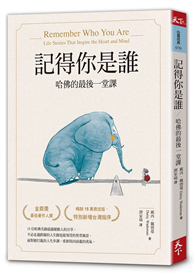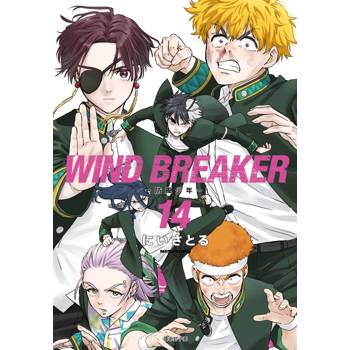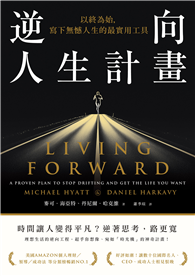固執的妳,定要見到才相信
上帝如庇佑,一棵無花果樹
在寒冷佛蒙特州也能生長
妳不明白,失樂園,花如人
凋謝一生,不會循環再來
再來是另一世,不知前生。
張錯的「誦讀葛綠珂」,是詩人透過與葛綠珂(Louise Gluck)的三十八場詩對話,演出的三十八場詩劇。舞台布景寬闊縱深、演出時空綿長,從希臘神話、荷馬史詩、到葛綠珂所歷人生風景,乃至張錯自身境遇。事件、人物、場景不同,詩人擇取的面具與發聲也不同。誦讀之,有音聲節奏自樸素語詞發出,迴盪耳中心中,如歌似曲之詩。──蕭義玲(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